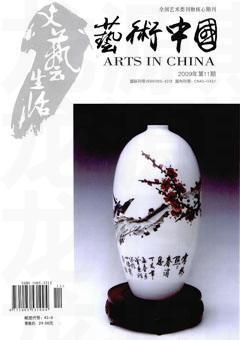自知的文化传薪者
刘兴国
中国的文化历经数千年而不朽,其中一个重要的特质就是她的承传性。她不断地在有意无意之间培养着不同时期的大师,让承传的可能变为现实,使其薪火相继、绵延不绝。如果就元代的文艺而论,确乎仅有一人称得起“执牛耳者”的大师——赵孟頫。
赵孟頫(1254~1322),南宋宝祐二年生,元英宗至治二年卒,享年六十九岁。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别署水晶宫道人、鸥波。浙江吴兴(今湖州)人,人称赵吴兴。为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十世孙,历官翰林学士承旨、集贤学士、封荣禄大夫,故世又称赵学士、赵承旨、赵集贤、赵荣禄。其卒后受封魏国公、谥文敏。
对赵孟頫的评判在当代已经有了比较公正的认同,依笔者浅见,对他的人生坐标还可以有另外的定位,即“自知的文化传薪者”。第一,说他“自知”,是因为赵孟頫生命中任何一点的决断都是“知性”指引下的明智选择,他不像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八大山人,因为八大的许多决择都是被迫状态下迷迷糊糊的无奈之举,而赵孟頫却是在聪敏性灵导引下的主动避让。他就像争道的担夫,虽然山路奇险,人流接踵,却也避让有度,进退自如。可是,“自知的决断”也并非易事,它需要对自我和现实做出深刻的辨析;同时,决断带来的任何后果又要无条件的担当。其背后的勇气和毅力是常人无法理解和轻易做到的。第二,说他是“文化传薪者”,皆因赵孟頫的行为所带来的综合社会效应。这个效应不单单是艺术领域的借古开今。而且是整体中华文化的续承。
赵孟頫的许多行为历来受到世人的诟病,主要集中在“出仕”与“失节”和“复古”与“开新”上。本文无意求新,也以这两个方向为入口,只是角度有所不同而已。说到“角度”,我想到了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的一段话:“我很少对历史人物做评判,因为很难站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去理解他们,我们的角度是很难公正的。”如果将许先生的话语反过来理解。人们尽可能地站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去换位思考,也许会更加公正一些。今天将赵孟頫“复活”是无法实现的,但我们可以拨开重重迷雾和偏见去无限地接近他,也可以体察这位“自知的文化传薪者”以何等的理智和坚韧来完成自我的使命。
一、“出仕”与“失节”
赵孟頫出身的特殊性给他的人生境遇带来了一定的转变,元仁宗在评价赵孟頫“人所不及者数事”中的第一点便是“帝王苗裔”。可是,家族的所谓优越性也为他的生命预设了诸多羁绊。在家族中,赵孟頫有兄弟八人,他排行第七,又为偏房丘氏所生,即非嫡传,又非长子,其在封建家族中的地位可称卑微。虽然他的曾祖到父亲皆为南宋显官,但十二岁时父亲便撒手人寰。而且,随着1279年宋恭帝降元,赵孟頫又沦为了国破家衰的“特殊平民”,使这位风华正茂的青年饮痛江南。宋亡后的第二年,赵孟頫父亲的坟墓被盗;不久,生母亦辞世而去,这让他一次又一次遭受精神上的打击。从小陪伴和教育他的母亲,使他直接感染着母性处事的柔顺,复杂的心性中也充满了多愁善感和抑郁惆怅。反过来。家族地位的卑微也让赵孟頫的内心燃起了一种强烈的奋进和倔强。一方面是棉里藏针的反抗,另一方面是不动声色的进取。他深刻地明白,家族的光环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坦途,他必然要寻找一条让“自我价值”能够实现和被认同的出路。
《元史·赵孟頫列传》载:“赵孟頫……幼聪敏,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宋亡,家居,益自立于学。”南宋灭亡后,赵孟頫一度蛰居,生母丘氏说:“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你不多读书,如何超乎常人?”他因而愈加努力,拜老儒敖继公研习经义,学业日进,声名卓著。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更注重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并以文治之道为立国之本。他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曾命行台治书侍御史程矩夫往江南访贤,“超乎常人”的赵孟頫自然是首选。况且,在程钜夫寻访江南之前,作为“吴兴八俊”之一的赵孟頫已经“声闻涌溢,达于朝庭”,为吏部尚书夹谷之奇所赏,举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其辞而不赴,并在《赠别夹谷公》一诗中说:“青春惠兰花,含英在林中。春风不披佛,胡能见幽心”,隐晦地道出了时机不当、暂不出山的想法。这是对元朝统治者的一种试探,也同时表明了赵孟頫的思想。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赵孟頫正是期待着“有道者”的“春风披拂”。这时的他,“出仕”的想法是占主体的。最后,在程钜夫的二请之下,赵孟頫于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应诏入宫。加上夹谷之奇的第一请,共为“三请”。这好像“三顾茅庐”的故事一样,赵孟頫看到元朝如此尊崇他,他没法再拒绝这样的“出仕”机会。也如同某些学者的设想:不是刘备三顾诸葛亮于草庐之中,而是诸葛亮数瞻玄德于馆驿之内。赵孟頫是否明白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出任胡元”会引来旁人的侧目呢?他又是如何理解的呢?这在他的《送吴幼清南还序》中有明确的表白:“士少而学之于家,盖亦欲出而用之于国,使圣贤之沛然及于天下。此学者之初心。然而往往淹留偃蹇,甘心草莱岩穴之间,老死不悔,岂不畏天命而悲人穷哉!诚退而省吾之所学于时有用耶?无用耶?可行耶?不可行耶?则吾出处之计了然定于胸中矣,非苟为栖栖也。”况且,在他身边还有一位“宁死不食周粟”的哥哥一赵孟坚,他岂能看不出世人的冷眼?而是“出处之计了然定于胸中”的坚毅战胜了世俗的影响。
再看看赵孟頫的“隐”,他在出仕前的“杭州文化圈”中已经有了很高的声望,诗文书画常常被称为“当世第一”,而且,畅游湖山的快意和笔歌墨舞的真性已经成为他生活中自然而然的习惯,他留恋这种生活方式,而“丝竹乱耳”、“案牍劳形”的俗务和尔虞我诈的权利争斗是他不喜欢的。但也需说明一点,“不喜欢”并不等于“做不来”,从赵孟頫参与铲除暴虐成性的桑哥逆党的行为中,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超常的睿智和勇气,甚至可以说“极具政治手腕”。从这一点就也可以否定人们对赵孟頫性格懦弱的评价。另外,从元世祖忽必烈到元英宗五代统治者对赵孟頫的信任和擢拔来看,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元史·赵孟頫列传》中载:“孟頫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世祖顾之喜,便坐右丞叶李上,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听,遂将此人逐出宫外。”忽必烈深见赵孟頫的才能,甚至每次见他都“语必从容久之,或至夜分乃罢”……这能简单地说他“失意”吗?能讲他受到大范围的排挤吗?如果他不是“荣登一品”的地位。还能受到世人过分的责难吗?显然不能。而赵孟頫“稀入宫中,力请外补,远离京师”的行为,纯是深谙历史变故下的自保手段,也是深知避让而后再图进取的策略。
所以,赵孟頫的“仕”与“隐”全然出于自我的意愿,旁人和现实的催逼只是微不足道的外因。在他“仕隐双兼”的行为中,还可以体会出他究竟是“失节”还是“守节”。
赵孟頫出仕以后,在铲除奸党的重大政治行为以外,还有其他的举动值得我们关注。这方面主要集中在“复兴汉学”和提携后辈上。复兴汉学需要做多方面的努力。首
先,赵孟頫收集了大量的古物。至元二十九年三十九岁的他出任济南总管同知府事。在奔走南北执行公务之余,他收集了大量的古代书画珍品。周密《云烟过眼录》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书法方面他收有《虞永兴枕卧帖》、《李北海葛粉帖》、《颜鲁公岂米帖》、《米海岳书宝章待访录》等。绘画则有王维、李思训、韩干、韩混、周昉、李成、黄荃、王诜、宋徽宗、李公麟、徐熙等多人的作品。这之外还收集到了著名的《独孤本定武兰亭》、《静心本定武兰亭》。而且他还关注北方收藏家对三代古器图谱和款识的收藏。这不但保护了经典的文化遗存,还为他在书画方面的成就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二。重视教育。赵孟頫在济南任上时,“为政常以兴学为务”。《元史口赵孟頫列传》载:“济南城东有膏腴田八顷,两家相争,数十年不决。孟頫判为赡学田。夜出巡察,闻读书声,往往削其柱而记之,次日,派人赠酒免慰,能文之人,亦必加褒美。三十年后该地俊杰之士,号为天下之冠。”第三,仁宗即位之后推行科举制度,也是在赵孟頫的极力谏言下促成的。关于提携后辈方面赵孟頫做出的努力更多。比如,他以成宗招写《藏经》的机会,向成宗举荐了二十余位善书者。据杨载《赵公形状》所记:“成宗皇帝……召金书《藏经》,许举能书者自随。书毕,所举廿余人,皆受赐得官。”这二十多人中著名的有:方回、邓文原、余寿之、丘子正等等。方回认为赵孟頫举荐它们入宫有“借此进贤培邦基”的目的。元代久废科举,儒士无以报国。通过文艺入仕,似乎更是他们希望通过汉文化来改造蒙古统治者的共识,也反映出他们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而以“文艺入仕”的方式,显然又是出于赵孟頫有意为之的引领。再如,仁宗朝上,赵孟頫认识到自己年事已高,便加大了提携后辈的力度,希望年轻一代实践自己的主张,并继续完成文化传承的使命。当时在大都的虞集、柯九思、朱德润、杨载、张雨等都受到过赵孟頫的教诲。
从上述赵孟頫的种种行为来看,他的“出仕”不但不能等同于“失节”,反而成为他传薪文化的重要条件。试想,如果没有赵孟頫在元代早期统治者中的作用,中国文化在那个时期很可能出现断层和扭曲,他作为“自知的文化传薪者”,功不可没。而仅仅以政治行为来判断历史人物的功绩,失之偏颇。
二、“复古”与“开新”
中国文化的极大包容性使她具有了超强的生命力,任何文化都会在她的中和状态下(有时是一种强势)被同化。另一方面,她固有的追本溯源的特征又使她不断地回归自我,形成源流俱存、纲目突显的统一整体。源头的不断明晰、流派的逐渐衍生,使中国文化在一个长恒性的过程中运行着自我的轨迹。正如国人对传统经典的再理解和不断的加注脚一样。当代提出的“大国学观”,其实就是一个大融合的整体文化观,她“来者不拒”又渊澄流明,让中国文化无限地延续下去。
艺术同整体文化一样也有着自我方式的循环,集中的表现就是某一历史时期对前代经典艺术理念和审美精神的反观和再认同,多数的情形是对“近世”的不满和鄙夷。元代的艺术正是这种历史时期的典型体现。而放之于执行者的角度来说,领军人物还是赵孟頫。要强调的是,“反观”的目的不等同于“复古”。“古”本身也是不可能复得来的。因为人们所处历史时期的理念、习惯、行为都会打上当代的烙印。如果“古意”还在,又有什么必要去“复”呢?所以说,“古意”是永远也回不到现代的。其实,“复古”的终极目标是“新”,是在“追求古意”理念下的价值再造和“重新洗牌”。元代的具体表现便是对“高古”的回溯和“文人意趣”的深化。这种说法与当代经常探讨的“传承与创新”很相似,但更加细微一些。好像磁石的两极,相互分离,又相互吸引,是典型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恼人探索。如果将赵孟頫的“复古”实践用一个词来概括,更准确一些地说,应该是“借古开新”。
不过,偏见总是有的,世人因赵孟頫“出仕胡元”的行为而一再地贬低他的艺术,最为突出的人物便是傅山。他初学书时是从赵入手的,明亡后,痛于国破家亡,于是一反过去,称“薄其人,痛恶其书浅俗”。然而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赵确是用心于王右军者”,甚至在书写这段文字时,傅山仍用的是赵体。傅山对赵孟頫的认知,到晚年又有了相当大的转变。他的《秉烛》诗中说:“秉烛起长叹,奇人想断肠。赵斯真足异,管婢亦非常。醉其酒犹酒,老来狂更狂。砧轮余一笔,何处发文章?”诗中赵、管相对,即指赵氏夫妇。而“想断肠”、“奇人”、“异”、“非常”等一连串的词语,充满着对赵氏夫妇的钦佩心理。诗中反映晚年的傅山已从明王朝的覆灭中清醒过来,而欲效仿赵孟頫,把自己的理想抱负寄托于笔端。傅山对于赵孟頫的认识变化也是另一代遗民的矛盾心理状态。我们不能用政治现象去衡量艺术行为,二者虽然有一定的关联,但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单向互选。高亢是美,凄凉也是美;清雅是品,富丽也是格。这要看审美的主客体在哪个角度上合拍了,更何况还有“绘者笔下未必有,观者心中未必无”的非预见性状况。所以“薄其人遂薄其书”的主观臆断不能消磨一位艺术家的真实成就。更重要的是,赵孟頫用主动性的艺术选择来抗衡和匡正“流俗”所带来的文化偏差,使中国的书画实践有了一个“自省”的机会。“人品不等于艺品”,在当代社会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如果说“文化品味的高低左右艺术品格的优劣”则更确切一些。赵孟頫用“中和”的文化品味去改造元代的艺坛,为我们启迪了一个很好的诠释“传承”与“创新”的时代、一个足可为后世借鉴的时代。
唐宋绘画的意趣在于以文学化造境,而元以后的绘画趣味更多地体现在书法化的写意上,赵孟頫无疑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的那首“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他人能解此,须知书画本来同”的著名诗篇中体现出的理念,已不是文人画运动在舆论上的准备,而是用成功的艺术实践开启了新的绘画领域。
赵孟頫的突出艺术成就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他提出“作画贵有古意”的口号,扭转了北宋以后古风渐湮的画坛趋势,使绘画从工艳锁细之风转向质朴自然。二是他提出“云山为师”的口号,强调了画家的写实基本功与实践技巧,克服“墨戏”的陋习。三是他提出“书画本来同”的口号,以书入画,使绘画的文人气质更为浓烈,韵味变化增强。四是他提出“不假丹青,何以写远愁”的口号,以画寄意,使绘画的内在功能得到深化,涵盖更为广泛。五是他在南北一统、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政治形势下,吸收南北绘画之长,复兴中原传统画艺,并使其发展。
最后要说明的是,我们研究赵孟頫也是传承文化、传承艺术的表现,是文化传薪意义上的再链接。今天的我们想成为赵孟頫的粉丝非常容易,但要想成为他的知己实属难事。只有在认定他“文化传薪者”身份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正视他的艺术和行为。今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大多诉诸于外部力量,而古人则注重的是内心的反观,从内在去解放自我,这便是文化人格所起的作用,也是让文人生存下去的内在动力。我们也应该学会以反观的态度去获得“自知”,进而来明智地选择自我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