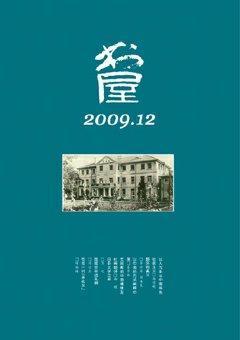艾思柯的中国情缘及杜甫翻译
郝 稷
一
1946年春天,芝加哥大学附近的梧桐居里,历史学家宓亨利(Harley Arnsworth Acnair)正在专注地写着信:
难道她不是一个神圣般的女人吗?她甜甜的笑优美的嗓音和温馨的体贴,她流光溢彩的心灵,她对每个人和每件事的兴趣与关注,她的实践能力……所有的这些以及其他无数的能力和成就使她成为我多年以来所称之的无与伦比的女人。
宓亨利心中这个“无与伦比的女人”就是弗洛伦思·艾思柯(Florence Wheelock Ayscough),在将自己的著作赠送别人的时候,她经常会在书上签上她的中文名字“爱诗客”(Love Poetry Sojourner),并附上一些具有意义的引言。婚前,艾思柯送给宓亨利的《松花笺》上便有这样的话:“要理解中国的问题,我们必须首先知道一些在白人闯入以前的中国历史和文化。”事实上在这一方面,艾思柯终其一生身体力行,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文章和专著,为西方进一步了解中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爱诗客”这个名字是她一生最好的注脚。
仿佛冥冥之中早已注定,从她生命的一开始,便体现出东、西方界限的跨越,她是一个天生的文化使者。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艾思柯出生于中国上海,父亲是加拿大商人,母亲是美国人,她早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和波士顿度过的,婚后她又来到中国生活,在第一任丈夫去世后,她最终与宓亨利结合。多年以后,宓亨利在致友人的信中仍然非常清晰地描述了他与艾思柯最初相识的那一刻:1916年秋天的那个午后,阳光很好,宓亨利为了研究的需要来到皇家亚洲协会图书馆查阅资料。他刚刚站在图书馆的门口,门便打开了,在此工作的艾思柯带着微笑出现在他的眼前。在婚前的那段日子里,宓亨利最愉快的时光是在艾思柯位于上海的居所里度过的。他们经常一起喝下午茶,谈论中国文化。与大多数在上海的美国人不一样,艾思柯的下午茶是非常简单的,仅有几片薄薄的涂着黄油的面包片或是蛋糕。对她而言,喝茶为朋友之间的相互交流提供了理想的场合,因此她更为注重茶给人带来的精神愉悦。艾思柯非常热衷于中国的传统习俗。有一年的除夕夜,艾思柯邀请宓亨利去她家吃晚餐,并且在那里参加送灶神的活动。晚餐后,艾思柯和宓亨利以及其他的客人走进厨房,将灶神从灶台上请下,走到前面的庭院,将灶神放在一个特别制作的纸飞机上——艾思柯觉得乘坐飞机可以让灶神提前赶到天庭汇报,从而不至于淹没在使用传统交通工具而后来的其他成千上万的汇报者中间。
也许是长期受中国文化的不断熏陶和感染,艾思柯的性格也颇具“士”的风范,从容镇定,洒脱有致。1927年早春的一个下午,上海法国俱乐部里,艾思柯正在用法语进行有关中国园林的讲座。忽然传来一声炮弹划过的声音,紧接着消防车的声音大作,在场的很多听众都慌忙撤离。艾思柯没有动,她静静地站在原来的位置,过了几分钟后,以异常安详而宁静的口气向在场的人们征询,是否愿意让她继续讲下去。在征得同意后,她又继续进行演讲。几分钟后,又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而且这次他们所在的房屋也为之动摇,现场顿时一片骚乱。艾思柯依旧静静地站在桌子边,等待骚乱稍稍平息后,再次平静地询问是否能够继续进行她的讲座。她的平静和从容极大震撼了在场的一些法国人,在他们表示了继续聆听的兴趣之后,艾思柯最终完成了这次讲演。
二
从“爱诗客”的名称中,我们可以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她对中国诗歌的挚爱。一个爱诗的女子,不仅自己在其中流连忘返,而且还用她的爱带着中国诗歌旅行,进入了异域视野,让中国诗歌的流光溢彩荡漾于英语世界之中。1917年秋天,艾思柯将大量中国字画带回美国展览,并拜访了她孩提时期的玩伴、也是当时的意象派女诗人艾米·洛厄尔(Amy Lowell)。洛厄尔对这些艺术作品特别是画上的题诗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在一遍又一遍的仔细端详后,一个新奇的天地逐渐浮现出来,最后她们决定以合作的形式对中国诗歌进行翻译。由于艾思柯不久即返回中国,两人只能主要通过书信的形式进行沟通。她们的翻译方法也独具特色,实行分工协作,充分发挥了她们各自的优势。作为汉学家的艾思柯写出一首诗中每个字的字面意思,并完成对每个汉字予以注音和释义等工作,而在此基础上,将其以英诗的形式译出。经过四年左右的不懈坚持和努力,1921年两位女士合力完成的中国诗歌选译集《松花笺》在美国出版,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后来还被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
在艾思柯的中国情缘里,杜甫是她痴迷一生的诗人。在那个年代的英语世界里,能够理解、欣赏杜甫诗歌的人寥若晨星,庞德(Ezra Pound)的《神州集》让李白的名字在异域响彻云霄,可是诗圣杜甫和他的诗歌却还是少有人知,依旧是“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然而真正爱诗和懂诗的人不能不欣赏杜甫,“爱诗客”成了诗圣千年以后的异域知音,对杜甫及其诗歌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和介绍,有力促进了杜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在《松花笺》的准备阶段,艾思柯就已经表现出对杜甫诗歌的强烈热爱。尽管她和洛厄尔基于多种考虑,认为《松花笺》的重点应放在李白身上,但是在她和洛厄尔的私人通信中,艾思柯经常向洛厄儿倾诉她对杜甫的喜爱,甚至明确表明在很多方面她对杜甫诗歌的喜爱胜过了李白的诗歌。《松花笺》以唐诗为主,其中选译了十四首杜甫诗歌,数量上仅次于李白的诗歌,而且该书的介绍部分明确强调了杜甫作为中国人心目中最伟大诗人的身份,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艾思柯对杜甫的钦慕有关。
面对杜甫诗歌如痴如醉的艾思柯,洛厄尔也受到了感染,于是在《松花笺》快要完成的时候,她们计划在以后继续合作,出版一本介绍杜甫及其诗歌的专著,让英语世界的读者得以体验这位中国最伟大诗人的魅力之所在。洛厄尔在1922年2月16日写给艾思柯的信中曾经激动地说:“我现在毫无保留地告诉每个人,我们正在写一本关于杜甫的书。我并不是说我在报纸上发布了这一点,而是我已经亲口告诉了每个人,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情。”《松花笺》出版以后,洛厄尔便忙于为济慈作传,暂时无暇顾及杜甫的译介,不过她依旧对此予以关注。在1922年12月7日的信中,洛厄尔再度问起艾思柯有关杜甫翻译的事宜,并希望艾思柯不要进行得太快,因为洛厄尔觉得等她忙完为济慈作传的事情后会非常累,需要一个很长的假期进行休息,然后才能进行杜甫诗歌的翻译工作。艾思柯在完成《松花笺》后将全部热情和精力投入杜甫诗歌中。在1923年1月26日,艾思柯在上海给洛厄尔写的信中提到她希望能够有时间对杨伦《杜诗镜诠》中所有的一千余首杜诗进行翻译和注解,从而使英语读者能够对杜甫的人生有较好的认识,同时她还迫不及待地告诉洛厄尔她已经按年代顺序翻译了三百七十六首杜诗。
不幸的是,在杜甫诗歌的翻译上,我们最终没能再次看到两位女士的联袂之作。1925年洛厄尔患病逝世,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艾思柯并没有完全放弃原来的计划,而是决定由自己独力来完成这项工作。1929年她成功出版《杜甫:一个中国诗人的自传》(Tu Fu: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Poet),从杜甫的童年一直介绍到他的中年,其中包括大量的杜诗翻译。再经过数年的努力,艾思柯在1934年又推出了《一个中国诗人之旅:杜甫,江湖客》(Travels of a Chinese Poet:Tu Fu,Guest of River and Lakes),重点介绍杜甫晚年的生活和诗歌,从而完成了英语世界中第一部较为详细、系统的关于杜甫生命历程和诗歌介绍的专著。杜甫的诗歌一向被视为具有较高的历史参考价值,孟棨《本事诗》中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而清代浦起龙的《读杜心解》曾称:“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除了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广阔的社会画卷以外,杜诗中也包含着大量有关其本人生活经历的信息。因此艾思柯决定在其著作中用杜甫的诗歌来重构诗人的一生,让他自己的诗歌来讲述他的故事。
由于洛厄尔的去世,艾思柯意识到她不可能像洛厄尔一样对中国诗采取一种非押韵的节奏式诗体呈现,同时经过多次试验后,她发现自己更关注的是:诗人说了什么?他是如何述说的?如何使诗歌被英语读者所理解?最终她决定摒弃书写习惯性英语的思路,而是集中精力将每个表意文字及其在语境下的内蕴呈现出来,因为她认为很难使用一个英语单词去翻译一个为复合体的汉字。有一次,在她正绞尽脑汁地要将一个汉字译成一个英语单词的时候,她的中文老师朱龙(音译)提醒她:“为什么你要费力去寻找一个单词?这个汉字是由三个字构成的。”其实这种拆字法(或字根法)的翻译方式早在她与洛厄尔合作时就已经出现了。在她们一同阅读中国诗歌的时候,洛厄尔惊讶地发现在很多情况下经由一个短语而非一个字来对一个汉字进行分析将会使整个句子的意义更为生动鲜明。发现的过程也有些偶然:在她们读诗的过程中,艾思柯大声朗读了“暮”字并向洛厄尔解释这个字的意思为“sunset”(日落),接着她又不经意地补充说这个字显示了太阳在地平线边际的长草之中逐渐消失。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不懂中文的洛厄尔一听之下,立即要求艾思柯给她讲述有关中国字构成的知识,而这一话题也恰恰是艾思柯平常感兴趣的,只不过她以前从未想过将其运用到翻译上来。在《松花笺》中的翻译中,这种字根法已经初现端倪。在《松花笺》的介绍部分中对她们所用的拆字法进行了一些说明。艾思柯指出,汉字在中国诗歌的创作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书法与诗歌在中国人心目中通常有着紧密联系。由于汉字最早是一种象形文字,笔画的奇妙组合实际上是复杂思想的单独的图画呈现。复杂的汉字在构造上并非一气呵成,而是由简单的字组合而成,这些简单的字都有着各自的意义和用法。当它们组合起来时,每一个在修饰复杂汉字的意义或声音上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同时又都屈从于整体的结果和最终的意义,形成整体的和谐。由于汉字是完整的概念,那么通过具有精确含义的特殊字能够很方便地表达这些完整的概念。
在后来杜甫诗歌的翻译中,艾思柯沿袭了这一做法,并在第一册《杜甫:一个中国诗人的自传》的前言中举了一个例子,即《夜宴左家庄》第一句“风林纤月落”的翻译。她首先用英文给出了每个字的意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纤”字的翻译上,艾思柯根据字典发现它除了有“纤细”这一较为通常的意义以外,还可以指白经黑纬的丝织物,因此将其作为该字的字源意义并翻译为“a silk woven with a white warp and a black weft”。这样,在艾思柯的眼里这句诗的意思就成了“风将树影与落月织成白经黑纬的图案”,而且她认为杜甫用来形容月色的美妙比喻是不应当在翻译中省略的,这也是她将“纤”字进行特殊翻译的意图所在。这一翻译固然颇具想象力,然而由于明显偏离了原诗句的意思,受到了洪业(William Hung)先生的质疑和驳斥。
此外在单个汉字的翻译上,她还倾向于通过对一个汉字的分析而使其固有之义更为鲜明的做法。比如“虐”字,《说文解字》中解释为“从虍,虎足反爪人也”,艾思柯注意到了这个字是由虎和爪两个部分构成,因此就译为“the tigers claws of oppression”,从而形象突出了“虐”字所包含的残暴与欺压。而对于一些惯用的复合词,艾思柯会采取“陌生化”的原则以追求更好的效果,即进行逐字翻译而不是对其通常的意义进行翻译。比如“消息”一词中的“消”字是“to eliminate,transpire”,而“息”字是“a full breath,agasp,to breathe”,艾思柯觉得这个词传达了一种“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仿佛通过呼吸一样”的概念,因此将其翻译为“the breath of news”。
传统中国诗中频频出现的典故一向是翻译者的梦魇,特别是对于被誉为“无一字无来处”的杜诗,如何在翻译中处理典故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艾思柯认为,由于有关杜诗的注解非常清晰详尽,用英语翻译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困难,但是这样做会使诗句淹没于长篇累牍的注释中,很难吸引西方读者。因此她在翻译中对典故进行了淡化处理,有的时候甚至因为典故过多而对某些诗句不予翻译。例如,在翻译《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滥堤防之患,薄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一诗时,艾思柯并没有翻译该诗的最后四句“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却倚天涯钓,犹能掣巨鳌”,因为没有冗长的注解这些句子里的典故是难以理解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艾思柯没有意识到典故在杜诗中的价值与作用,在书中她一再重申杜诗在典故运用上超乎寻常的技巧,而且诗歌本身的活力并没有为此削弱。
艾思柯对杜诗翻译关注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杜甫的诗歌来书写其生命历程,彰显杜甫的人格与个性。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就必须对诗歌的系年有比较准确的把握。艾思柯选用了以精简著称的杨伦的杜诗编年诗集《杜诗镜铨》作为她翻译的底本,这一选择无疑是非常明智的。洪业在对比冯赞克博士(Erwin von Zach)的杜诗德译和艾思柯的杜诗英译时也曾经指出,在原诗版本的选择上前者要比后者逊色得多。
其次,杜甫的诗歌有一千四百余首,作为译者是应该全部翻译还是选取部分予以翻译呢?翻译全部杜甫诗歌不仅工程浩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显得比较琐碎,不利于实现艾思柯的既定目标,为此她倾向于选择那些有助于呈现杜甫整体生命历程和重要生活片段的诗作。《杜甫:一个中国诗人的自传》分为《童戏时代》、《弱冠时代》、《壮游时代》和《中年时代》,描述了杜甫从公元713年到759年离开华州这段时期的生活经历;《一个中国诗人之旅:杜甫,江湖客》从公元759年开始到770年杜甫去世,勾勒出晚年的杜甫生活。虽然第一册与第二册的出版时隔数年,它们之间还是有着很强的连续性,在翻译策略上也保持了一致。这两册书一共翻译了四百七十余首杜诗,使杜甫的一生在其诗歌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同时她还围绕着诗歌进行适当的解释,并补充了一定的历史背景知识来帮助西方读者理解杜诗。
三
作为一个女人,艾思柯对杜甫的迷恋是非常少见的,不仅表现在杜甫的译介上,还体现在她的生活中。现今中国有几处杜甫草堂,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成都的草堂。但是本世纪上半期还有一处鲜为人知的草堂,那就是艾思柯位于上海黄浦江畔的居所。她不仅以草堂命名自己的居处,而且还曾经和宓亨利一同沿着杜甫的足迹旅行。有趣的是,她和宓亨利的结合也与杜甫有关。1929年9月艾思柯送给宓亨利她的新作《杜甫:一个中国诗人的自传》,成为后来宓亨利私人图书馆里最为珍贵的书籍之一。艾思柯在那本书上还写下一句杜诗“自可持旌麾”作为赠言,这让后来回顾过去的宓亨利觉得它是他和艾思柯婚姻的预言。1934年9月7日,宓亨利又收到了艾思柯送给他的另一本书《一个中国诗人之旅:杜甫,江湖客》。一年后的9月,他们结合了。
艾思柯逝世后,时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胡适曾给她的丈夫宓亨利发去唁电,指出在艾思柯一生所致力于的向西方阐释中国诗歌的事业中,她对杜甫诗歌的系统翻译是有助于西方了解中国的最大贡献之所在。
除了文学以外,艾思柯对于中国历史、社会和宗教等其他领域也有广泛的涉猎,同时还积极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在中国的人道主义救济。1942年4月24日,她结束了人世间丰富多彩的生活,踏上了天堂之路。在她的墓碑上,宓亨利选取了她翻译的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的句子作为铭文:“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