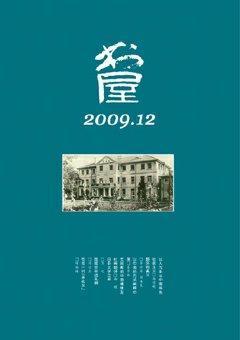题外有真义
李泽厚 刘再复
老庄哲学与海德格尔的根本区别
刘再复(以下简称“刘”):前次到台湾城市大学“客座”,我又讲了《道德经》。海德格尔晚年非常崇拜老子,他追寻存在的意义,而老子仿佛就是存在本身。海德格尔重新发现荷尔德林,把荷尔德林的“诗意栖居”(“人类应当诗意地栖居于地球之上”)看作存在的目的,而老子的存在方式和他的思想似乎正是一种诗意存在的范例,他拒绝被知识所异化,主张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也就是守持生命的本真状态,这正是诗意的源泉。
李泽厚(以下简称“李”):海德格尔的确喜欢过老子,现在已出版了好些探讨海德格尔与老庄哲学的关系的书和文章,认为两者有共同点。但《道德经》一书很复杂,从作者、时代和内容上讲都如此。除了有回归婴儿的内容,也有来自兵家、走向法家(韩非)的一面,现在较多探讨海德格尔与老子的相同点,但没有重视他们的根本区别。我认为两者区别很大,老子即使包括兵家、法家的主动行动因素,基本上是静观性的,但海德格尔则充满行动性。海德格尔哲学我曾称之为士兵的哲学,是向前冲锋、向前行动的哲学,当时我还不知道“二战”时在德国士兵的尸体中发现好些人带有海德格尔的哲学著作。
刘:以前倒是没有人这么说过。老子的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确实是纯粹形而上的思索,是心灵指向,不是行动,但它也影响人的行为和人生的根本选择。复归于朴,不仅是复归于朴素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回归质朴的内心,是精神活动。海德格尔很厉害,他道破了存在的意义只有在死亡面前才能充分敞开,这就调动了士兵的生命激情,在战地上与死神共舞,你称为士兵的哲学很有意思。有人称老子的《道德经》为兵书,但老子只是说明自己对战争的态度和一部分用兵的策略,非常冷静,没有海德格尔的激情。
李:海德格尔确实厉害,他强调人出世后一面踏进人生,一面进入死亡。“此在”的要义就在每一时刻都能感受死亡与接近死亡,这才是真实地活着。
刘:也就是说,我们生命的每一瞬间既是活着,但又是和死亡相关。
李:海德格尔通过死亡来规定生的意义,所以我说他的哲学公式与孔子相反,孔子是“未知生,焉知死”,而海德格尔则是“未知死,焉知生”。
刘:你很早就说过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两人,你喜欢海德格尔的哲学,但不喜欢海德格尔的为人。相反,你喜欢维特根斯坦的为人(但对他那自负和怪异脾气并不喜欢),但不喜欢他的哲学。海德格尔在二战时是纳粹党员,在大黑暗时期,还充当希特勒治下的大学校长,完全被纳粹所利用。
李:海德格尔被纳粹利用去做校长,在政治上自觉地拥戴希特勒,这是没有疑问的,但这还是表层的方面,更深层的是海德格尔哲学本身的问题。他的哲学充满生命激情,有吸引力却有问题。包括整个德国哲学的一脉,都有毛病,可惜中国学人一直不注意,没人讲。康德之后,费希特、黑格尔、谢林等一直到海德格尔,舍弃康德的自由主义,强调总体、强调国家、强调主权,他们的理想是超个人的理性,如黑格尔把普鲁士王国看成是绝对精神的体现等等。在康德的体系里,是人权大于主权,后来则是主权大于人权,以致导向了希特勒种族社会主义的产生。德国出现纳粹,从某种思想史意义说,正是从谢林到海德格尔的结果,并非全是偶然。卢卡奇《理性的毁灭》讲了这个问题,可惜文体和内容都像大字报,没有好好分析,缺乏学术价值。总之,将超个体生存的理性或非理性当作最终的实在或个体,都是非常危险的。
刘:现在那么多人谈论海德格尔,却没有指出他和德国哲学的这一危险性,难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你就主张返回康德,所谓返回康德,便是回到个人,回到“人权”,回到自由的可能;八十年代重新讲“启蒙”,你讲康德,便是启蒙重新肯定个体价值,重新肯定人的生命权利与自由选择。康德讲主体性,是个体生命才是最终目的的主体性,并非国家主体性、民族主体性。
李:现在时行的后现代主义,反理性、反启蒙,最后走入强调国家、强调集体,又是新一轮的主权大于人权的民族主义。在国家开始强大的时候,这很危险,其实对中国前途很不利。所以我重提“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第一次提出(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强调个体(反对黑格尔的总体)和感性(反对黑格尔的理性),这次是强调普遍性(反黑格尔的特殊性)和理想性(反黑格尔的现实性)。当然两次又是相通和一致的,都有所针对,有感而发。
刘:你说海德格尔强调集体,强调国家,可是他非常喜欢荷尔德林。而荷尔德林的生命状态则是隐居的、远离国家的个人状态。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推崇,实际上是肯定荷尔德林的生命本真状态,这是非共在的个体存在状态。
李:海德格尔所讲的真实存在,有这一面。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面,就是他对生存的执著,对明天的悲情与盲目行动,我说他的哲学是士兵哲学正是指这一面。这种哲学提示你,人必然要死,面对这一未定的必然,人要赶快行动,要自己抉择,要决断未来,这才是真实的存在。日常生活、常人的习惯,那是非本真的存在,只有摆脱平常的生活去行动,去把握未来才是本真的生活,才是真实的存在,这一点与老子、庄子特别是禅宗完全不同。尽管海德格尔说禅宗(铃木大拙之介绍)所说正是他要说的。
刘:海德格尔的哲学的确很丰富复杂,仅仅是“存在”这个概念,就不是用几句话可以阐释清楚的。这是一个巨大的概念,他自己也不断定义,就像加缪,一面创造荒诞文学,一面不断定义“荒诞”。我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总是沉浸在生命的激情中,而且只关注其中关于摆脱常人的编排纠缠,回归生命本真状态,不太注意你所说的士兵哲学盲目性的一面。
李:危险恰恰在盲目性的一面。“存在”这个大概念在海德格尔那里到底是什么,众说纷纭,包括海德格尔自己也未说清楚过,它好像很抽象,我以为在海德格尔那里,实际上并非纯精神性而是带有巨大的物质性。当甩开一切所谓“非本真”的生活,存在成了一个大空洞的时候,它就要求物质来具体填充,存在便成了危险的深渊。海德格尔哲学在“二战”时,就导致了纳粹填补深渊的合理性。物质上升为虚空,此在的生命激情成了罔顾一切只奉命前冲的士兵的牺牲激情和动力。没有东西填补,就只要用希特勒来填补了。
刘:海德格尔是现代哲学,但他似乎并不支持现代化,也不支持现代民主理念,倒支持了以主权为核心的民族帝国主义理念。
李:不错,海德格尔是反对现代化的,他支持纳粹。希特勒反对资本主义,以国家、种族、集体名义扼杀个人。海德格尔的士兵哲学,充满个体献身国家、集体的激情,貌似强调个体,其实不然。尼采也是这样,尼采把自我膨胀得太厉害。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国内追随西方,到处都是一片吹捧尼采的声音。
刘: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以膨胀的自我即超人的神话取代上帝,结果二十世纪产生无数的小尼采,都以为自己是创世者、救世主,过去的一切价值等于零,现在的一切从零开始,从我开始。二十世纪无休止的艺术革命,无休止的颠覆、打倒、取代,都受到尼采的影响。尼采为二十世纪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地狱,这就是自我的地狱。
李:叔本华、纳粹都讲意志论,但我宁要叔本华,也不要尼采。
刘:一个是消极意志论、悲观意志论,一个是积极意志论,权力意志论,为什么你喜欢前者?
李:叔本华与尼采都回到感性,探究活人的生存,所谓意志,就是人要生存的意志,就是求生欲望,他们都反对康德的纯粹理念,当然也反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但纳粹与叔本华的哲学方向不同,叔本华主张消灭意志才能沉静下来,意志太张扬,就会发疯。
刘:尼采自己最后发疯了,希特勒也发疯了。二十世纪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庞大疯人院,都是权力意志论的表象。叔本华喜欢佛教、佛教哲学,也是消极意志论,也是要消灭欲望,消灭意志。我认为,老子、庄子所崇尚的自然,其对立项就是意志,消解意志欲望,便走向自然。王国维借用叔本华的消极意志论解释《红楼梦》并不牵强,他找到一些对应点,其中最关键的是指出人的欲望无法消解便造成普遍性悲剧。《红楼梦》中的男人除了贾宝玉,都太张扬意志,或为功名意志,或为权力意志,或为财富意志,各种色欲都是意志的显现,空则是意志的消解。
李:艺术包括文学,便是让生存意志休息一下,放松一下,在欣赏时放下意志欲望,进入自由境地。消极意志论一旦进入审美领域,倒是变得很积极。我记得爱因斯坦、维特根斯坦都比较喜欢叔本华。
刘:你的哲学有一种彻底性,想清楚了,想透了,一旦道来,便格外明确。刚才你谈起积极意志论与消极意志论,使我想起对存在论似乎也可以作这样的划分。海德格尔一方面向往荷尔德林,向往生命本真状态,可视为消极存在论,即消解冲锋意志的存在论;海德格尔的另一面,也就是带着牺牲意志创造明天的士兵哲学,则可称为积极存在论,两者都想摆脱人的日常生活状态,追求真实的存在,追求栖居的诗意。我当然是选择前者。不知道是否可作这样的区分?
李:对所谓积极意志论与消极意志论,我研究得很少,无法多说。
刘:叔本华讲意志论,王国维用它来解释《红楼梦》,我现在则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来解释《红楼梦》,这部小说在精神层面上,探讨的正是一群通灵的生命来到地球走一回以后,提出为什么要来这一回,来了要什么?在地球上走一遭、活一回意义何在?既然来了,该怎么生活?是靠近以少女为主体的净水世界,还是靠近以男人为主体的泥浊水世界?
李:从这个角度来观赏《红楼梦》很有意思。《红楼梦》问题确实是为什么活,怎样活等存在问题,而不是反封建这类意识形态或一般男女爱情之类的问题。
刘:过几个月我将到台湾中央大学,准备也讲讲《红楼梦》哲学。我发现曹雪芹的哲学思想正是与海德格尔相通,他一再强调,人必死,席必散,好必了,他让妙玉说出范成大的诗句:“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即使你是千年的豪门贵族、帝王将相,终归要面对一个“坟墓”(土馒头),不管你是怎样的角色,终归要变成一具骷髅(“风月宝鉴”),也不管你怎样“千里搭长棚”,终归有个席散的时候。曹雪芹正是面对死亡思考人生,面对这个“未定的必然”,他才觉得不应当在短暂的人生中为了那些功名利禄而争得头破血流,才看出“唯有金银忘不了”的荒诞,才有“好了歌”。曹雪芹的哲学与老子、海德格尔相通之处还有一点就是他也认定,唯有守持生命的本真状态,活着才有诗意。
沟口雄三亚洲表述的质疑
刘:2006年5月我受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加加美光行教授的邀请,去参加他们的年度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由沟口雄三教授主讲,由我和张琢、张梦阳、金观涛、刘青峰和其他日本教授对话。沟口雄三教授讲述的主题仍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态度与方法问题,与他过去发表的文章、著作的基本点相同,他强调史学家进入问题之前要有自己的立场、态度。其要义是说,对中国近代史的论述应以中国自身为中心,为镜子,不应当把外部的刺激(外来因素)看成主因,没有外来的刺激,中国近代史包括思想史也会按其自身内部的因素而进入现代社会。他所著的中国前近代思想史,以李卓吾为开篇,此次他侧重讲黄宗羲,他认为,如果没有外部因素,中国的思想家也会推动中国走向现代社会。参加会议之前,我把沟口教授的几部中译著作都阅读了,其中还有你的学生赵士林的中译本。沟口雄三先生在他的文章里还提到你,你们是不是见过面?
李:见过多次面,1992年他还邀我和史华慈教授去开过会,对我似乎很客气。
刘:我读了他这些的著作,总的印象是他研究中国近代史,在方法论中有一个根本特点,就是用亚洲表述来代替欧洲表述,以中国镜子来取代欧洲镜子。所谓镜子,就是参照系。他觉得过去用欧洲的参照系来看中国是不公平的,西方学者站在欧洲中心的立场,把中国近代史视为西方国家枪炮推动下的历史,是不公平的。归纳一下,有三个意思:其一是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是内因推动的历史,不是外因推动的历史;其二是对这一历史的评价尺度应该是中国自身制度的尺度,不应是欧洲西方的尺度;其三是以往西方的中国近代史表述只是欧洲表述,而他所作的表述是亚洲表述。
李:日本汉学界的历史研究重资料、重实证,下了许多细致的功夫,其认真态度值得中国学人学习,可惜一般讲来,比较不重视思想。沟口教授是一个特出的例外,但他的思想我不太赞成,我以为他基本上还是在转述柯文(Paul A.Cohen)等人的后现代看法,强调态度、立场、方法,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许多国外汉学家的中国近代史常以明代为起点(如史景迁),不无道理,这就是国内以前讲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它甚至可追溯到北宋。但我仍以为,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各种纷至沓来的外部刺激改变了中国,才真正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刘:不错。我在会上和沟口雄三教授进行了一次质疑性的对话。首先我肯定了沟口教授重视中国内部因素自然发展的线索,过去我国学界在讲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时,忽视了这一点。1988年我在科罗拉大学召开“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提出一个论点,思路与沟口教授接近。我说中国现代小说史及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双线双向”的文学史:第一条线是外国文学刺激下的文学史,这是由欧美留学生与日本留学生创造的,即由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和胡适、冰心、巴金、老舍等创造的历史;一条则是由本国自身的文学语言传统自然演化的历史,这是由刘鹗、苏曼殊、鸳鸯蝴蝶派、张爱玲、张恨水、金庸等构成的历史。前者可称为“外烁新文学史”,后者可称为“本土新文学史”。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介入,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本土传统一脉的文学,也会自成系统,自己汇成江河。但是,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成其现代文学,恰恰是由于外国文学的刺激而获得全新的视角、全新的方法和全新的语言。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主线索的是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胡适、冰心等为骨干的“外烁文学史”一脉,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鲁迅自己就说过,他写《狂人日记》全仰仗阅读一百多篇国外小说和自己的一些医学知识。没有异国文学的刺激,就没有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沟口教授的思维方式是在关注内部线索时否定作为主流的外部线索,这样书写下来的历史只能是片面的、丢掉基本事实的历史。
李:金庸小说讨论会,我也参加了。你以文学的例子说明现代历史的论述方法,我也是支持的,而且即便是苏曼殊、张爱玲也仍然受西方影响很深,刘鹗、张恨水包括金庸倒是更本土一些,但观念和作品内容仍大受西方影响。
刘:我还向沟口教授提出另一条质疑。中国历史发展到十九世纪中叶,如果没有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中国是否可能面对世界现代社会潮流?到了世纪末,如果没有甲午战争失败的大耻辱,中国是否会有巨大的反省而导致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发生?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如果不是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是否会有1949年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都是历史发展中的质变。没有外因,没有外来刺激,是否会产生这些质变?!沟口教授所讲的从李卓吾到黄宗羲的例子,只能说明在没有外力影响下,中国的量变,但这些量变不能构成历史的主脉。在此次会上,我们的好朋友张琢特别支持我的发言和观点,他说,如果没有外部历史的刺激,中国绝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也不是一百年来中国的样子。他又说,如果没有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十月革命的外来刺激,一百个黄宗羲也没有用。张琢仍然是那样锋芒毕露,口无遮拦。
李:黄宗羲的《原君》、《原臣》包含着某些民主思想,所以梁启超曾加以引用发挥,但这种思想的萌芽,与洛克、卢梭、康德等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不同(他们是在确定个体价值前提下的民主思想)。李卓吾肯定“私”、“利”、“欲望”等,与当时礼教败坏的社会风气有关,后来便被同样有着进步思想的王船山大骂。如果不是外来思潮,不是五四运动,李卓吾的思想不可能演变成现代的个人主义、自由思潮。沟口否认外来刺激,否认近代外来力量对中国社会的震荡,这不合乎历史事实。沟口的说法仍然是西方流行的否认进步、否认普遍公认的价值的文化观念,他的亚洲表述实际上是一种相对主义。他否认“欧洲表述”,实际上是否认普世公认的价值,也不承认在人类文明史上,欧洲在近现代确实是个先锋角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所呈现的价值给人类历史带来很大的进步,我一直不赞成后现代主义否定进步的种种说法。沟口是竹内好的学生。竹内好先生是日本的左翼,在政治上一直反对美国反对欧美文化对日本的入侵,沟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反映了日本左翼的立场,对中国革命充满同情,但是不能用某种政治立场来解说历史。
刘:日本的明治维新,其思想前提是肯定欧洲价值的先进性。有了这一前提,才有“脱亚入欧”的大思路,才有日本的近代改革和现代社会。中国近代的变化,也是在外来的刺激下惊醒之后,确认一个思想前提,即确认中国落后了,无论是技术层面、制度层面或文化层面都落后了,有了这一前提,才有这一百年来的不断的反省和改革。
李:前面提到哈佛大学的柯文反对费正清的刺激反应论,提出中国中心论已经二十年,费正清忽视内在因素,把外来刺激说得太绝对,有他的片面性,但柯文、沟口更片面,把中国的内因说得更绝对。我以为比较起来费正清的表述还准确一些。我不愿赶时髦。
刘:柯文写了一部《在中国发现历史》,已译成中文,是部相当有影响的书。我也买了一本。对于柯文这部书的主旨和他的中国研究思想脉络,林同奇教授已写文章作了详细介绍,发表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柯文思想的语境正是针对费正清的中国研究模式。费正清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看法大体上是“外部刺激/反应”的模式,强调外部力量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决定性作用,但对中国内部的相应变革力量估计不足,柯文对此提出问题,提出另一套思路,其要点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心动力不在欧洲,而在中国本身;用我们熟知的语言表达,内因是主要的,外国是次要的。总之,是用中国中心论取代欧洲中心论。
李:从柯文到沟口都是把欧洲表述变为亚洲表述、中国表述,否认人类发展的共同尺度、共同价值。这种思潮很有势头,迷惑了很多人,所以值得注意。柯文、沟口都是沿袭福柯后现代的新历史主义。所谓新历史主义,就是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客观的历史事实,只是如何讲述、如何表述的问题,也就是论述的方法问题。后现代把这看作新发明,其实与毛泽东当年强调“关键在于立场、观点、方法”非常相似,我们这一代很熟,也难怪中外好些后现代学人特别喜欢毛了。
刘:中国近代史最根本的动因还是外来的刺激,因为外来的刺激,才打破中国历史的内部循环。如果不是天演论(进化论)的进入,我们现在可能还以为历史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沟口先生否定外部刺激这个根本,其实,外部刺激是铁铸的事实,我们的研究应先肯定这一事实前提,然后再考察不同文明模式对外部刺激的不同反应,这才能进入问题。例如亚洲三个主要国家:中国、日本、印度,就是三种不同的文明模式。三个国家在十九世纪都经受了西方文明的冲击,但反应很不相同。日本曾是弱势文明,并且有接受汉族文明的历史传统,因此,当他们感到自己落后时,很容易正视自己的落后并很快地接受欧美的强势文明,迅速作出决断,实行改革,他们以“和魂洋才”为中心口号,在接受外部刺激时很少发生冲突。印度和日本相比,更是弱势文明,在西方文明面前他们几乎是全盘接受,近似投降。中国则不同,它一直是强势国家,一直具有中央大国心态。西方文明在自己面前出现后,自己的架子很难放下,本来让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平起平坐已不容易,现在还要承认西方文明比中国文明“先进”,更是难以设想,因此,对于外来刺激,开始便是反抗,不得不面对与接受后,仍然充满焦躁与冲突。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才第一次与强势文明接触,才进入现代历史。这之前,中国都是老大,打交道的都是比自己低一级的弱势文明。中国如果不是西方强势文明的震撼性刺激,就只能按照自己的逻辑缓慢发展,缓慢循环。把重心放在不同文明的不同反应,这种思路也许更贴近历史本来面目。
李:这里还涉及一个偶然与必然的问题。只重内因便忽视了历史有诸多偶然,实际是回到某种宿命论,恰好是后现代的反面。各文明、文化、国家、民族都是在各种错综复杂又难以预料(即偶然)的内外部刺激震荡下兴衰存亡和变化着的。从李卓吾到鲁迅,中间如果没有外来刺激,是不可想象的。
反“反二分法”与“后现代主义”
刘:关于后现代主义,我们以前已作了批评,以致福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我们也比较早就看清他们的弱点。若干年前,我们主要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觉得中国重要的不是需要福柯、德里达解构理性的这一套,中国需要的恰恰是理性,中国刚从乡村时代全面转入城市时代,全面进入现代化,恰恰需要借鉴十八世纪以来的启蒙理性成果,而不是要接受福柯、德里达这套颠覆启蒙成果的“造反”理论。我现在想从福柯、德里达哲学本身的弱点和你继续讨论。
李:后现代主义似乎已经到头了,可中国学人还继续在赶这个已经不时髦的时髦。后现代主义这概念非常宽泛模糊,如果以福柯、德里达为代表,他们的理论有可取之处,例如反对本质主义,反对主、客体的二分法,强调知识被权力渗透和支配,历史讲述主体的立场与态度等等。我们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阅读中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看待历史与现实,不同立场、不同世界观的人对历史和现实会作出不同的阐释,这对了解福柯权力即知识等一套理念就比较容易。福柯尤其是后来的福柯崇尚者走过头了,走得太远了。反对本质化变成不承认任何根本、任何实在、任何价值,只剩下讲述,只剩下文本,只剩下一个无意义的破碎的当下的自我,而这个自我究竟是什么也并不清楚。
刘:福柯本是想在1968年的风暴中用街头政治造反,造反不成,就通过语言颠覆这一基本策略进行造反。他们非常聪明,发明了一种颠覆西方形而上即西方概念体系的解构方法进行造反,企图一举打破西方二百多年来的理性建构。他们的造反不是没有理由的。西方讲了那么长时间的理性,讲现代文明,但是二十世纪上半纪出现两次反理性的世界大战,出现希特勒这种反理性的怪物,于是他们失望了,对理性体系产生怀疑,开始造反。反现代主义、反对本质化,首先就是揭开“绝对真理”、绝对精神的虚妄,对真理采取开放的态度,这是很好的。本质化确实会导致简单化。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几乎天天看到、听到本质化即简单化的口号、文章、社论,非常荒谬。福柯的阐释者确实走过头了,之所以会走过头,是因为他们的理论出发点是造反的,其整个“主义”的基本点只有破坏性,缺少建设性,这是致命的弱点。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哲学家建构那么多伟大的经典,取得那么高的成就,无论是康德、黑格尔还是马克思,你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但不能不承认他们的成就,其原因就是他们的基本点是建设性的。但福柯的解构理论则只是在不断颠覆,最后否定西方理性体系的价值。
李:福柯、德里达等人揭发理性的负面价值有功劳。理性带来的东西的确并不都是好的。各种哲学的理性体系和精神指向不同,带来的影响与后果也不同,康德的主体理性指向个体价值的肯定,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则可能导致集体主义。但福柯等人夸大了理性的危害,他们反理性,反启蒙,反进步。我们要问,启蒙理性所推动的工业文明、科技文明和现代生活文明,其总效果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祸害,哪一方面是主要的?一百年前的人,寿命达到七十岁的很少,现在多数超过七十岁,科学技术的发展、医药卫生事业的进步导致人的寿命增长,这到底好还是不好?“进步”概念是不是可以笼统抛弃?判断理性、非理性、反理性的是非,恐怕还是以有助还是有碍于总体人类的生存延续为最终标准吧。
刘:后现代主义除了反对本质化、反进步观念之外,还特别反对主、客体的二分。他们反对二分法,倒是和我们的老子、庄子、慧能的思想相通。老子的“大制不割”、庄子的“齐物论”、慧能的不二法门,都是反对二分法。老、庄、释都讲整体相,反对分别相。万物一府,生死同状,他们去掉内外之别、尊卑之别、是非之别,确实导致平等观念,导致慈悲。不二法门最后泛化到物我不分、天人不分,也达到对宇宙主体、生命本体的一种把握。我们以往太重二分法,动不动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动不动就是“红五类”、“黑五类”,这种命名与分类,实际上是一种权力运作,二分法导致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教训极深。从本身的经验中我们获得对二分法的警惕,也更容易理解反对二分法的理论意旨。但是,我愈来愈感到,在宗教领域心灵领域讲不二法门,可以讲得通,但在科学领域、社会生活领域不讲二分法,却行不通。所以我们对二分法也需要认真分析一下。
李:我很早就说过,在某些领域中,二分是绝对必要的,否则就乱套,例如今天,在社会生活极为重要的交通领域,红、绿灯的二元区分就绝对必要,否则就会车辆大乱,死伤无数。同样,如果没有正负、增减、上下、左右等等区分,科学技术就会变成不可能。这里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明白,二分法本就是人为的方法,人制造出来的手段,而不是“本体”、“存在”。换句话说,二分法(也包括“本质化”等等),是人为了生存需要所使用的一种方法与手段。宇宙、大自然、万物万有,原来是没有名字的,是不能用概念来规定、描述或二分的。正如老子所说的“道”本是没有名字的,真正的道,是不能命名的。现在命名它为道,已不是真正的道,即与命名者想指涉的那个本来的道已不相符了,已经把它僵硬化、割裂化了。这就是说,人为了生存,为了认识,才命名,才创造各种概念和概念式的方法,包括二分法。二分法出现以后,导致把二分看成是本来的事物本身,看成是宇宙、自然、生命的本来面目,这就错了。其实,宇宙、自然、生命本是不分的,用你的语言说,是整体相,而非分别相。所谓分别相,是人为的分别,是人为了认识整体而使用的方法,如果我们把这种方法固定化,就会失去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列宁依据黑格尔的观点说过,任何概念都是把人的经验僵化,而一旦僵化,就离开了事物的真面目,但人没有概念就没法认识事物,没法进行思维,进行活动。什么都是混沌一团,不可言说,又怎么活?
刘:理性总是讲“分”,神性则不讲分。禅宗追究世界本体、人本性,认定佛性无南北之分,也无优劣之分。每个人身上都有佛性,关键是你自己能否去开掘。慧能主张不立文字,就是不要理会人为的划分,不要理会人为设定的各种概念、命名、分类,直接把握心性本体,直接把握真理。禅宗这套方法是直觉、直观、感悟的方法,是直达事物本体的方法,但其把握是模糊把握,不能言传的把握。而科学理性则要求准确把握、分析把握、实证逻辑把握,这种把握,就离不开二分法了。没有分解、分类、分析,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了。
李:现在“反对二分法”仍很盛行。什么本与末,什么正与邪,什么进步与不进步,什么本质与现象,什么主观与客观,什么真理与谬误,一切界线全都没有了,全看你怎么说,怎么讲述,一切都相对化。现在文化相对主义正在全球学界扩张,由欧美进入亚洲,进入中国,谈追求“真理”变成是一种笑话。这种时尚有某种破除迷信打破成见的功劳,但也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