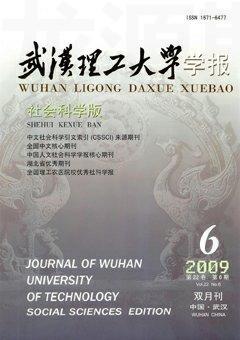儒学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角色
王汉苗 王德成
摘要:儒学虽在近代中国渐逝了官学地位,但还是承担了任何思想替代不了的历史角色:儒学仍然是多数国人的生活准则,民族凝聚力的动力源泉,中华民族脊梁的精神支点以及主要政治学说的思想资源。对儒学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角色的认识,可以为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和利用儒学,服务于现代化建设提供思维的平台。
关键词:儒学;近代中国;历史角色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6.022
在近代中国,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地从西方引进新的思想、主义、学说,如启蒙思想、进化论、实用主义、改良主义等。这些理论对近代中国思想的启蒙和社会的发展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它们却无法实现近代中国人民富国强的愿望,因而,它们最终没有能够在中国的发展中取得重要地位。虽然部分中国人从西方文化的冲击中明确体认到儒学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但也找不出全盘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充足理由来。在这种情况下,儒学仍以顽强的力量支配着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承担了任何思想替代不了的历史角色。
一、儒学依旧是多数国人的生活准则
生活准则是人类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最简单,最起码的社会公德。中国近代社会是动荡转型的社会,人们为了维持公共生活的正常秩序,总是要遵守一些最基本的社会公德来规范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使整个社会生活正常运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古代优秀的知识分子在吸收历史与现实的文明基础之上,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等问题经过长期深入思考而发展起来的,对人们的生存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其发展到中国近代社会时过2 000多年的积淀,已溶汇在中国人的政治思想、道德伦理、民族性格以及风俗习惯里,其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都随时在起着作用。近代中国社会的国情是,在政治上排孔而“在思想上仍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孔子为中心,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1]363。这足以表明,儒学独尊地位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儒学的消灭,也不意味着儒学在社会生活中再也不起什么作用。而恰恰相反,孝敬父母、信用、诚恳,学识与教育,以家庭为中心,廉洁、勤劳、仁爱、修养、民族凝聚力等儒家思想,正是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的人们所需要的。尤其是儒家的孝道思想,在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中已根深蒂固,甚至一些批孔的英雄也难以逾越,比如,鲁迅长期供奉着他母亲赠予的无爱情的婚姻,20年不敢有爱的追求。再如胡适,他曾鼓吹全盘西化,但他也不得不遵循母意,跑回老家与从未见过面的小脚女人结婚。在教育上,人们还是尊孔子为师,比如,1917年11月,毛泽东在主持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学开学仪式上,还向孔子像行三鞠躬礼。他在《夜学日志》中记有:在仪式上,师生员工“整队向国旗、孔圣行三鞠礼,职教、学生相向互行一鞠躬礼”[1]103。这些都说明,儒家的思想并没有随其官学地位的逝去而被人们彻底抛弃,在新的社会公德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儒家思想还是担当着生活准则的角色。即使当时进步思想家们在新公德观的建设中,也没有无视儒家思想所担当的生活准则角色。
由于中国近代社会,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社会公德的建立依然是以家庭为基础,在当时,与之最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是儒家思想,所以近代进步思想家们在新公德观的建设中,还是看中了儒家思想。他们提出了正确而又科学的原则,其基本精神就是既反对复古守旧,又反对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既要批判中国传统道德,又要借鉴吸取西方道德文化。为此,他们都反对建设新道德中照搬西方的错误倾向。孙中山也不赞成形式主义地去对待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他说:“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2]243正是在这样的原则之下,他提出要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孙中山审察了“固有的道德”的社会功用后指出:“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缘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的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2]242。“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2]243。孙中山所强调的“固有道德”,就是儒学所宣扬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以及已从道德范畴发展成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政治哲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孙中山对此十分赞赏:“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2]247这就是说,中国近代社会新道德的建设要吸取儒家思想中的精华,继续担当人们生活准则的角色。其实,时至今日,我们仍遵循着儒家的许多生活准则。
二、儒学是民族凝聚力的动力源泉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由一个主权国家沦落为半殖民地国家。在近代109年时间里,中国遭到了列强六次大规模的侵略: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战争、中日战争。前五次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中国被迫签订了从《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中国被列强割占了157万平方公里土地和掠夺了13亿两赔款白银。危害更大的是,鸦片的大量输入,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体质,损害了中国发展近代经济的潜力,降低了中国人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加剧了社会动荡,使中国近代经济发展难以获得一个稳定的环境;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使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国家,不但原有产业迅速衰落,近代工业也难以顺利成长。但是,中华民族是不甘屈辱的民族,面对列强的侵略,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反抗,表现出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产生了林则徐虎门销烟,三元里抗英,太平天国打击外国洋枪队,刘永福抗击法国侵略军,邓世昌撞击日本军舰,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全民族抗日战争等英雄业绩。虽然前五次反侵略战争都失败了,但展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不屈不挠、大无畏意志精神和英雄气概,以及为维护民族独立,争取国家富强而斗争的民族精神。尤其是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民族凝聚力,是指特定民族的思想整合力量,也就是该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对民族成员的吸引力,以及民族成员对整个民族依恋不舍的向心力。无论民族内部各族系、各阶层之间发生过多么严重的歧异与分裂,只要有优秀文化的传统存在,终究会由离散到聚合,由动荡到稳定,由对立到协作,结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民族。具体地说,民族凝聚力是通过民族的精神、民族的心理、民族的价值取向和人格理想等许多方面体现出来的,它是统摄人心、团结族类的纽带。在中国近代社会达此要求的文化只能是儒家文化。《周易》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3]3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3]13的思想。这种“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延续发展并永远兴旺发达的思想基础,是民族生命的源泉。早在《尚书•禹贡》中,就有天下大一统之义,并热烈赞美大禹统一中国的功绩;孔子作《春秋》,主张“华夷一家”,这一思想经其弟子子夏“四海之内皆兄弟”观念的提升,再经《春秋》公羊学派的倡导,在战国时期加速向“天下大一统”的观念发展。“天下大一统”观念是形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精神的源泉。儒家所强调的宽厚仁慈,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情操与人格,成了激发人们爱国爱民、齐心奋进的力量和人生追求。这也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之一,有利于协调人们的心理和行动,促进社会的发展。儒家经典中还包含着在别的国家里很少见的伦理价值体系: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上,如:“与人为善”,“诚信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在个人自身修养的问题上,如:“志存高远”,“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并且把个人、集体、国家联成一体,例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中华传统美德,在动荡不定的中国近代社会中对于增强民族内聚力,振奋民族精神,整合群体价值,协调社会秩序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正是这种精神使近代中国没有像同时代的其他国家那样沦为西方的完全殖民地或国家的解体——虽军阀割据迭起,但还是形式上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正是这种精神,在中国近代社会推动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也正是这“血浓于水”的亲情思想,使中国近代各种政治势力能够众志成城,以“御侮”思想促成民族团结共同抗日,以“义勇”思想动员群众进行反日武装斗争,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思想鼓励人们为国家民族利益而不惜牺牲自己,以“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思想激发人们在反日斗争中发扬注重人格情操与民族气节精神,使绝大多数民族成员决不屈服,坚持抗争到底,最终取得民族独立。
三、儒学是中华民族脊梁的精神支点
近代中华民族脊梁是指那些为拯救中华民族出离水深火热之地而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的人,他们大多是中国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近代以来,作为国人人生哲学轴心的儒学发生动摇,多数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一时找不到新的共同信仰来填补思想空缺,不知何以安身立命,于是痛苦莫名,不得不四处探索,但是新的民族主体信仰始终建设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在儒家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多数近代知识分子,依旧以儒家的思想为精神支点。
清末维新变法领导人梁启超在维新变法失败后,赴欧考察,写了《欧洲心影录》,将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分析,指出:中国应将传统优秀文化的“国宝”发扬光大,同时,吸取国际文明之精华来扩充中国文明。他引用近代法国著名哲学家柏格森的导师蒲陀罗的话:“你们中国有绝大的责任,就是拿西洋文明来扩充自己的文明,又拿中国的文明补助西洋文明,叫做互相化合的一种新文明。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把本国文明发扬光大。好像子孙继承祖先遗产,要保住他,发扬光大,因为他有民族特质。你们中国确实可爱可敬。我们法国祖宗在蒙昧时期,你们中国已出现了许多哲人。我近来读些中国哲学译本书,总觉得他精深博大。我希望中国人不要失掉这份传家宝才好”[4]35。这足以体现了儒学对梁启超的强大精神支撑。中国现代思想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在“五四”时期指出:“我从那时决定搁置向来要做佛家生活的念头,而来做孔家的生活。……我又看着西洋人可怜,他们当此物质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复,而他们所谓精神又不过希伯来那点东西,左冲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谓未闻大道,我不应当导他们于孔子这条路来吗!我又看见中国人蹈袭西方的浅薄……我不应当导他们于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来吗!无论西洋人从来生活的猥琐狭劣,东方人的荒谬糊涂,都一言以蔽之,可以说他们都未曾尝过人生的真味,我不应当把我看的孔子人生贡献给他们吗!然而西洋人无从寻得孔子,是不必论的,乃至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从为人晓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来做孔家生活的缘故。”[5]这表明儒学促使梁漱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了转变。1924年在广州召开首次国民党代表大会,孙中山在接见中外记者时说“中国有一个正统的思想,自尧、舜、禹而汤、文、武、周公、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的思想来发扬光大的”[6],并且孙中山多次强调,他致力于中国革命,所持三民主义,是承袭了“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孙中山赞扬孔子、孟子是民主政治的倡导者,并且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我国特有的最完备的政治哲学,必须作为“国宝”来捍卫。
即使批孔的中共优秀领导人,也把儒学作为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支点。《礼记•礼运》中提出了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这一理想是把共产主义引入中国的桥梁,是“五四”知识分子所向往的目标。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在构想中国未来社会的时候,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大同思想作为择取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评判标准。陈独秀首先把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他提出要破除“国家偶像”,他说:“我想各国人民若是渐渐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与真正和平的幸福,这个偶像就自然毫无用处。”[7]155他希望中国人“有教育,有知识,有团结力,有资格和各国思想高远的人共同组织世界大同”[7]431。李大钊认为“今日的民主,乃是一步一步向世界大同进行的一个过程,今日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求独立民主,救贫苦大众,而未来理想,乃是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8]。青年毛泽东写道:“大同者,吾人之鹄也。”他希望实现“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的“大同圣域”[1]89。恽代英认为,共产党人要具有孔孟倡导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百姓福祉,必不可自居高大地位,不肯牺牲。郭沫若说,他就是因为信仰儒家的大同理想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两者是相通的。年轻的郭沫若写了《马克思进孔庙》的小品,虚构了马克思向孔子请教的对话,表明双方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小品中表现马克思设想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与孔子设想的“大同”世界不谋而合,马克思最后对孔子说:“我想不到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曾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们中国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9]于是得出结论,要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文化结合起来。郭沫若还说:“我的想法是,在个人修养上可以体验儒家精神,而在社会的兴革上,则应依社会主义的指导,努力吸取科学文明的恩惠,使物质生产力增加,使物质分配平等,使各人的精神得以遂其全面发展。”[10]郭沫若又表示,要发扬孔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为了人民大众,应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概。“在大众未获得发展个性、享受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与自由,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人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11]。抗日战争时郭沫若写过《屈原》剧,宣传爱国主义,他认为屈原是一个爱国儒者。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写的《十批判书》,多方面赞扬孔子儒学。
毛泽东好读古书,经、史、子、集,稗史、笔记,无所不读,对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学颇有研究。他倡议:“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2]因此,他以身作则,常常在讲话、著作中用儒家经典语录来表达自己对问题的看法。以至于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来源是中国传统思想,而非外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少数论者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毛泽东之手已发生了变形,不再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性质。更有甚者则认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封建化”、“儒家化”。这些论点虽有偏颇但也足以说明儒家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之深。
四、儒学是中国近代主要政治学说的思想资源
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政治势力,无论是反动的还是进步的,基于儒学的强大传统力量,在创建自己的政治学说时,都要把儒家思想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
儒学在近现代中国,成了反动统治者复古与镇压革命的有力工具,最典型的是袁世凯利用儒学大搞帝制复辟。北洋军阀制造尊孔读经的逆流,并非单纯为了提倡“尊孔”和“读经”,而是利用孔学的某些主张,为自己复辟和复古的反动政治目的服务。他们凭借儒家的“克己复礼”、“大一统”、“定于一”思想实现其专制独裁和复辟帝制的梦想。更让人气愤的是,袁世凯竞利用孔子的大同思想,为媚敌卖国寻找借口。袁世凯借用《孟子•离娄上》中的“小国师大国”,天下为公为大同的思想,制造“文明无国界”的谬论,实际上是要中国人民切实承认清政府同外国签订的一切卖国的不平等条约,顺从帝国主义的奴役。以上这些说明,他们把儒学的消极作用发挥到了极点,并把儒学融入到封建军阀专制主义与封建买办专制主义政治之中,成为其反动政治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主要是用孔子学说及其传统力量稳定其统治;因为孔子学说本身有利于稳定统治秩序。这是反动势力对儒学的利用,那么批孔的进步势力又怎样呢?
中国近代的民主主义运动中一般都要批孔,但又都离不开儒家传统。众所周知,太平天国时洪秀全曾激烈反孔,但是太平天国“天朝田亩”的理想又部分来源于儒家的“大同”理想,并且太平天国走上被儒家思想消极面吞噬掉(如其等级制度绝不亚于清王朝)的道路。康有为曾为维新变法而抨击儒家纲常名教,但却打着孔子的旗号进行改革,并且最后走上尊孔保皇的旧路。孙中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曾尖锐批判儒教“束缚人心”,要对其“扫除净尽”;但孙中山也吸收了大量儒家思想,并对其进行了部分改造,作为三民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社会主义者是近代中国最彻底的批判儒家糟粕者,同其他革命阶级一样,也逃不出儒家思想这一强大的传统文化的影响,社会主义者既要与儒家封建思想作斗争,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同时,他们又往往在一些问题上借用儒家思想的外壳,找到了某些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如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者就是以儒家的“大同”思想为桥梁来认识与接受它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实行批判继承的正确方针,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既要尊重历史又不颂古非今,既不肯定一切也不否定一切,既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又反对国粹主义。这就使社会主义者与儒学这一重要传统文化,也产生了某些批判继承关系,吸收儒学的优秀部分,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儒学最终成为社会主义者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中国近代进步势力对儒学的这种既批判又脱不开的矛盾情况说明,在中国近代社会,传统儒学虽然在政治上辉煌不再,但其思想在生活中及社会实践上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儒学虽在中国近代社会逝去了官学地位,但并没有因此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中国近代社会发挥着其他思想替代不了的作用,因而在近代中国社会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对儒学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角色的认识,可以为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和利用儒学,使其服务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思维的平台。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2]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1.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9:35.
[5]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20-221.
[6]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M].上海:民智书局,1925:43.
[7]陈独秀.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8]李大钊文集: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625.
[9]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61.
[10]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99.
[11]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M].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l990:146.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责任编辑 文 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