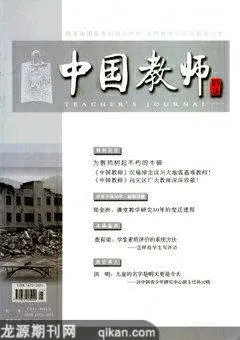游走在承接与拓创之间
纵观中国画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中华民族绘画创造源出于“意象”。意象,即主观意念想象。意象造型,就是不拘泥于形似,不模拟自然,而是把自然物象作为传情达意的中介,强调对自然物象内在神韵上的把握。它不需要真实的视点、科学的透视、比例和客观色彩理论,而是根据主观意愿、理想及对物象大悲大彻“顺天应人”的理解和关注,跨越表象、跨越时空、默契着客观法则的自由表象和任意组合,并与“天人和一”的传统哲学观念一脉相承。儒、道、释三家的“入世”、“出世”、“忘世”以及庄禅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众生平等”的写意观,构成中国画的“物我交融”、“主客合一”的,既观物又观我的宏观思维方式。“入世”就是积极投身参与现实生活,在负起责任、担起义务中求得自由。“出世”超逸了现实“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是对“入世”,欲念情感的超脱,追求的是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只有精神上的绝对自由才能到达“忘世”——“忘怀现实”的物我两忘、浑然一体的,“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的境界。儒、道、释三家都是“天性自然主义”,三者会通,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自由超越的精神。精神的无限性,才能达到艺术的无限性。中国画传统就是在这种精神完全自由下,对时代及人与自然的所感所悟,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的表达和表现。正是这种超越精神的自由,使中国画家在认识大千世界时,一开始就排除了时空序列性的制约。这种精神的超越需要历史的展现,更需要跟随时代的脉动、与时俱进。
众所周知,中国画传统博大而精深,源远流长,它与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审美意识、思维方式、美学思想、哲学观念等息息相关。它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的“生成”之中。学习中国传统不是简单的从前人那里继承和积累美术技能知识、制作方法及审美意识,不是简单的继承、模仿、再现、复制;而是应该学习传统的精神——“创新”即扬弃。
“创新”就是打破旧的秩序,建立新的和谐;突破旧的思维框架、审美定势而努力创造出新的形式。生活中,我们常常发现一些艺术家因一两幅画得名,找到了所谓自己的风格、样式就不再敢求新求变,而是画地为牢。就好像一束枝繁叶茂、花苞累累的鲜花,当第一朵鲜花绽放时,就应顺其自然,任它开花结果,自生自灭。然后再孕育新的力量绽放另外一朵,使之更加绚丽多彩,只有这样它才会生生不息、硕果累累。而不要仅停留在第一朵鲜花面前大做文章,对其千般呵护、万般保鲜,即便是喷“定型液”、涂鲜亮颜色,它也终将枯萎、失去原有的生命意义。“任何艺术形式或手法,都不可能红颜永驻、长生不老,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对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并日趋衰败的艺术形式和手法,人为的耗时耗力给予抢救是不明智的。”传统就好比鲜花,只是生命过程中的一个亮点、一粒果实,传统的精神就好比它的“根”、它的全部的生命动力。鲜花否定枝干,果实否定鲜花,留下的是生命。我们应该继承传统的创新精神,否定或超越传统的样式。传统的精神是一个活生生,不断生成和发展着的生命本原,而不是一种法则或一套审美样式。正如人们意识到的,当我们把一种技艺变成一套程序固定化、教条化的时候,其实正是背离了传统的精神。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没有永恒的真理,没有清晰、精确的概念和标准,没有完美完备的结论,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一切都是处于永恒的流变之中,无论是创作的理念,还是创作的技法,抑或创造者自身的艺术感悟都会因人因地因时而变。艺术创作中没有创新,就好像失去了生命本原的花朵。终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任何时期、任何时代,艺术品的创新都是在表现自我对客观事物独特感受和认识的情况下,依据两个条件得以完成:一是与创新所伴随的时代的脉动。二是与艺术品的创新相关联的材料和技法的革命。
一、创新必须跟随时代的脉动
任何艺术作品的创造都是根据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哲学思想等情况,进行有的放矢的创新求变。艺术是时代的灵魂,是时代精神的折射镜。“创新并非指表现现代题材,也并非指全新的绘画手段;而是指从作品深层到表层渗透着的与以往不同的时代气息,和时代观念”。艺术作品应当符合时代的审美取向。一切手段都可以是旧的,关键在于对时代新观念、新理念、新认识的重新选择和重新组合。中外艺术大师的创作历程无一不是游走在承接与拓创之间,无一不是紧紧跟随时代的脉动,例如:德国柯勒惠支的《织工暴动》《母与子》《牺牲》《死神与小孩》;西班牙戈雅的《1808年5月3日的枪杀》;法国达维特的《劫夺萨宾妇女》、德拉克罗瓦的《阿希岛的屠杀》;俄国列宾的《意外归来》,苏里科夫的《近卫军临刑的早晨》;美国约翰•特朗布尔《帮克希尔大会战》等。他们的画像一面镜子折射出当时社会政治动乱和革命战争带给人们的挫折、灾难、困苦、恐慌、悲伤与无助。
印象派伴随着时代物理科学的发展,在一个早晨睁开了双眼,看到了缤纷的色彩,突破了人类的固有色的认知概念。打破了以往单一色调、造型严谨的古典主义的审美框架,从此艺术家们的画面充满了浪漫色彩和激情,拓宽了绘画领域的新天地。
毕加索之所以被称为“艺术伟人”,是因为他一生的艺术生涯都是在不断摈弃旧风,探索新路的自我否定之中,他在不同时期、不同感觉,产生出不同形式的美术作品。前无古人,即便是有后来者,或后来者超出了他,也占据不了他第一人的位置。因为后来者只是重复、再现,而没有创新。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也是如此,即便后来者画出了远远超过《蒙娜丽莎》的惊世之作,但它依旧难以摆脱“仿效”与“临摹”的梦魇,更无法撼动《蒙娜丽莎》的原创价值。
中国近代画家石涛的创作风格的形成与演变也是一个极好的例证。作为四僧之一,石涛的画对近现代影响最大,而在当时他的影响远不及渐江。明清时代的传统绘画,讲求的是静穆作风和宽宏气度;讲求儒家“文质彬彬”和“外柔内刚”的静态美。而对那些表现出强烈气氛和外现张力感的绘画视为浮躁和粗鄙,甚至对“浑厚”、“刚劲”皆有所忌,王原祁就说,要“化混沌为潇洒,变刚劲为柔和”(《麓台画跋·题仿大痴笔》)。渐江就是把静态美做到了极至,他的静的意识、静的精神状态附和当时社会的审美需要,所以才倍受推崇。其后,社会发生了大变动、大变革,当世界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弱肉强食的时候,民族意识觉醒了,不再柔弱、不再寂静。民族意识决定了时代的审美标准的改变。这个时代需要雷霆万均之势,来驱除列强,扫除黑暗势力。因而需要吴道子的磅礴大气和“天付劲毫”,需要梁楷式的天风海雨的逼人气氛,需要石涛的“没天没地当头劈面”式的纵横挥洒。石涛的画笔情放纵,奇异多变,“动”到极点。以奔放“动态美”取胜。从这个意义上说,石涛的画在契合时代脉动的同时,也筑就了其独树一帜的画风和强劲的生命力。
由此可见,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哲学思想,都会影响人们的审美观念,同时也不可避免对艺术作品的风格、样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创新要跟随时代,抓住时代的脉搏。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这样的艺术作品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蓬勃的生命力。
二、绘画材料和技法的弃旧图新是中国画创新的基础性建构
绘画风格、形式的变化与创新往往以材料和技法的开创性变革为先端,画家的创新理念也大多借助材料和技法的创新来得以表达和传递。绘画材料和技法的创新与革命,一直是国画创造者不懈探寻的领域,也是中国画创新的基础性建构。中国画材料和技法的创新在传统与创新的悖论中,一直艰难地游走在承接与拓创之间。
纵观中国画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中国画已具备了一套完整完备的、独特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技法、艺术样式及材料使用的宝贵经验,并伴随着时代的精神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之中。
从中国画表现技法的发展看:最开始使用比较简单的“五笔七墨”、“十八描”发展到“皴、擦、点、染、丝”;以及“没骨”、“双钩”、“工笔”、“写意”等形式语言;另外还有“胶”、“矾”、“油”等绘画媒介的混合使用;“盐”、“砂”、“洗涤剂”等特殊技法的配合运用等等,在逐渐地丰富发展和弃旧图新。
从中国画艺术样式的发展看:最初的基本要素是“线”和“面”;再由“线”、“面”发展到“色彩”、“明暗”;色彩、明暗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平面上塑造“立体空间”感;再进一步是“半成品”艺术,亦即是在画面上粘贴实物(如植物、昆虫)和“现成品”等等。近年还出现了岩彩画和综合材料等绘画形式。从中也可以看到多源化的发展趋势。
从中国画材料使用的发展来看:原来由“墙上、门扉上、天花板上”发展到“布帛、绢绫”,再发展到“纸”上。现当代中国画的多元趋势在保留“纸”的基本运用基础上,有的又延伸到“亚麻布”上。在颜料使用上由原来的“矿物质颜料”,发展到“水彩、水粉、炳稀”的混合运用及矿物质“粗颗粒”和各种“金属泊”、“泥土泥沙”的混合运用。总之,这些技法、形式、材料的形成和不断发展,是伴随着时代科技的进步、审美观念的改变而出现的。并伴随时代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断完善、发展和延伸。
随着信息时代和知识多元化趋势的来临,中国画所赖以附丽的社会生活正日益变得丰富多彩,原有单一的绘画材料和技法已不能充分表达现已拓宽的绘画题材。题材的拓宽需要与之表现形式的扩大。新形式的扩大需要新的语言技法和材料的不断丰富与更新。中国画的创新,需要根植于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并跟随时代的精神,不断开阔视野、吸纳百川,以“拿来主义”的精神,广泛地吸收古今中外不同民族、不同画科的营养。研究边缘学科的处女地,把握各学科相互渗透的时代脉动,才能创作出与现代人精神结构相吻合,表达现代人新宇宙观、新时空观以及新审美意趣的形式语言,形成有别于传统文化的创新语境。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学院美术系)
(责任编辑:王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