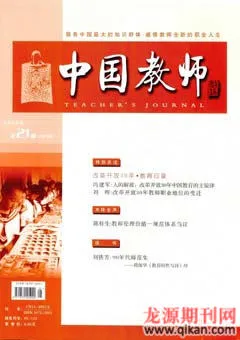八股举业,士林标准
八股文是明清时期用于科举考试的一种特殊文体。这种文体,有一个“敲门砖”的浑名。因为它除了在殿试以外的童生试、乡试、会试中使用之外,任何公私文书和各种体裁的论著中,都不会采用,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就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所说的那样:“这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奥,不过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明清两朝的读书人,开蒙之后就学习它、钻研它,只是为了用它敲开科举考试的大门。一旦考中,就将它弃如敝履,不复一顾,所谓“得第则舍之”。很多人甚至在晚年编辑自己的著作时,往往剔除早年为应举而制作的八股文,活像我们现在为了备考而发行的“同步练习”,它广泛流行于社会,泛滥天下,但只对求取功名的人在特定的时期才有意义。一旦离开这个环境,就毫无价值,甚至失去了立身之所。藏书家不取,目录学不讲,图书馆不收,覆瓿烧薪,是其最终的命运。
八股文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制义”或“制艺”,因为这是国家规定的考试文体,“制”有制度或规定的意思。八股文又叫做“时文”或“时艺”。“时”是当前、现在的意思,“时文”是与古文相对而言的,说明这种文体,不同于以前的文章。“艺”是指礼、乐、射、御、术、数“六艺”,“制艺”和“时艺”,是指当时学会八股文的写作,和古代掌握礼、乐、射、御、术、数的技能,具有同样的意义。
这一独特的文体起于何时,始于何世,人言人殊,众说纷纭。最早的甚至追溯到唐朝的“帖括”或“帖经”。更多人说它始于北宋的经义,尤其是南宋后期的经义,已经有了比较固定的格式;元朝王克耘的《书义矜式》,最先称这种文体为“八比”,八股文就滥觞于这时。《明史•选举制》说它是“太祖(朱元璋)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说它始于明朝成化年间。八股文不是一种刻意创造的文体,不成于一时,更不会出自一人之手。宋朝的经义确定了其大致内容,南宋的格式奠定了其基本体式,元朝出现了“八比”的名目,明初被最高统治者认可并规范,成化年间,经王鏊、谢迁、章懋等人提倡,形成了比较严格的程式。“厥後其法日密,其体日变,其弊亦遂日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六)它的规范和流弊,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显现的。
八股文还有一个名称,这就是“四书文”。乾隆年间,方苞奉皇帝之命,选录明清两朝“词达理醇,可以传世行远”的时文,编了一部41卷本的八股文选本,名为《钦定四书文》。这一名称的得名,是因为八股文的出题范围。
“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儒家经典。“四书”并行,最初是由于程颢、程颐兄弟的表章,朱熹为之作注,刊行《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之名从此确立。元朝确立了朱子之学的独尊地位,以《四书集注》考察士子,明朝初年,朱元璋和刘基在制定科举规范时,进一步强化了《四书集注》的意义。
八股文的题目,一律用《五经》《四书》中的原文,因而分大题、小题两类。乡试、会试多用《五经》命题,称之为大题。童试只从《四书》中出题,称之为小题。《四书》中可以作为题目的句子,为数有限,再加上童试的场次多,社会上到处泛滥着中式士子的优秀试卷选编——程文墨卷,还有的被人们写成了可供模拟的范文,完整的句子都被使用殆尽。考官便想方设法,出偏题怪题,甚至不惜割裂原意,将上下两章、两节互不相关的文句合为一题,或各取半句凑成一题。如嘉庆年间,鲍桂星为河南学正,割裂《论语》“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以“礼云玉”为题。咸丰年间,俞樾为河南学正,割裂《孟子》“王速出令,反其旄倪”,以“王速出令反”为题。面对这样的偏题怪题,考生只好生拉硬扯,缀合成文,近乎文字游戏。如古书没有标点和分段,在“夫子曰”、“孟子曰”之前,往往画一个圆圈,作为两段的界限。有试官居然以这个圆圈“О”为题,更有考生这样做破题:“夫子未言之先,空空如也。”顾炎武在《日知录•拟题》中感叹说:“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于拟题。”
不仅题目要严格限定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内容的阐释、经义的发挥,也必须以程朱学派的注释为准。这里没有独立思考的空间,只有亦步亦趋的规矩。这就意味着,要在科举的路途上斩关夺将,一路凯歌,不仅《四书》要背得滚瓜烂熟,随便说到哪句话,哪个字,甚至没有关联的两个字,都要记得起来,知道出处(否则,不知所自,不明题意,就根本无从着笔);而且对朱注也要通晓(如果背离注释的意义,自出机杼,擅生新义,就是触犯大忌,即便写得妙笔生花,也无济于事)。
“时艺所论,皆孔孟之绪言,精微之奥旨。”为了写好八股文,为了养成“中国人式的博学”,读书人长期浸淫于《四书》《五经》之中,以“龙马的精神、骡子的体力,又要像土鳖虫那样麻木不仁和骆驼那样吃苦耐劳”,孜孜不倦地苦读这几十万字的内容。通过古典的学习,他们受到儒家伦理的熏陶,从而服膺儒家的学说,把具有统治意义的最高价值体系,潜移默化到了自己的灵魂深处。
“八股文”或“八比文”的得名,则是由于它的形式。
每篇八股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但“八股”之名,并不是指这八个部分。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的意义破开或点破;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作进一步的说明,引申而言,使之晓畅。起讲是议论的开始,首二字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尝思”等开端,以圣人的口气,主要内容是继续阐明题意。明朝起讲较短,清朝颇长,但无论长短,都要总括全题,笼罩全局。“入手”又称入题、领上、领题、落题,是用一两句或两三句散句,将文章引入正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也是全篇的主干或核心。在这四段中,每段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共八股,所以称之为八股文或八比文。
除文章结构有严格规定之外,八股文的字数也有限定。明万历时,限500字以内,清顺治时定为550字,康熙时增为650字,乾隆时又改为700字。超过字数的不予誊录,考官不会阅卷,最后不会录取。
八股文这种严苛、机械的形式,最受时人的嘲讽和后人的诟病。本来,“文章无定格”,贵在鲜活,创意造言,各不相师。“立一格而后为文”,而且是如此严苛的清规戒律,“其文不足言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往往说八股文有形式而无内容。实际上,这种僵化、繁琐文体的出现,是科举制度在追求公平和公正过程中的必然结果。当试卷之外的干扰因素已经被排除,对公平的唯一影响,仅仅可能来自于考官个人的爱憎好恶;严定程式,客观衡文,公正评卷,尽最大的可能,控制评卷过程中的误差,就是科举考试发展的内在要求。八股文最大特点,是它有一定的结构规定和字数限制,还有章法、股法、句法、字法、浅深、虚实、开阖、离合相生、衬贴、反正、关锁等等写作技巧,这使得对一篇八股文进行客观评价成为可能。着眼于对这些具体的要素进行考量,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客观性。
此外,八股文的这种程式,也起到了训练思维的作用,邓云乡先生就称它“是一种单科独进的大运动量式的思维训练教育”。除了训练持久的记忆能力、敏锐的反应能力、高度的概括能力之外,还有严整的思维能力、简净的表达能力。“八股文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学会了在如此严苛的格局中依然能游刃有余,在更加开阔的空间中,援笔行文就更能纵横驰骋,一线到底,一丝不乱,理路分明,脉络连贯,简约能为一句,扩张能为万言。
八股文的写作,要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只读几部程文墨卷是无济于事的,而必须有深厚的积累。方苞在《钦定四书文》的凡例中说:“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材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复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兼是三者,然后能清真古雅。”要达到理明、辞当、气昌的境界,写出清真古雅的好文章,就必须出入文史,纵贯古今,品汇百家,包罗无外。
八股文的巨擘王鏊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在八股文上的地位,被一些人视为司马迁之于史学、杜甫之于诗歌、王羲之之于书法,古今罕有,旷左未闻。清朝的四库馆臣说:“鏊以制义名一代,虽乡塾童稚,才能诵读八比,即无有不知王守溪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一)所以如此,就在于他的古文根底湛深,经术典雅猷洁。虽然写作的是时文,但研索六经,泛览百氏,却绝对必要。只有这样才能培植根底,写出义理显明、措辞恰切、气势丰盈和气韵流畅的好文章。
历代对八股文的嘲讽讥刺、攻讦痛斥,不外乎陈登原在《国史旧闻》中总结出来的七大罪状:一是沉溺滥套,未尝学问;二是渣滓细嚼,毫无滋味;三是依口胡说,重复沓叠;四是即使工巧,并非艺术;五是对于文学,反为阻碍;六是明知无用,聊以求官;七是即有法眼,准则无从。的确,八股文恶贯满盈,罪孽深重,但它在弊端显露无疑、沦为千夫所指之时,依然僵而不死,苟延残喘,乃至废而复兴,几起几落,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才最后废止,这其中的况味,是我们不能因为它系恶名昭著的“八股”而忽略的。
(责任编辑: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