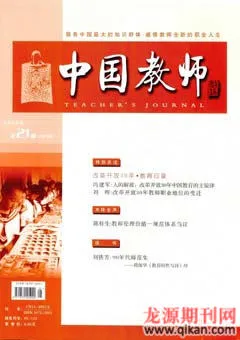尊重、同情与怀疑、批判
2004年,被学术界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年”。这一年,蒋庆选编的皇皇12卷本《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以其浓烈的“原教旨主义”倾向,引来了有关媒体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关于儿童读经问题的激烈争吵。2008年9月新学期伊始,清华大学文科实验班讲授《四书》再掀波澜。就争辩的激烈程度而言,后者远不如前者,但反对方的基本立场和一些观点却出奇地一致。其中之一,就是对“怀疑”“批判”等现代性态度的极端崇信与张扬。
对于蒋庆,笔者久读其书、久闻其名而未睹其人。但“文如其人”,读其书,可以想象其为人。且看他在《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后记中所写的两段话:
两经寒暑,一聚心力;今日书成,差可告慰。宣圣删述代作之意,朱子训蒙养正之心,于今吾知之矣!吾知之矣!
近世以降,斯文见绌;经书之厄,甚于秦火。学堂废读经,杏坛禁祀孔。于是弦歌声绝,《诗》《书》扫地,国人已不知经典为何物矣!所幸天运往还,斯文重振;经籍复兴,弦歌再起。是编之出,正其时矣。十万之文,经典精华尽在是;十二之册,圣贤法言萃乎此。唯愿吾中华儿童手持一编读之读之再读之,而他日君子之国、大同之世,必在此朗朗读书声中也。
本着同情、理解与欣赏的态度,一个活脱脱的蒋庆会出现在我们面前:饱读诗书,为文古朴,信奉儒学几乎到了迷信的程度,自信非凡而近于自负,迂腐之中充满执著,古朴之文不乏童真之气……若换一种眼光,完全基于“怀疑”“批判”立场发言,那蒋庆就完全是一副“腐儒”模样:迷信自负,食古不化,迂陋有加……打响“斥‘当代大儒’蒋庆”第一炮的旅美学者薛涌,就是本着后一种立场向蒋庆开火的:
对孩子的教育,应该是苏格拉底式的,不应是蒋先生所界定的读经式的。……教育是质疑而非背诵的过程。……后来的腐儒不让孩子提问,只让他们背书,实际上是以他们那些陈腐的“人之末”,压制孩子充满创造力的“人之初”。笔者对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的一个主要批评,就是这种启蒙主义有一个基本的设定:少数几个读书多一点的人,不仅在知识上优越,甚至在道德、价值方面,也有垄断性的权威。他们可以替别人作出决定:什么该学,什么不该学。……这实际上全是来源于传统士大夫对文化的垄断。笔者则认为,这种文化垄断需要打破。世界上人人有思想的权利,只需要记住那些自己认为值得记住的东西。(《什么是蒙昧主义?——再评读经,兼答秋风》,《南方周末》,2004年7月22日)
儿童读经之争因文化问题与教育问题相互缠绕而格外复杂,非一言可尽。在此,我更加关心的问题是,薛涌所极端崇信与张扬的“怀疑”“批判”等现代性态度对于经典研习究竟意味着什么?引申开来说,如果研习传统经典可以被视为一种人文学的学习和探究活动,那么,其合理的学习和探究方式到底是什么?
人文学的学习和探究活动所直接面对的,可以是特定的知识和文本,但这不是只在与文本、尤其不是与被当做“物”来处理的文本打交道,而是以之为中介,在读之者与作之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精神性联系。因此,人文学探究不过是以文本为中介所展开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交流活动。在日常交往中,我们对交往对象的理解和评价(包括作为情感判断的好恶之情)总是相互渗透的:既会因特定理解而产生某种评价(如好恶),也会因某种评价(如好恶)而导致特定理解。同样,在人文学探究中,探究者对于人的立场和态度,并不是外在于探究对象的,它们会作为观察视角、情感底色、精神氛围,使同一文本呈现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意义。同一部《红楼梦》,在政治“运动员”、道学家、唯美主义者、窥阴癖者眼中会呈现出十分不同的面貌,道理即在于此。说到底,在人文学的意义上,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与我们如何看待他人、解读历史,是完全无法分开的一件事。
然而,探究主体与文本意义生成的自然同一性,并不意味着出于任何立场和态度的探究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没有高下之别。如同人与人之间的有效交往和交流要以对交往对象的尊重、同情、理解为前提一样,人文文本的解读,也需要对于潜藏在那个文本之后的精神生产主体的尊重、同情和理解。这既是人文探究的伦理性要求,也是其科学性要求,是探究人与探究物的根本区别所在。袁隆平种水稻无须尊重、同情水稻,因为水稻不是人,没有人格;向袁隆平学习水稻种植技术的农民,也未必要去关注袁教授的劳动品格和精神境界,因为掌握了他那套高水平种植技术就已经达到了学习的目的。但是,当我们把袁隆平作为人文学探究的对象,要去呈现一个科学家的精神世界之时,却必须以尊重和同情为前提。这时的袁隆平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有喜怒哀乐、利益计算、理想追求,唯有从尊重、同情和体贴出发,才谈得上对他全面、完整而客观地理解。陈寅恪先生主张历史研究应有“同情之理解”,研究者要“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因为,没有对人的尊重、同情和体贴,便没有对于人的真正理解。以非人化的方式(无论是轻蔑还是冷漠)去研究人,充其量只能呈现作为物的人;而当我们把他人作为物来处理的时候,我们自己先已变成了某种没有灵性之物。佛教讲“大慈大悲”,这“慈”、这“悲”,不仅是对良善之人悲苦处境的同情与悲悯,也同时指向恶贯满盈之徒的恶行恶迹。惟其如此,“慈”和“悲”才来得博大、深沉,能唤醒那久已沉睡以至沉沦了的人性。
不仅如此,中国人对于自己的祖国、文化和人民,不仅需要一般意义上的尊重、同情和理解,更要有一种历史承担意识。因为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注定不能以一个旁观者的面目出现,而应快乐着她的快乐、悲伤着她的悲伤,为她的缺憾而扼腕叹息,为她的罪恶而痛心疾首。当年孔老夫子周游列国,其道不售,累累若丧家之狗。有隐者对子路说:“而与其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意思是说,你与其跟着孔子那种逃避坏人的人,为什么不跟从我们这些逃避整个社会的人呢?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这怃然而叹、回应隐者的话,同时表达了孔子对于社会充满忧虑、期待与责任的复杂心情和深切关怀,尽管现世人群充满了问题、缺憾以至罪恶。对于先圣之道,孔子提倡“默而识之”。这个默,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的默识心通,是在言思路断之际,用生命来体证生命——体认言说背后的那个言说者的完整精神世界。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论语•述而》)。“述”是“传旧”(朱熹这样注释),但这个“传”并非口耳之间的事,而是以心传心。所以,“述”不仅需要言、需要知,更需要“信”、需要“好”——一言以蔽之,需要整个生命的投入和体贴。惟其如此,“述”的过程才是一个“学”的过程,是一个人在深入历史、文化世界的同时,不断开拓和丰富自己的精神成长空间的过程。惟其如此,这“述”才能传神,具有教和诲的价值。故孔子又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故”可以是历史,可以是旧知,也可以是习见、习闻的常事(因而也是故事,“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就是指向日常故事的);“知新”不仅是所知者日新,更是这个知者在温寻故事过程中,“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的日新月异的精神世界。因此,“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其实是说,一个有述的本领而又具有日新精神的人,方堪当师者之任。这个“温”字用得很妙,同时表达了情感体贴和思维寻绎的丰富内涵。
我想,《史记•孔子世家》在“当世则荣,殁则已焉”的帝王将相与身为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的孔子的对比中彰显孔子的价值,并以“至圣”相许,那“至圣”所代表的是非凡的学问,更是构成那学问的生命骨骼,是孔子那深切的人文关怀。对于物从而对于作为物的人的知识可以因时而迁,但这种使人与人相沟通的人性情感却历久弥新,具有永恒的文化价值。惟其如此,尊重、同情、理解才构成了人文学学习和探究的基本前提。而所谓“怀疑”“批判”,只有运作在那个前提之下才会真实有效,成为有人味的文化创生。
进入现代社会,半是西方科学主义和民主自由思想驱策,半是中国人求胜心切而又文化自卑心态作祟,世风丕变,尚新、尚异、尚自我,疑古、疑人、亦疑我。张口批判,闭口创新,仿佛若非“我”字当头、“破”字领先,便与“作”者无缘。以“怀疑”“批判”为代表的现代话语,在增强中国人自我反省和批判意识的同时,也助长了藐视前贤、轻慢自己文化传统的消极心态,似乎每一个人都在扮演“文化警察”的角色。古时作文“诗云”“子曰”之类固让人皱眉,倒还有点儿谦逊的意思在。今人“我”字当头、自以为是的创新,则连自知之明亦付阙如,就不能不叫人忧虑了。为了“创新”,我们用所谓“批判”“怀疑”精神,拼命地找古人的茬儿,找他人的毛病……于是,学问未必增高,心胸却日趋褊狭,最后只剩下个空荡荡的“我”。时间久了,当我们“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时候,就又跟自己、跟“我”过不去了——自我从此分裂。要摆脱这种精神分裂症,我们最好先把“批判”的姿态搁置一边,从学会“欣赏”开始。欣赏前人,欣赏他人,也欣赏自我。在思维上,先学会“正向思维”,再开发“逆向思维”。如孩童学步,要从向前走,走正道开始;一上来就倒着走,弄不好就跌坏了稚嫩的大脑。
因此,当蒋庆宣称自己所倡导的儿童读经旨在“启”以启蒙自任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之“蒙”时,话虽说得大了些,但他对中国人现代文化心态之弊的揭示却是深刻的。倒是秋风——那位被称为“温和自由主义”的学者——在批评薛涌之文时的论说,更加平实而中肯:“让我们还是理性一点,宽容一点,尤其是对自己的传统、对自己的祖先、对自己的文化,多一些同情的理解,而少一些刻薄、猜疑、鄙视和仇恨。”(《现代化外衣下的蒙昧主义》,《南方都市报》2004年7月13日)。不少新读经运动的追随者也不无“蒙启”的成分,但运动的兴起和持续至少表明,国人的文化立场和文化心态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朝着符合人文文化本性的方向。
(责任编辑: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