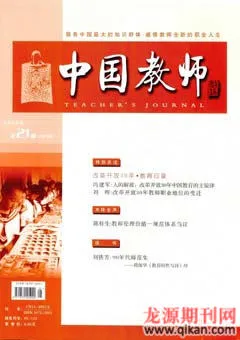爱与教育精神
教育者必须对教育有信仰心,如宗教徒对于他的上帝一样;教育者须有健全的人格,尤须有广泛的爱;教育者必须能牺牲自己,任劳任怨。
我斥责那些以教育为手段的人!我劝勉那些以教育为功利的人!我愿我们都努力,努力做到那以教育为信仰的人。
——朱自清:《教育的信仰》
教育事业是爱的事业,教育精神特质在于以爱使人成其为人。对教师而言,爱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操守,是一种敬畏。
一、爱使教育成为可能
教育源自爱,教育的价值和内涵取决于对教育的爱有多深。没有爱为基础,教育可能成为混饭吃的一种营生;没有爱,教育活动可能成为一种强制灌输,成为一种压迫、压制的反教育行为。爱之于教育犹如水之于池;无爱之教育,如同失去生命与活力的无水之池。
“有爱的地方,就有天堂。”有了爱,教育活动成为春风化雨般的沐浴,优秀者更优秀,孤独者不再孤单,贫弱者不再贫弱,问题学生可能成为优秀学生。“要有爱心,一个人如果不爱他的事业,事业就将抛弃他;一个人如果不爱他的国家,也就失去了原动力。”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曾深情地写道,“要不是老师对我的爱,我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要不是同仁、学生对我的支持,我的成果不会这么多;要不是我的亲人对我的爱,我也将一事无成。我只有做得更好才能回报所有为我付出无限爱心的人们。”[1]是爱激励他不断追求卓越,他同样以爱回馈他的事业和学生。
陶行知曾有语:“好的教育可以使人成龙,坏的教育可以使人成蛇。”没有爱的教育就是坏的教育,它将教师与学生摆在对立位置,成为一种压迫人的反教育行为:教师有知,学生无知;教师思考,学生是思考的对象;教师作出选择,学生依从选择;教师选择课程内容,学生顺应这些内容;教师演讲,学生听讲;教师执教,学生受教;教师把知识的权威性与他自己职业的权威性混淆在一起,使他处于学生自由的对立面。[2]这种教育教学方式直接导致学习者被动、服从、缺乏主见和进取心等与身心发展背道而驰的结果,成为一种压迫活动。“爱人者则人爱之,恶人者则人恶之,知得之己者则知得之人。”(《孔子家语•贤君》)教育中没有爱,便成为一种悲哀甚至是反人性的教育。悲哀教育可能带来悲哀的结果。2007年11月7日芬兰图素拉镇约凯拉中学的学生奥维宁手持手枪,对着昔日的同学说:“你们没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我要毙了你们!”致使多人遇难,他也随后饮弹自尽。警方发现他遗书上仅写着一句话:“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和我成为朋友?”
二、爱使教育得以成行
弗莱雷这样概括教师的工作:“它是这样一种工作,要求那些从事教育活动的人培养特定的爱,不仅要爱他人,更要爱教学所包含的过程。没有爱的勇气,没有不轻言放弃的勇气,就不可能有教育。简言之,没有长期培养的新鲜而深思熟虑的爱,是不可能做好教育工作的。”[3]从弗莱雷的观点来看,教师工作就是爱的工作、理智的工作、严肃的工作。
知识是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爱是不断获取新知与尊重知识的心理基础。正如罗素所言:“爱引导明智之士去寻求知识,以清楚地知道如何使所爱的人获益。”[4]没有对教育、对学生的爱,获取新知将成为一种外来强加的负担,成为枯燥的吸收;没有爱,失去对待知识的严谨和尊重,获取知识的活动将成为“道听而途说”的“德之弃”的工作。
爱学生,才能了解学生;了解学生,方能有效教育。有了对学生的爱,才会有“各言其志”(《论语•先进》)、“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退而省其私”(《论语•为政》)的“言”“听”“观”“察”“省”的知人之法;才有“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果”“求也退”“由也兼人”(《论语•先进》)的认识;才会有“闵子在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訚訚如也。子乐”(《论语•先进》)的快乐;才有“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的判断;才有“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言之,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的做法,才能因材施教,才有孔子作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荣誉。
教育过程是知识传递的过程,更是人格塑造、情感陶冶的过程。因为这一过程不仅提高领悟能力,而且规范行为;不仅影响和塑造智力,同时影响和塑造意愿;不仅对思想而且对心灵进行教化。只有对学生的爱,才可能有“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悔乎?”(《论语•宪问》)的反问,才能抵制“己所不欲”的灌输式教学;只有对过程的爱,教学才能以“循循然善诱人”的方式展开,才可能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论语•子罕》)的效果出现。
爱是一种情感传递,爱的传递使得教育过程得以和谐,大大减轻管理的负担。所谓“恭而敬,可以摄勇;宽而正,可以怀强;爱而恕,可以容困;温而断,可以抑奸”(《孔子家语•五仪》)。赫尔巴特在其《普通教育学》中指出,爱所要求的情感和谐可以在两种情形下产生:教师深入到学生的情感中去,不让儿童注意到即机警地参加进去;或者设法使学生的情感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接近教师的感情,教师一旦得到学生的爱,就可以减轻管理、教学工作的困难。
三、爱使教育有所坚守
“人而无独立之精神,是之谓奴隶。任教育者,而不能养成国民独立之精神,是之谓奴隶教育。以教育为己任者,安可不知此意。”[5]教育的特质要求教师具有高度的心智独立,在追求真理时,不受不合理的限制,在表达学识结论时,不需要检查制度的威胁;具有抗拒影响正常教育、教学和研究的外部控制的能力,使自身的心智保持独立和自由,并以养成独立精神之国民为己任;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坚持自己的信念,正如顾炎武所说:“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没有爱做支撑,没有对教育的信念,这些几乎都不可能。
教师的这种信念建立在如下认识的基础之上:教育是公共事业,教育有自己的特点、规律。这意味着教师只对教育负责,不会屈从于某种偏离公共价值的意图、制度、规范;教育以自己的目的为目的,社会目的通过教育自身审视后成为教育目的的一部分,但这种选择一定是由教育主体而非其他主体做出;教育无论对学生个人还是对社会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成功教育需要的不仅是知识,还包括献身精神。教育包含着一种使命,因而它不仅仅是一项工作、一种职业,而是教师的天职。
正是基于此,在教师看来,在教育与社会各要素的关系中,教育自身是本,社会各要素是末,有本才有末,只有教育正常发展了,才谈得上为社会服务。教师是使教育成为自己的本、自己的主体的人。对教师而言,忠于教育是一种操守、一种信念、一种行动,教师会以自己的良知效忠于自己的志业。九十多年前,陈独秀就指出:“以执政之摧残学校,遂无教育可言,执政倘焚书坑儒,将更谓识字之汪阔乎?以如斯志行薄弱之人主持教育,虽学校遍乎域中,岁费增至亿万,兴国作民之事,必无望矣。”[6]
爱使教师有所坚守,也使教育有所坚守。教师“必须敢于说爱,以便在我们熟知的条件下长期继续教书,那就是:低工资,缺乏尊重,时时存在的变得玩世不恭的风险。我们必须学会勇敢,以便对我们天天面对的思想官僚化说不。我们必须敢于说爱,这样,即使在不这么做也有很大的好处时,也能继续敢于说爱。”[7]当教师有所坚守时,教育就有所坚守。
四、爱使教育得以有效
教育活动始于人,终于人,而非制造某种特殊用途的工具。教师知道,只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获得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对获得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鉴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8]
教育不是压迫和驯服,教育目的不在于是制造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不在于培养人的依附性。“在现代社会,从自由向依附的任何倒退都是精神不健全的标志,因为这种倒退与人类已经达到的发展阶段不相符合,而终究导致各种精神病症。”[9]教师知道,失去了对学生的平等、民主、尊重,教育活动可能成为一种压迫行为,使学生被置于受压迫的地位,成为被压迫者。在学校,依附于教师;离开学校,依附于强UW/xzSLoG/3b2F0TrZp1VQ==势人物。作为被压迫者,他们会尽力改变自己的地位,但他们改变自己地位的目的不在于消除这种压迫现象和机制,而在于将自己从被压迫者变为压迫者。一旦成为压迫者,他们又会强化这种压迫机制,从而使压迫行为成为一种循环。学校中的被压迫者终将步入社会,他们会将这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压迫观念和行为带入社会,使得压迫成为一种社会现实,并且使得社会处于压迫的循环怪圈之中。跳出压迫与被压迫怪圈的方式是将人当做人,是爱人,恭敬地爱人,因为人是自由的。人的自由只能在尊重、平等、民主的教育过程中实现。同样,教育中的平等、民主会被受教育者带入社会,使得社会不断向平等、民主方向发展。
没有理智的爱,缺乏力量,难以持久;不严肃的爱,则可能是溺爱,甚至是在爱的外衣之下的反爱行为。所谓“恭者不侮人”(《孟子•离娄章句上》)、“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爱是教育的基础,但失去了平等、民主、恭敬的爱,对教育是一种灾难,对社会同样是一种灾难。“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恭敬者,币之未将者也。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孟子•尽心章句上》)。若“视学生为群羊,仁者牧之,不仁者肉之,牧之始,肉之兆也。故牧民政策之下,个人无位置,尽群羊而已。教育因尊重个人,故曰自动、曰自治,曰个性……一社会之中,各个人之价值愈高,则文明之进步愈速,吾人若视教育为增进文明之方法,则当自尊重个人始。”[10]
对教育的爱是中国文化教育的传统,奠定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基础,这种传统依然是今天教育的守护神。日渐走向平等、民主的中国教育依然需要这种爱,需要理智、平等、恭敬的爱来守护教育之精神。
注释:
[1]顾秉林.清华园里“一个也能不少”[EB/OL].http://edu.people.com.cn/BIG5/8216/7278180.html.
[2]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5-26.
[3][7]保罗•弗莱雷.十封信:写给胆敢教书的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6、6-7.
[4]罗素.罗素的智慧[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3.
[5]佚名.教育泛论[J].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