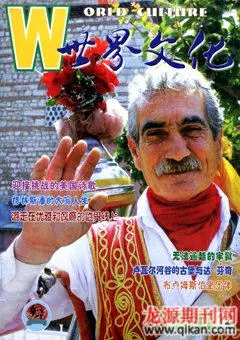卡丽的礼物
感恩节就快到了,我带着6岁的妹妹去看爷爷,并且邀请他到我们家来和我们一起过感恩节。
到了爷爷家,屋子里一片寂静,一切都和往日一样,冷冷清清,连一点节日的气氛都没有。
我们找遍了整座住宅,最后才在厨房里找到爷爷。他一个人坐在一把垫了衬垫的椅子上。他的身体僵硬,粗粗的胳膊放在福米卡家具塑料贴面的桌子上,嘴里叼着他的旧烟斗。
爷爷是一个旧式的意大利乡下人,不仅脾气暴躁,而且性情执拗,倔强起来,几头骡子都拉不住。每当他恼火或者不耐烦的时候,他就不愿意说话,而是用喉咙里发出的一声“咕噜”来代替回答。岁月的沧桑和生活的磨难在他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伤痕,使他至今仍无法忘记那些令人痛苦的回忆。
“爷爷,我们来看您了。感恩节您到我们家去和我们一起过吧。”我嘴里虽然这么恳求,心里却知道他是不会答应的。
果然,在听了我的恳求之后,他只是在喉咙里咕噜了一声,给了我一个否定的回答,混浊的目光越过我,落在对面的墙壁上。
“来吧,爷爷,您就答应我们吧,”卡丽撒着娇恳求道。“我会单独为您做一些您最喜欢吃的饼干的。妈妈说她会教我怎么做的。”
“爷爷,这是感恩节,看在上帝的份上,您就过来和我们一起过吧!”趁着卡丽在向他撒娇的机会,我再一次恳求道。“您已经有四年没有和我们一起吃过晚饭了。就让以前都成为过去吧。爷爷,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他瞥了我一眼,蓝色的眼睛里照旧闪烁着一种愤怒的眼神。在过去的许多年里,这种眼神一直震慑着我们家庭里的每一个人。可是,我是不受他的震慑的。因为,我了解他。因为我也像他一样孤僻和不善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当然,我是不愿意公开承认这一点的。
卡丽仍然在喋喋不休地说着,试图说服他。她不知道这样做简直就是徒劳。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俯瞰着爷爷的后院。在冬天的阳光照射下,荒凉芜杂的花园被蒙上了一层灰色,里面杂草丛生,蔓藤纠结。过去,爷爷把那里拾掇得可好看了,绿的草,红的花,到处充满生机。可是,自从奶奶去世以后,他就再也不去管它们了,任由它们自生自灭。尤其糟糕的是,他对自己也是这样,他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孤独的世界里了,不让别人进入。
我从窗前转过身,在更深的幽暗中端详他。从他那突出的下巴到他那粗大的双手,他身上的每一处都映射出他一生的艰辛。的确,他从13岁就开始干活了,在经济大萧条期间又饱尝失业的痛苦;此后,又在特伦顿的斯通采石场里干那种重体力的活儿,而且一干就是几十年。他的生活的确是不容易啊。
我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亲。“我们现在得走了,爷爷。如果您决定来和我们一起过感恩节,我会来接您的。”
他仿佛没有听见我说话,仍然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眼睛直直地注视着前方,嘴里叭嗒叭嗒地吮吸着他的旧烟斗。
几天后,卡丽向我要爷爷家的地址。
我问她:“做什么?”
她一边将一页纸叠得整整齐齐的,塞进一个蓝色的信封里,一边回答我说:“我想送给他一件礼物。是我自己做的。”
我把爷爷的地址告诉了她,她写得很慢,全神贯注地将每一个字都写得既整洁又漂亮。写完以后,她放下手中的铅笔,坚定地说,“我要自己去把它寄走。哥哥,你带我去邮局,好吗?”
“我们过一会儿再去,好吗?”
“我现在就要去。求求你了。”
我拗不过她,只好答应了。
在感恩节那天,我醒得很晚,是意大利沙司的香味把我诱醒的。妈妈正在厨房里准备她的特殊的晚餐:馄饨、火鸡、椰菜、甜马铃薯,还有酸果曼沙司—— 一桌意大利和美国的传统食品的完美组合。
“只要准备4个人的位置就够了,卡丽,”我走进厨房的时候,正好听到妈妈对正在布置餐桌的卡丽说。
卡丽摇了摇她的小脑袋,说:“不,妈妈,我们要准备5个人的。爷爷会来的。”
“噢,亲爱的,”妈妈看了看卡丽,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会来的,”卡丽坚定地说。
“卡丽,你就相信我们这一次吧。他不会来的,这你是知道的。”我不想看到她这一天被失望给毁了,就提醒她说。
“约翰,让她摆吧。”妈妈看着卡丽,无奈地说。“那么,再多摆一套餐具吧。”
这时候,爸爸从起居室里走过来,站在门口,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卡丽摆餐具。
忙碌了一天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坐下来准备吃晚饭了。我们围坐在餐桌边,静静地等了一会儿。然后,妈妈瞥了卡丽一眼,说,“我们现在可以做饭前祷告了吗,卡丽?”
卡丽向门口看了一眼。然后,她低下了头,嘴里开始喃喃地念诵起来,“请保佑我们,上帝,谢谢你赐予我们食物。保佑爷爷……帮助他快点来。谢谢你,上帝。”
我们三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作声,也不吃饭,似乎只要我们不开始,“爷爷不会来了”就不算是定局,而卡丽也就不会失望。我们全都默默地坐着,只有客厅里的时钟在滴滴答答地响着。
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沉闷的敲门声。卡丽一下子跳了起来,向客厅跑去。她猛地拉开门,高兴地大叫:“爷爷!”
来人正是爷爷!
他笔直地站在门外,身上穿着他仅有的那套已经被磨损得发亮的黑西服,一手拿着一顶浅顶软呢帽,压在胸前,另一手拎着一个正在晃来晃去的褐色纸袋。“我带了一些果汁来,”他一边说一边举起了那个纸袋。
几个月之后,爷爷在睡梦中平静地去世了。在清理他的橱柜时,我发现了一个蓝色的信封,里面装着一张折叠起来的纸。纸上画的是我们家厨房里的餐桌,餐桌边摆着五把椅子。其中有一把椅子是空的,而另外四把椅子上则淡淡地画着标示为妈妈、爸爸、约翰和卡丽的人。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则都用大红色的彩笔醒目地画着一颗心,每一颗心的中间都有一道锯齿状的裂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