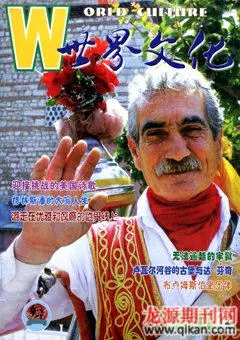友谊树上的花蕾
翻阅新出版的《丝路盛开友谊花》,看到我国前驻叙利亚文化参赞王贵发同志回顾中叙两国文化交往的文章中提到,他1998年去叙利亚履新时,曾专门去看望首位毛主席诗词的阿拉伯文译者、叙利亚著名学者马姆杜哈·哈基博士,不禁思绪翩跹,将我又带回上世纪六十年代,同马姆杜哈·哈基博士相处的日子……
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工作。那时,在国内学习外语远没有今天这样好的条件,加上阿拉伯语的书面与口头语言之间差别较大,初出国门口语与听力往往比较吃力。使馆特意为我们这些初到使馆工作的青年聘请了辅导老师,而那位导师恰恰就是马姆杜哈·哈基博士。
哈基博士当时年近六旬,比我们年长30多岁。他头发花白,体格却十分健壮,这大约得益于年轻时热衷于足球及健美体操。他早年留学法国,精通法语、英语,是叙利亚著名的学者。除在大马士革大学任教外,还是海湾与北非好几个国家的客座教授。他学识渊博,著述丰富,除文学作品外,还涉及教育、体育、卫生及社会其它领域。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封建势力依旧占据阿拉伯社会主导地位的时候,他不顾保守主义与极端势力的威胁,毅然将他用文学家的浅显易懂的语言写的科普专著《谈性欲》出版了。在当时这本书与埃及著名女作家、女权运动倡导者纳瓦勒·苏阿达维著的《男人与性》、《女人与性》等专著,敢于就人们避讳的两性问题进行科学的阐述,无疑是惊世骇俗的。他说:“我认为文学家首要的职责是维护真理、自由和帮助人们挣脱社会与思想的禁锢”,鲁迅先生曾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比作勇士,在这一领域,哈基博士在阿拉伯世界可算得上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同哈基博士相处是十分愉快的。那时,我们每人每周辅导两个小时,我总是将日常工作、生活中遇到的语言上的问题集中起来,向他请教,或就某一问题和他用阿拉伯语交流,以提高用阿拉伯语听、说的能力。那时我们同其他初学外语的人一样,总摆脱不了母语的束缚,说话时习惯用母语思维,再在脑子里“译”成外语说出。说出的话不是按母语的语序、不符合所学外语习惯,就是词不达意。正因如此 ,往往“心虚”不敢张口。而哈基博士总是不厌其烦地鼓励我:“说下去,说下去……”待我说完后,他不是简单地指出表达不完善的地方,而是例举出几种不同的表达方式,让我对两种语言的差异进行比较,以便尽快掌握阿拉伯语的习惯用法。所以我们都格外珍惜每周同哈基博士相聚的那两个课时,每次都早早地在使馆门口等他到来。
哈基博士是著名作家,当他得知我也喜爱文学,14岁就开始写诗,并已在报刊上发表过近百首诗歌时,十分欣喜。每次辅导时,当解答完我的问题后,还常就中国与阿拉伯历史、文化、社会生活、民族风习等方方面面同我交流,令我获益匪浅。他也把我当作忘年知交。有一次,使馆俱乐部组织我们去叙利亚南部城市巴士拉游览,在那里第一次参观了巴士拉古城堡。古城堡始建于中世纪,是石砌的,与国内常见的砖砌的高墙、碉楼的古代防御体系迥然不同。城堡内除囤兵的营房、水池、仓库外,还有四通八达的甬道、高高低低的城堞、视野开阔的射孔和无处不在的能致强敌于死命的暗道机关。在以弓箭、刀斧、攻城锤为主要作战工具的冷兵器时代,可谓是“固若金汤”。登上城堡,极目远望,见天边黄沙漠漠,耳畔风声呼呼,可以想见当年人喊马嘶,旗飞剑舞,戈矛相击的争战场面……尽管远古争战的烟尘早已散去,但上世纪六十年代正处在冷战时期,中东以至整个世界仍是阴晴不定。古城堡西望,越过胡兰平原,叙利亚与以色列交界的戈兰高地上,三天两头便响起隆隆炮声。我想,天下并不太平,每一个爱好和平的人都应当警觉,应当在心中筑一座“城堡”。回使馆后,我将这种感受写成一首小诗,同哈基教授会面时,他要我把诗译给他听。译诗是很难的,只能一句一句解释大意。不料哈基博士却饶有兴致地听着,他说:“阿拉伯诗人也曾写过同样的题材,但观察的角度与理念同你写的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你将古城堡同中东及国际时局联系起来,呼吁人人心中都应筑一座‘城堡’,对我们来讲十分新奇。这或许是不同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缘故吧……”他把我译的诗一句句记下来。我当时并未留意,不料再一次见面时,他竟把那首小诗用阿拉伯诗歌的传统格律译成了阿拉伯文。这无异于重新创作,令我十分感动。他建议由他将这首诗推荐给叙利亚或黎巴嫩的文学刊物发表,他认为阿拉伯的读者也会同他一样,对中国诗人从另一个角度描述他们熟悉的古城堡感兴趣。而我却踌躇了。因为出国前,组织上同我谈话时,曾委婉地提出:“你喜爱写作,这不是坏事,但国外人少事多,应当把全部精力用到工作上。”我一直牢记着这话,这次写也只是偶然为之,并不想张扬。倘在阿拉伯报刊上发表,“动静”就太大了。我只好婉拒了。但对哈基博士,一直心存感激。
哈基博士也常给我介绍阿拉伯文学与诗歌。记得有一次,他在谈到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阿拉伯国家在黑暗的殖民统治下的悲惨情况时,随口背诵了阿拉伯半岛一位诗人写的诗歌,那是描写英国总督“规劝”一位被捕的起义者说:“你只要服从我们,就恢复你自由”,那位起义者冷笑着回答:“我宁可从你这窗口跃下/那样我还可以拥有两秒钟的自由……”这两句诗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那时,使馆文化处经常收到国内提供的外文刊物《中国画报》和《中国建设》,是对外宣传用的。也有少量英、法文版的《中国文学》,只提供给懂英、法文的教授、学者。我将《中国文学》送给哈基博士,有新出版的,也有前几年的旧刊物。哈基博士对这本刊物很感兴趣,特别是上面刊登的毛主席的诗词。毛主席诗词诸如《沁园春·雪》、《七律·长征》等,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首次集中发表,却是在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上,一共是十八首诗词。而首次译成英、法文,则是在1960年4月英、法文版的《中国文学》上。哈基博士读到毛主席这十八首诗词后,非常兴奋。他说:“过去,我只知道毛泽东是中国的政治领袖,也是一位领导过长征,推翻过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创建了新中国的传奇人物,却不知道他还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 他对毛主席的诗词赞赏备至,认为它既有政治家、哲学家高瞻远瞩,对事物洞若观火的气度,又不乏文学大家与诗人轻灵、敏锐的艺术表现力。他读时用铅笔作了许多批注,记得他指着其中一处说:你看这首叫《大柏地》的诗歌,后面的注释说它是一个地名,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曾在那里打过一个胜仗。那时,红军还很弱小,而敌人却很强大,他们不得不到处转战,条件十分艰苦。几年后,毛泽东重游战地,用这首短诗,抒发他的感慨。他没有写红军面临的困难,也没有写战争的残酷,而是描写雨后的彩虹,起首便用“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色彩写出彩虹的瑰丽多姿,像是什么人持着这条彩带在空中翩翩起舞。接下来又说和这彩虹相辉映的夕阳及墙壁上残留的弹痕,把这雨后的山川装点得更加美丽。读者感受到的是爽朗、乐观与自信。他说:“大概只有毛泽东这样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斗争经验,又有高度文学概括与表现力的领袖,才能写出这样的诗。”他还说那首诗令他想起阿拉伯诗人伊本·鲁米描写彩虹的名句:“(天上)那一弯弓是用黄色、红色、绿色在白色的云朵上绣成……”他说这和毛泽东的诗句有同工异曲之妙。
他决定将这十八首诗词译成阿拉伯文,这显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我能给予他的帮助十分有限,《中国文学》上的注释是周振甫先生的,我知道臧克家先生也曾专门对这十八首诗词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便让爱人给我寄来一本,作为同哈基博士探讨这些诗词含义及背景材料的参考。如他在《序言》中所说:“我们了解西方的诗歌,更了解阿拉伯的诗歌。而这些诗对我们来说,却是全新的、毫无所知的。不仅对诗人所描写的他们国家的重大事件毫无所知,诗中引用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神话人物与传说(如吴刚、嫦娥、桂花酒、唐僧、孙大圣等等),中国读者一看就心领神会,而我们要弄懂它,却需加上长长的注释不可。”因此,他说他在翻译时,“常常发觉自己茫无所从地站在交叉路口……”
诗是语言的艺术。中国与阿拉伯的古代的诗歌,都有严格的格律、音韵的限制。除格调、意境、灵动的巧思外,遣词、造句都需要对对方及本民族的传统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极高造诣。要将它们互译,又能不失原诗的语言特色,绝非易事。哈基博士在翻译毛主席诗词时,绝不满足于将原诗的意思翻译过去,他说:诗属于美学范畴,一首好诗会以它高尚的格调、优美的意境和诗歌特有的音韵、旋律产生的感染力,深深打动读者的心灵,令他或悲或喜,或哭或歌,欲罢不能。如果失去了它原有的特色,就会变得索然无味,不能感动人、鼓舞人,那便失去了翻译的意义。因此,在翻译时,他还特别关注原诗词的音韵、旋律,常要我一遍遍用中文为他大声朗诵,他在一旁仔细地聆听、品味。记得毛主席1934年至1935年长征途中写的那三首《十六字令》,原注中有当地一首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宝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毛主席将这首民谣 “反其意而用之”OXqsMY6iF+9hbb0MVTORpny5e3ffzOYE+9AeiVrPOno=,起首一个“山”字,便将突兀而起,阴森陡峭,气度非凡的山势跃然纸上。而红军战士却不为所惧,不“低头”,不“下鞍”,扬鞭策马,直上山巅。猛然回首,惊觉离天只有“三尺三”!。这首诗他斟酌了很久,起初,第一句也仅用了一个“山”字。但阿拉伯语单数、复数是不同的,原诗中的这个“山”字,无疑是指红军长征途中的崇山峻岭,应是复数。而阿拉伯国家除黎巴嫩外,没有很高的山,即使用了复数的“山”字,也难表现原诗的气势,他在翻译时,决定在后面加了一个形容词“高大、巍峨的”,为了加重语气,又在后面按阿拉伯行文习惯加了两个惊叹号。而“离天三尺三”的“三尺三”,是形容人几乎快触着天了,并非实际距离。倘死板地照原文直译,还得用公尺来换算,那样译出,诗意全无。哈基博士灵活地选择了阿拉伯民间习惯的表示距离极近的俚语:离天“只有三只脚加三根手指”。不仅未失原意,而且阿拉伯读者一看便心领神会。这些大约也只有哈基博士这样的学者、诗人,才能有这样大胆、从容的妙译。
这本诗集终于在1966年1月,由黎巴嫩阿拉伯觉醒社正式出版了。我忘不了哈基博士郑重地将散发着油墨芳香的译本递给我时的兴奋的表情,他说:“这不仅仅是阿拉伯学者、诗人翻译的第一本毛泽东诗词,而且,是我出版的第60本书,我将它作为我即将来到的六十岁生日的最好纪念……”他像完成了一件重大的使命那样高兴。 这本书装祯精美,封面与封底浅灰的底色上,分别用阿拉伯文与英文印着:“毛泽东来自中国的诗马姆杜哈·哈基博士译”。封底的英文是印刷体印的,而封面的阿拉伯文,是他特意请他的朋友、叙利亚当时最著名的书法家巴拉维为他用阿拉伯的竹签笔题写的,笔划圆润、流畅,显得格外庄重、素雅、大方。扉页上还印着一帧圆形的毛泽东侧面的浮雕头像。
哈基博士六十岁生日时,邀请我们几位他的中国使馆的学生:当时在使馆文化处工作的吕志星、在新华分社工作的唐继赞和我去他家作客,我们和他、他的女儿以及他的亲朋好友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友好、温馨的夜晚。不久,他应邀去苏联讲学,特意来使馆向我们辞行。当我们挥手与他告别时,除了祝福他一路平安之外,还按穆斯林的习惯用阿拉伯语对他说:“真主与你同在”。不料这位并不笃信宗教,却珍视友谊的穆斯林竟摇摇头,笑着说:“不,不是他。是你们与我同在。” 记得几天后,我便接到一张他从莫斯科寄来的明信片。这是他在莫斯科机场一办完手续,便去服务台买来,分别向他女儿和我及他的中国学生报平安并致以问候的。后来,哈基博士应聘去摩洛哥的一所大学任教,我们这几个他的中国学生也相继任满回国,同他中断了来往。但他寄给我的那张明信片,及他翻译我那首小诗的阿拉伯文手稿,我都一直珍藏着……
一晃几十年过去,读到王贵发参赞的文章,缠绵的思绪又把我带回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同哈基博士相处的日子。前苏联一位著名作家,曾把文学作品比作“友谊树上的花蕾”,当年,马姆杜哈·哈基博士翻译的第一部阿拉伯文的毛泽东诗词,也正是中国、阿拉伯友谊之树的一束花蕾。随着时代的推进,这友谊之树上的花朵,也将绽放得更加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