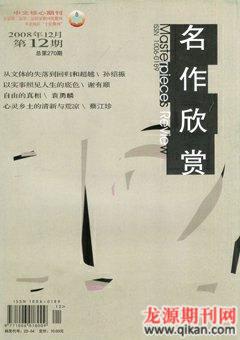樊篱中的枯玫瑰
罗 媛
威廉•福克纳是美国南方文艺复兴最杰出的代表,《纪念爱米莉的一朵玫瑰花》是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里世系”里的最负盛名的短篇小说。这篇恐怖、阴森和充满感伤的短篇小说备受历代评论家的关注,也吸引着无数读者饶有兴趣的阅读。通常爱米莉被解读成一个代表传统的纪念碑,一个代表内战前南方价值和南方文化的象征。随着20世纪80年代短篇小说认知批评的发展,批评家们从认知的高度就短篇小说意义解读过程中的认知框架设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 ①,在认知批评的框架下重读《纪念爱米莉的一朵玫瑰》,该文本有了新的内涵。
美国批评家苏珊•亨特•布朗(Susan Hunter Brown)认为,我们在阅读短篇小说时,同时面临文本的两种组织方式,一种是‘整体相继(succession),一种是‘局部构造 (configuration),当我们把一个文本读解成一种‘整体相继的事件系列,我们会把每个单独的事件读成一个具体历史时空中的具体事件,而当我们把它读解成一个由多个局部细节组成的主题结构,那么,我们就可能把所有细节看作是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隐喻,因此短篇小说不同的读解方法对于文本意义的阐释影响甚巨。布朗以《纪念爱米莉的一朵玫瑰花》为例,指出该小说的叙事人完全放弃了时序性阅读,而彻底地选择了一种隐喻和象征性阐释。福克纳通过该叙事的安排,向我们揭示:男性主导的战后美国南方社会对于女性继续实施着或天使化或妖魔化的压制策略,叙事人竭力引导读者把女主人公的故事读成一种隐喻符号,完全地抹杀了她作为一个现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物的生活逻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小说中,福克纳将女主人公的故事巧妙地织入了整体时序与局部特征之间,使作品的原始事件随时可能冲破叙事人强加于小说的主题解读而暴露在所有读者面前,此外,他把女主人公描写得桀骜不驯,有意让她的叛逆精神颠覆小镇居民对她的象征性解读。布朗暗示,《纪念爱米莉的一朵玫瑰》向读者讲述的不仅是一个美国南方的寓言,小说更让我们看到了男权文化当中一个真实的被压迫女性与社会坚定抗争的一个经典个案。②虽然布朗作出了暗示,但没有对该文本作出具体而详尽的解读,在布朗观点的启示下,笔者跳出了叙事人为读者设定的隐喻和象征性阐示,而是从文本的整体时序和局部特征之间捕捉女主人公原始生活事件,结合弗兰克•欧康纳的短篇小说理论,重读文本,指出文本再现了在男权文化压迫下这位游移于社会边缘的有血有肉的普通女子的幽闭的心灵和孤独的生存状态,这期间艾米莉有过抗争,但最终还是孤独一生, 艾米莉本人就是一朵美国南方男权樊篱中的枯玫瑰。
著名的短篇小说评论家弗兰克•欧康纳认为短篇小说往往关注于那些孤独地游移于社会边缘的小人物的生存状况,尤其是凸显他们强烈的孤独感。③佩里在其《小说研究》中也指出,不论是果戈理的《外套》还是福克纳的《纪念爱米莉的一朵玫瑰花》,不论是麦尔维尔的《文书巴特比》,还是劳伦斯的《木马赢家》对弗兰克•欧康纳所谓的孤独地游移于社会边缘的小人物的生存状况刻画得极为深刻。④爱米莉这位社会边缘的小人物出生于南方没落的贵族家庭。我们打破文本的“时序颠倒”的叙事顺序,将文本的整体时序和局部特征相结合,可以看出小说背景置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历经变迁的美国南方的一个普通小镇。爱米莉居住在19世纪70年代的古老屋子,“在汽车间和扎棉机之类的东西侵犯了这一带庄严的名字,把他们涂抹得一干二净,只有爱米莉的屋子独存,四周簇拥着棉花车和汽油泵”⑤,屋子里的“壁炉前已经失去光泽的画家架”和“已经失去光泽”的镶金拐杖头都表现出这个没落贵族的家庭曾经的辉煌。在一个正历经变迁的年代,爱米莉的一切都与古老的、农业的南方息息相关,这位社会边缘的普通女子又悖论地成了传统的南方价值观念的承载体。 “骑士精神”和“淑女风范”是美国南方人引以为荣的文化传统,在南方家庭伦理思想中,父亲是一家之主,家庭首脑地位是不可动摇的,爱米莉的父亲这位顽固守旧的封建贵族卫道士,女儿被他塑造成标准的“淑女”形象。在镇上人的记忆里,父女俩被看作是“一幅画中的人物”:“身段苗条、穿着 白衣的艾米莉小姐立在背后,她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背对艾米莉,手持一根马鞭,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手持一根马鞭”的故事源于一个古老的传说,马鞭是前辈们赶走女儿们不受欢迎的求爱者而使用的武器。也正是父亲“手持一根马鞭”“赶走了”她所有的追求者,使她在三十岁时还孑然一身。除了父亲,没有其他人闯入她的生活,这也造就了爱米莉孤独的心灵世界。
父亲对爱米莉的“干涉” 和掌控还与旧南方根深蒂固的清教妇道观密切相关。基督文化中,“妇女被看作是地狱之门,万恶之源。”⑥妇女在基督教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在清教徒中更是这样。美国南方正是清教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区域,在那里妇女的贞操看得出比她们的生命乃至她们作为人的价值更为重要,妇女的“罪恶”莫大于她们代表的性欲和“淫荡”。在南方妇女之所以可爱是由于她们的“纯洁清白”,而一个“纯洁”的妇女应该没有激情,应该没有性欲,应该像“冰块一样冷峻”⑦,于是女性正常的渴望爱情的欲望和激情遭到压抑。在加尔文教清规戒律和男权思想的束缚下,艾米莉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牺牲品。在父亲将身边的青年男子都统统赶跑的时候,没有人了解她真实的内心感受。对爱的渴望是每一个豆蔻少女的自然情怀,艾米莉不过是善于怀春的普通女子而已。当有人问福克纳该故事是否源于他的想象,福克纳的回答是:“当然是这样, 但是少女们都梦想有一个恋爱的对象,这是故事存在的前提。”⑧可以看出福克纳所表现的是一位渴望爱情的普普通通的众女子之一。但她却因为 父亲的“过度保护”丧失了普通女子应该拥有的正常生活。艾米莉虽然普通却又极其特别,她的孤傲与怪诞让人过目不忘,短篇小说“因其形式短小所以刻画人物时常常集中于那种独一无二,让人一眼便能注目的特别人物”⑨,唯有如此,艾米莉,这位社会边缘的小人物的孤独的生存状态才会发人深思。
屈从于父权、在父亲“过度保护”的阴影里成长,艾米莉对外封闭的心灵也成为了孕育“怪诞”的暖箱。她傲慢、蔑视他人,“年近30尚未婚配”,被镇上人看成是偶像, 是纪念碑,体现着南方的“传统”和“义务”。爱米莉和周遭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环境是不和谐的、矛盾的,同时也是柔弱的,她必须从父亲那里寻求到庇护。在封闭的世界有父亲的“保护”,尽管孤独,倒也觉得安全。在父亲去世时,封闭世界的“安全符”轰然倒下,爱米莉拒绝面对现实,认定父亲没有死,拒绝处理父亲的尸体。在她幽闭的心灵里,内心的孤独在逐渐吞噬着她的灵魂,她抓住父亲的尸体,也是同命运进行的抗争:“我们还记得她父亲赶走了所有的青年男子,我们也知道她现在已经一无所有,只好像人们常常所做的一样,死死拖住抢走了她一切的那个人。”
父亲去世后,大病一场的艾米莉,幽闭已久的心灵尝试着向外界敞开,“剪短了头发”,“看上去像个姑娘”,没有父亲的“保护”,她终于可以挣脱南方淑女的形象,尝试着过上正常女子的普通生活,她开始大胆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她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爱上来自北方新英格兰的筑路工人荷默。 “这位北方男子的粗犷与豪放无疑给她幽闭的心灵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⑩,然而将她尊为纪念碑的小镇的人们一反常态,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认为这是全镇的耻辱,也是青年的坏榜样,深信她堕落了,“我们”设法去挽救她,迫使浸礼会牧师去拜访她,写信给她的亲属。可以看出,镇上的人们,在他们将她看作纪念碑、义务、象征的同时,就已经拒绝承认她是一位普通的有血有肉的、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的女性。在这里南方、北方价值观念发生了冲突,他们不能容忍象征南方传统价值的爱米莉嫁给一个“北方佬”,爱米莉又注定是价值冲突的牺牲品。然而艾米莉不顾流俗,依然故我,跟荷默自由出入。其实这是孤独的爱米莉在奋力把握人生中唯一的一次获得爱情、摆脱孤独的机会。早年由于父亲的干涉,爱米莉的青春年华“流水落花春去也”,逐渐成为一个“老姑娘”,加上门庭的败落,她多年与外界的隔绝等因素,根本没有再寻觅到门当户对的婚姻的可能。福柯说:“社会中存在着一整套衡量、监督、纠正反常事物的技术与制度,而人们总是害怕成为病态的一员,于是就产生了一种约束机制” ①,而爱米莉依旧我行我素,为了抓住生命中唯一的一次爱情,她并不在乎自己是否被看成病态的一员。
当荷默最终背弃她,爱米莉唯一的一次拥抱爱情、摆脱孤独的梦想也就被彻底击碎了,因为荷默“他本人说过他是无意于成家的人”。对于荷默来说,和爱米莉的恋爱不过是逢场作戏,这位老姑娘不过是他暂时的“玩物”而已。可以看出在男权社会里男性永远是欲望主体,是主动的、自由的,即便荷默只不过是个“拿日工资”的北方佬远非南方的贵族,女性则只能是被动的欲望客体,无法在情感生活中主动地驾驭男性。但是当爱米莉确信荷默要弃她而去的时候,害怕孤独的她选择了用毒药将其毒死并将尸首锁在阁楼上,同尸体同床共枕达四十年之久。爱米莉的疯狂举动其实颠覆了男权社会中对女性是欲望客体、男性是欲望主体的规定,她主动地选择了“永远留住他”,自由地追求了生命中唯一的一次爱情。然而爱米莉的颠覆和抗争是失败的,相伴她度过余生的不过冷冰冰的荷默的尸体。爱米莉再次蜷缩于自己封闭的世界里,牢牢地把握住在她看来确定无疑的安全的东西。她与世隔绝到极端的程度,她将一切都掩藏起来,直到她死后,小镇上的人才发现这个谜。
可怜的爱米莉,“为了不被背叛,她选择了毁灭,为了不被发现,她选择了掩藏,独自蜷缩于记忆和过往的问题里”②,从此时间在她的世界里依然停留在过去,“不能适应已经变化的世界这也从某种程度上促成她悲剧的产生”③。她公然拒绝交税,让上门催税的参议员们去找替她免税的沙多里斯上校,而沙多里斯上校已经去世十多年了。她还无视法律,坚持买砒霜而不遵循法律说出其目的,而药剂师对她无可奈何。“福克纳将她塑造成桀骜不驯,有意让她的叛逆精神颠覆小镇居民对她的象征性解读。”④如果说爱米莉在父亲去世前,屈从于父权、被动地生活;那么在父亲去世后,她试图主动地控制环境与社会抗争,然而最终,她还是孤独一生。事实上她的这种出世原则和与命运的抗争方式在男权主导的美国南方社会并不奏效,或许与外界现实的隔绝有助她生存下来,她也不过是一位活着的死人而已。昔日“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爱米莉小姐”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时,她已经是一位老妇人了,“看上去像长久泡在死水中的一具死尸,肿胀发白。”她始终没有摆脱孤独的困境。虽然叙述者从来没有对人物的内心进行直观的描述,但是人们越过草坪看到的灯光下爱米莉小姐的身影,她偶尔“在窗口晃过”的“像神龛中的一个偶像的雕塑般躯干”,这些比任何直接的描写更能烘托出她内心深处的孤独和凄苦。在爱米莉死后,人们进了40多年从来没有人见到过的楼上的房间,这是通篇小说唯一出现“玫瑰”的地方,人们在这里看到了玫瑰的影子,:“败了色的玫瑰色窗帘,玫瑰色的灯罩……”尘封了40 年的玫瑰色的新房是爱米莉与世隔绝后的精神寄托的地方,在这里有她守护着荷默的尸首并与之相拥抱的痕迹,枕头上留下的一缕她“长长的铁灰色头发”。这些在带给读者心灵强烈的震撼力量之余,我们更感受到“爱米莉对爱的顽强追求”,以及“最终采取极端的方式挽留自己心中的那朵“玫瑰”时所表现出的万般无奈与凄美”⑤。这也是在男权主导的美国南方社会里爱米莉做出的无奈的抗争命运的方式。虽然孤独一生,爱米莉还是勇敢地生存了几十年。正是由于爱米莉悲惨的一生,和在那样的环境中仍然渴望爱情、表现出坚韧的人性,福克纳给她献上一朵“玫瑰”,对她表示充分的同情乃至钦佩。⑥
在爱米莉作为一名有血有肉的普通女子的真实的现实生活浮出水面之后,我们不再受制于叙事的“魔力”仅仅将之读解成南方传统价值的纪念碑、隐喻与象征。事实上,我们看到了爱米莉这位在南方男权文化压迫下游移于社会边缘的普通女子的幽闭的心灵和孤独的生存状态。这期间,爱米莉有过坚定的抗争。她大胆地试图摆脱清教主义、父权对女性的束缚和压迫;勇敢地追求爱情,颠覆了男权社会中男性是欲望主体、女性是欲望客体的规定;她桀骜不驯、遗世独立。但爱米莉最终还是摆脱不了孤独和凄苦的生存状态,她本人正是一朵美国南方男权樊篱中的枯玫瑰。
作者系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苏州科技学院外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水涓)
E-mail:shuijuanby@sina.com
①②④参见王腊宝.当代欧美短篇小说的认知批评[J]. 当代外国文学2006,(4):126-133.
③ Frank, OConnor. The Lonely Voice: A study of the Short Sy. Ohio: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1962,P19.
④⑨转引自王腊宝. 怪诞、奇想与短篇小说[J]. 当代外国文学,2001,(1):115,119.
⑤《纪念爱米莉的一朵玫瑰花》,杨岂深译,文中有关译文不再另注。载《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刘俐俐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页。
⑥⑩⑤转引自郭国旗.《 献给爱米莉的一朵玫瑰花》之叙事解读[J].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4,(2):88,87,90.
⑦⑥肖明翰. 威廉•福克纳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187,198.
⑧②③Hans H.Skei. William Faulkner: The Novelist as Short Story Writer—A Study of William Faulkner Short Fiction,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p.112,p.124, p.112.
①转引自陈枫艳.生存还是毁灭——试从女性主义角度比较白先勇《谪仙记》与福克纳《纪念爱米莉的一朵玫瑰花》[J].苏州大学学报,2001年增刊: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