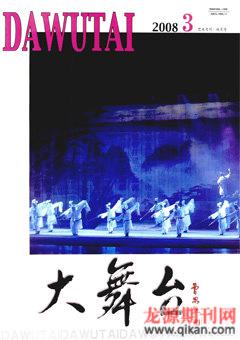笔与刀下的“金石气”
华若帆
自清代大兴碑学以来,“写手与刻手论”已成为近百年中书家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一方面使许多人得到了碑学的滋养,更关注碑派书法的审美情趣;另一方面也丰富了关于这方面的理论,以期借古开今,指导我们书法临习创作。作为书法学习的后辈,我也整理了些前人的资料,浅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与书卷气所对立的“金石气”,是一种苍茫、浑厚、朴拙的表现样式,而碑就是具有了这种天性。从书法的本体来看,这种“金石气”的产生,一是碑石本身的缘故,它的石质决定了它本身的硬度、气度,体现了刀刻的趣味;二是拓片的视觉效果。我们一般所见拓片黑多白少的视觉反差,又使人们心理“有一种寒冷的感觉”或是黑色的冷漠、威严。
说到“碑”,原本是古代文字铭刻的一种形式,大多指刻有标志性或纪念性文字的竖石,而在《说文解字》中也有记载,早在先秦时,碑上是没有文字的,仅是竖在地上的石块,有的观测日影辨别方向识别时间,有的用来系牲口,而后用途最广泛的是设在基地上的碑,是用来牵引棺下葬的,所以现存的东汉石碑以碑首大多还保留着圆形的“穿”。
(二)“碑”的美感是来自于刻凿、锤拓。刻拓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刻是拓的先决条件,而刻在石头上,使拓的纸张拥有了本来没有的石质肌理效果。
在古代,碑大多是先由书写者用朱墨直接写在石上,然后镌刻的。《后汉书》载:“熹平四年,邕秦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这就是近年洛阳出土蔡邕亲自书丹上石的东汉《熹平石经》。至于实物,如清出土的所谓《王基断碑》,是三国时期的碑刻,并非断碑,初出土时,半截未刻的朱书仍在。书丹上石十分普遍,但不可不提的是摹勒上石。至梁隋时,就有将碑文书写于纸上,然后再另纸勾勒上石。后代碑刻基铭,虽皆用黑墨书碑文于纸上,仍依习惯署某某书丹,则书丹又为书写碑文别称。
而刻手一般都是不识字或无文化的工匠,有“百工”,其自周秦两汉后一直是一个很特殊身份的社会群体,与普通士民有所区别。他们掌握一定的技术手艺,世传其业,地位低下,不得改行,不得入仕途。他们在刻字时,通常都将每一个字的相同方向笔画一起刻成,然后再刻其他方向的笔画。比如《郑长猷造像论》拓片首行首字“前”刻了一半;第二、三个字漏刻;第二行首字“郑”未刻等等。出现这种现象,合理的解释是文辞在书丹后,刊刻时不小心或由于其他原因把字擦模糊了,而刻手不识字,故有未刻完和未刻的字。后来未请书手补完,也无人补刻,更无人验对,所以碑中出现了很多断笔、漏笔,甚至断字、少字的情况,是很容易推出原因来的。
一般石刻文化是以在行为上的分阶段逐步完成,至少两次(三次)成形作为基本特征。因此,在一方石刻中,书丹、凿刻这两个行为过程,又存在着相当大的变数。
碑刻大都先书再刻,但也有“不写而凿”的,如《侯太妃造像记》。研究龙门石窟艺术的专家宫大中先生认识:“其刊刻的自由无束,字句重复和字形笔画从不规范上来看,很可能是未经‘书丹,由刻工直接捏刀何石,刊刻而成的。又如东晋时很多墓碑只做假葬或辨识而用,《王兴之》、《颜谦妇刘氏墓志》、《孟府君墓志》等书刻,更是草率,字迹大小不称,点画错乱、漏刻,刀锋真露,刻得十分随意。
(三)碑版书法的字迹与原迹虽然有相当大的差距,但仔细想想,这种距离倒是一种积极的发挥和创造。这旨在自然中形成的,没有一点做作,也是我们出自主观的审美意识和艺术表现欲。碑版给我们的视觉效果不单只是剥蚀的石花,模糊的刀痕,更是它透出的那种雄浑石拙的“金石气”。
我们在临习的过程中,应当“透过刀锋看笔锋”,剥去刀刻这一层,看到笔刀的差异,否则就会被碑所“骗”。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北魏的墓志中的笔画,有很多方笔并使得整体似乎由“块面”构成的,也使大多初学者简单地认为写“魏碑”就只要大量(甚至是全部)运用方面、块面,于是就写得呆板,陈式化。也就犯了教条主义错误了,仔细比较那些墓志就不是如此了。
从书丹上不用刀镌刻,墨拓,除了观之,更深层地是如何用笔墨来体现到宣纸上,而这也是个相当困难的过程。在我们临摹创中,更要注意很多东西,下面就以自己经历浅谈几点感受。首先,应强调逆入回收,有块也有线,丰富作品的构成形式。其次,明白书从印入,借鉴刻印时刀口顶着石面朝前运行的道理,将笔杆往笔画、运动相反方向倾斜。笔画右行,笔管左倾,笔管上倾,笔锋始终顶着纸面运行,由此使辅毫受顶压之后张开,在线条两边划过,造成毛糙,产生浑厚的效果。再次,增加运笔时的提按动作,按下去行笔的部分线条就实,提起来行笔的部分就虚;增加运笔时的阻力,不让前行,竭力与争,手不期微颤,这样会因书写速度的变化而产生墨色的枯湿浓淡变化,表现出金石线条深浅不一的感觉。最后,注意在临习前更先要观“气”,将点体印象落实,在对点画结体和章法的处理上,在总体把握作品的精神状态,将观者打动。当然做好这几点确实很难。
但面对这浩瀚的碑林,想要去学习时,我们又应注意些什么呢?第一,像《王兴之》、《王闽之》诸刻,其落笔幼稚且笔笔是方角,刻得并不好,且大多学者认为此类为下品,我们若临习,可能人中并不能像学习《张玄》此类碑获益那么多,所以建议不深入临习为佳,但可作为“小菜”来欣赏。第二,像龙中造像中《孙秋生》、《朱橛》各品中,刻手虽佳,横画收笔还是有些切齐,看得出并非毛笔书写的原样,所以我们可以从中汲取意外情趣,写出毛笔原没有写出过的东西,增加趣味。第三,像《高归彦造像》、《刘岱墓志》基本上按墨迹刻出了圆势、方势,刻工较好,那么我们就必须尽力还原墨迹,并结合碑刻的金石趣味,去靠近原迹。
(四)众所周知,纸帛材料细腻,加上墨迹挥洒之时动作的灵敏,造成了纸帛书法的“书卷气”;石碑材料硬而粗糙,又加上斧凿刀刻之时取其大意,略而化之和作为工序的书丹、刀刻、锤拓过程的多环节性,导致锤拓书法的“金石气”质地。而我们面对碑去追求它们沉拙重涩的“金石气”时,又似乎看到了顽强,刚硬的行笔,如锥画沙,墨痕如刀,一点一点,刻切入纸,在这后面是率真厚拙的意趣,奇特神秘的意境、纯朴浑厚的意韵。在民族传统文化渗透的当代,对于碑刻“金石气”的理解,已不仅成为书家表现其性灵,张扬个性的手段,更是一种新的审美意味的发展。从“写手与刻手”问题上我们确实看到很多,因此把我们在书法艺术的审美上推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