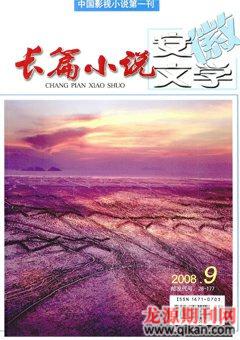堤坝上的心愿
梅海霞
那是一条窄而长的堤坝,微微隆起,像一道浅褐色的疤痕横亘在平坦的原野上。
虽然已是早春三月,我们到达的时候,却刮着阴冷的风,寒塘衰草,天地间一派苍茫,只有麦苗在饱满的积雪覆盖下,蓄积了一冬的能量努力地钻出大地,给农人一个年头的希望。
友人承包下这段堤坝,盛情邀我们踏青植树。下了大巴,踏上土地的那一刻,踏实的感觉真切地从脚底延伸到心房。
第一场春雨还没有到来,堤坝上翻开的土地干硬、粗糙,捏在手里有一种北方的质感,叫人想起荒山上的岩石,老农皴裂的手背。
河岸边躺着一捆捆纤细的杨树苗。翻地、挖坑的重头工作已经做好,我们只需要把树苗放进坑里,填上土即可,连浇水都不用。这是植树过程中轻巧而最有成就感的环节。来之前的晚上曾辗转反侧,民间有植树祈福许愿之说,许多父母为自己的孩子栽树,希望孩子像树一样茁壮成长。这是生平第一次植树,也该许个愿吧?愿千里之外的父母快乐安康?愿多病的爷爷健康长寿?愿身边的人能相扶到老?……终究没能想好,第一个愿该为谁许,就来到了堤坝。
短暂的手足无措后,一行人自由分组、分工,正式开工。久居城市,肢体功能居然退化得如此厉害。握着铁锨的手,笨拙地在土地上捣捣戳戳,胳膊好像怎么都使不上劲。面对土地的倔强,我觉得害臊。不是这土地和故乡的土地不一样,而是我已经忘记了该怎么和土地打交道。我只有虔诚地放下利器,用手一捧一捧地培土。友人说别用手,会磨伤。我说不怕。只希望洁净的土地多磨去些结在心灵上的茧子。低头、弯腰、俯下身。面对土地,真的不需要那么趾高气扬。等你直起身的时候,树苗就在你身后一行一行地立起来,把根伸向了大地的深处。
我终究没有在任何一棵树上许下心愿。因为当我把第一棵树放进土坑的时候,已被那些细弱的须根打动,它们的一端紧紧抱在一起,另一端努力地朝着土地的方向延伸、舒展,它们是那么渴望自由而轻盈地成长,而不是我强加于它们的一己私愿,不是那些人世间的束缚与背负。
我问友人这些树苗要多久才能长成大树?问完了方觉问题愚蠢,多大才算大树?那么就按可以砍伐售卖的标准算吧!起码得十年吧!十年?一时间不知道如何丈量十年的长度。十年里我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十年里这世间会有多少聚散离合?十年里天地间又有多少生命出生或死亡?十年对我来说太漫长了,而这些树苗将要在这段堤坝、这片土地上待上十年,不移不动。这十年里它们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努力地生长。它们耐得住十年的清寂吗?我显然多虑了,它们耐得住,生性使然。而比树更耐得住的是守护它们的人。
友人望向堤坝的尽头,神色凝重地说干旱和洪涝也许免不了吧!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会照管好这片林子。友人的目光在身边孩子的身上停留片刻,又望向远方。他的身影让我想起杜拉斯的《抵达太平洋的堤坝》,一个母亲为了生计,为了三个孩子,倾其所有买下太平洋岸边一块贫瘠的土地,在太平洋潮水肆意蹂躏的土地上绝望地挣扎,却始终无怨无悔。
身体陷进大巴舒适的座椅中,乏累得恍恍惚惚生出梦意,忽而觉得自己的身体慢慢摊开、延长,变成了一段堤坝,千百根纤细的杨树根须扎进我的皮肤,随我的经脉一同延伸,我荒芜的身体一行一行地绿了起来。
责任编辑鲁书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