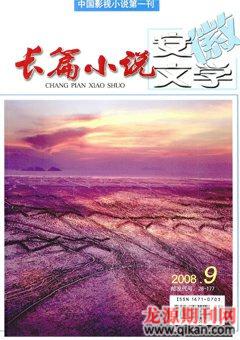打鸟者的忏悔
刘伯谦
俗话说:宁吃飞禽四两,不吃走兽半斤。
童年打鸟不一定是为了吃它,更多的是一种捕猎后的刺激。
那时最原始的工具是弹弓,子弹是随地可拾的石子。把石子安放在橡皮条的中间,右手拉弓,左手拉开包裹着子弹的橡皮条,瞄准了树上房屋上的鸟儿,猛然弹开,中弹后的鸟儿就会从空中落下。当然成功率不是很大,更需要日积月累的训练。小时候跟在那些大孩子的身后帮他们捡鸟,似乎是一件很光荣的任务。
后来有了汽枪,打起鸟来比弹弓现代化多了,我很想能拥有一杆汽枪,然而当时我买不起。
依然是跟随在别人后面,依然是捡鸟的干活,屁颠屁颠的。遇上持枪人高兴,一不留神让你打上一枪,那感激涕零的模样,肯定比那跟在皇军后面的汉奸毫不逊色。
记得那次去黟县演出,空闲时,我们又干劲十足地重操旧业了。
黟县的老剧场后面是一排排古民居,古老的瓦檐下是麻雀们最最温馨的家。那雕刻精美的青石门楼门罩上是麻雀尽情表演的舞台。它们万万没有想到,死神正不知准备亲吻哪位可爱的小天使?
民居的旁边,就有一条水渠,清澈的溪水潺潺流过。县城的居民饮用洗涤都靠这条清渠。麻雀的欢叫声引导我们的视线只投向空中而没有注意到脚下。
持枪人端起汽枪,瞄准着那相互追赶嬉戏的鸟儿,屏住呼吸,扣动枪栓,哇,打中了!但只见这只中弹的鸟儿在即将落地的一瞬间,它又顽强地重新跃起,向着水渠对面飞去。这时的我非常英勇非常大无畏地直追而去,谁知才跑两步就掉进了沟底。我的狼狈模样决不亚于《小兵张嘎》里的翻译官。小伙伴们看着我落汤鸡似的样子,再也顾不上去追赶那只受伤的鸟儿,一个个捧腹大笑不止。等他们把我从水渠里弄上岸来,这才发现,后背让渠边的石头划了一个长长的口子,鲜血顺着后背一直流到脚后跟,地上殷红一片。
这个伤口,持续了很久,直到现在还留有一块疤痕。
这是十四岁留给我永久的纪念。
谁知我竟然死不改悔,当我有能力买一支汽枪时,我立即“不当汉奸当皇军了”。
那时候剧团下乡演出,去的都是边远的山区,那些地方生态极佳,鸟类自然繁荣昌盛,种类很多。麻雀八哥是常见的鸟,另外还有画眉、黄莺、黄鹂、斑鸠、乌鸦。竹鸡、野鸡也时而遇见。珍稀鸟类还有相思鸟、蓝嘴长尾雉……
下乡时把汽枪藏在“把子箱”里。把子箱是用来装刀枪剑戟的,里面的东西全是用来演出的道具,只有这杆汽枪才是真家伙。演出间隙,情趣颇好,便扛着汽枪出发了。每次出门,收获总是大大的,最多的就是麻雀与八哥。回来之后,拔毛开膛是女演员们的活儿,洗净晾干,将鸟们放进酱油中浸上数日,再拿到太阳下晒上几日,这样集少成多,演出几个点之后我们就可以大饱一下口福了。
鸟肉烹饪有很多讲究,生姜、大蒜、茴香、桂皮、黄酒、干辣椒一样不可少,最好再有一两斤新鲜猪肉。鲜猪肉红烧风干酱鸟肉,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在哪家酒楼饭店见过这道名菜,这应当算是我们的专利了。
我还曾像打飞碟的运动员一样打过一只飞翔中的八哥,其实并非我的射击技术有多高超,只因八哥太多,从割过稻子的田里轰然飞起一大片,我举枪便射,瞎猫碰到死老鼠而已。
记得有次在休宁流口演出,出猎时一只山鸡让我遇上了,那漂亮的羽毛,斑斓的色彩,令我激动不已,当我举起枪野鸡出现在准星里的那一刻,我犹豫了。我被它的美丽震慑了,放下汽枪,无声地看着它钻进浓密的灌木丛中。
漂亮的女人是祸水,这话也不尽然,漂亮有时会招来是非有时也能保护自己。人是这样,禽兽也不例外,只不过逃过我子弹的这只野鸡是雄性而并非雌性。
与美丽相悖,丑陋总非好事,一只乌鸦就在我枪口下壮烈地牺牲了。
一天,我们正在团部组织学习,大院外传来阵阵乌鸦的鸣叫,我上楼跑进临近的一个窗口,只见那只乌鸦立在临窗的一棵树枝上。我举起枪,屏住呼吸,在我觉得把握十足的情况下,我扣动了扳机,一声惨叫,它从树枝上掉了下来,我赶紧下楼跑出大门去捡那只中弹的乌鸦。
当我在菜地里看到它扑扇着双翅,我被它那临死前挣扎的惨状惊呆了,它是那样地痛苦,那样地想重新飞起,然而,子弹射中了它的翅膀和胸膛,鲜血直淌,不一会便没了气。始终,它没有闭眼,那死不瞑目的模样让我至今想起来不寒而栗。
一整个上午,我们住处的四周乌鸦的鸣叫声不绝于耳,久久在空中萦绕。那是它的伴侣或是它的子孙在深情地呼唤,在焦急地寻找。最后,变成一声声呜咽,一声声哀鸣。叫得我心里发怵头皮发麻,中午同事们还是把它红烧了,我一筷子没敢动它。
从那之后,我经常会做同一个梦:在一大片一大片古树与古藤缠绕的森林里,有各种各样的鸟在无忧无虑地自由自在地玩耍,嬉戏,当我出现在森林里的时候,鸟们都逃得无影无踪。我去追它们,但无论我怎么努力,也挣不出藤蔓织成的罗网,渐渐,不是水漫到腰际便是在泥潭里挣扎,怎么也走不出阴森森的大森林。
我是无神论者,我不相信有什么因果报应之类的神话,但我的梦是确确切切的。肯定是那只乌鸦的死给我的震撼太大、印象太深刻了,我开始觉得我是在犯罪。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去打鸟。
在我们民间的意识中乌鸦被视为灾星,而在澳大利亚等国家乌鸦是一种吉祥鸟。麻雀也曾一度被戴上“四害”的帽子差点斩尽杀绝。当然我的伤害不能用民间意识或者决策者的某些错误来作为我的辩护词。
今天,我说了这些打鸟的故事不是为了显耀,也并非为了消遣,而是为了忏悔,为了谢罪,深深地忏悔与谢罪。向鸟们,向屈死在我枪下的鸟儿们。
责任编辑鲁书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