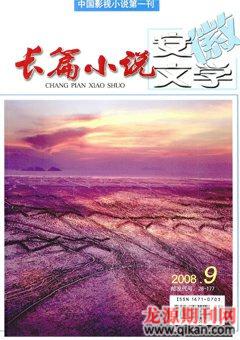泥土下面的村庄
高家村
时近清明,我沿着村后的一条小路走向墓地,我的亲人——爷爷、奶奶还有一个早逝的堂哥,他们静静地沉睡在这里,再不回来。我不知道在泥土下面是否真的有一个安静、冷清的村庄,但是,我宁愿相信他们是在我所不能感知的地下以另一种方式生活着,他们生活在泥土下面的村庄里,就像我们一样。多少年时光匆匆而逝,渐渐冲淡了我对他们的印象,但只要走近这里,他们又都会在我的记忆深处重新复活,栩栩如生。
在逝去的亲人中,奶奶是第一个先离开的。奶奶走得很突然,夜晚睡去后,第二天再没有醒来。记忆中奶奶的身体非常瘦弱,她总是在忙一些家务活,没有见她清闲过。奶奶的一生大半都是从苦日子里熬过来的,母亲说奶奶就像油灯一样,油熬干了,生命也就结束了。安葬前我们最后一次向奶奶道别,那是我有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凝视一位亲人的遗容,奶奶无神的双眼似是透露出无尽的遗憾和无助!
奶奶就被安葬在村后的那片墓地里,紧挨着那些祖辈们的坟墓。那些坟墓整齐地排列着,那是他们的房屋。这些房屋构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村庄。平时这里是宁静的寂寥的,祖先们沉默着,生前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劳作,死后他们也成了泥土的一部分。
在这些排列整齐的坟墓前边,有一座又矮又小孤零零的坟墓,那里收留着年轻堂哥的魂魄。小时候,我们总是形影不离,下地割草、拾麦,到离村一里多路的东塘里洗澡。后来我随父亲到离家30多华里的一个古镇上学,但只要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堂哥,还像小时候一样,谈谈各种有趣的事儿和各自的理想。但那次回来,我只能看到一座新坟前飘飞的纸灰,铁锨挖出的新鲜泥土在夕阳的余晖里闪着冷冷的光,刺痛了我的眼睛。
就像每次回来一样,我在离他最近的地方坐下来,但他却长眠在遥远的梦境里,他的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了20岁。
一些青草在堂哥的坟墓前茁壮地生长着,就像他曾经鲜活的生命。
堂哥的匆匆离去,第一次让我感觉生命是多么的脆弱和无常。
接下来是大姨的去世。那是接近年关的一个下午,我正在远方的一个城市里坐着,窗外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我坐在室内靠近窗子的一隅,忽然就感觉浑身不适,这种无来由的感觉说不上是心理的还是身体的,突然就想回家了。当我回到家里时,就听到大姨走了的消息,而且是喝了农药走的。乍一听这个消息,我的心情难以用意外和悲痛来形容,大姨那么开朗、爽快的一个人,怎么会想不开说走就走了呢?及至赶到大姨家时,看到堂屋当门一些烧过的纸灰,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不见了大姨的身影,似乎才从懵懂状态中醒来。我知道大姨是最疼我的人,但还是没敢看被单下大姨的遗容,尽管我非常想再看一眼她慈祥的面容。大姨没有被埋进祖坟地里,这里的规矩“凶死”的人是不能进祖坟地的。看到大姨远离墓地孤零零的一座坟茔,听着姨夫和表弟妹们的哭诉,悲哀之余,心中陡生无限感慨:虽然我们就站在大姨的跟前,但她却连一句话也不能和我们说了……
咫尺天涯,这是世上最切近而又最遥远的距离了!
家族中每一个亲人的逝去都会促使我好长一段时间对生命毫无意义的思考:他们离开我们世俗意义上的村庄,住进了那些在贫瘠野地里泥土垒成的村庄里,会不会害怕?会不会想念与他们不同世界里的亲人?他们能够感知我们对他们逝去的悲伤和思念吗?
这些思考毫无意义,没有人能够回答。一望无际的淮北平原上,庄稼在各自的季节里依次生长,乌鸦一次次从天空掠过。这阔大的空间只适合飞鸟和想象存在,先人们沉默着,给墓地的空气平添了几分凝滞与肃穆。
除了屈指可数的几种顽症,我们所处的时代,使我们对生命可以有几分优雅和坦然。但是,外爷和爷爷都是自己以一条绳索结束生命的,我想像不出他们离去时,对生命到底是自信、坦然还是无奈、茫然?
作为历经生活磨难的老人,他们有自己朴素的人生观。我无从知道他们对生命的态度,也无法透彻地理解他们对死亡方式的选择。人们常说上吊死去的人很恐怖,舌头会伸得很长。但外爷和爷爷的遗容都很安详,他们就像正在沉沉地睡去,马上就会醒来一样。
外爷是农村里那种与世无争、老实本份、木讷少言的人。我上小学前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那时外爷在生产队里喂牛,午饭后外爷总是会领着我去牛屋,他给牛槽里添草加料,我站在他身后,闻着牛料的香味,看着那些吃得津津有味的牛们。但是性情温厚的外爷还是选择一种决绝的方式离开了,只是因为一点小事和外婆争执了几句。
爷爷给我的印象是很和善的一个老人。在村里,别人和他开一些善意的玩笑,他总是呵呵地笑,从不答话,他也很少主动和别人说话。及至后来慢慢长大,我觉得爷爷的性格还是很倔强的。奶奶去逝后,他一直坚持一个人住。自从外出上学和工作后,我就很少和爷爷在一起了。有时回到家里,就到他住的小院子里去,很想和他说说话,可到了跟前,除了几句问候外又往往没有别的话题,但我心里总是感觉和爷爷很亲近的。
爷爷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还是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时,在门前的大槐树下,他问我学的什么,问我“上海”会不会写,我只会写“上”,爷爷又教我写“海”。后来好长时间,我都认为爷爷用手指写在土地上的“海”字,是世上最稠最难的字了。
爷爷走时没有任何征兆,那时他已八十三岁高龄,身体健朗,无疾无病,也没有生活上的特别的困难,爷爷离开的方式让我困惑了好久。不久前一个细雨绵绵的午后,我无神地坐在窗前,百无聊赖中随手按下多日不听的录音机的放音键。立即,悠远苍凉的蒙古长调从录音机里飘出来,那是十年前我去内蒙古参加一个诗会带回的,那种原生态的充满生命质感的声音飘散在房间里。我似乎突然感悟了爷爷——是呵,相对于乡村寂寥、单调而漫长的日子,生命中的艰难和困苦也许更容易度过些。爷爷是从苦日子里趟过来的,他不怕苦。而我们总是满足于物质赡养,疏忽于对老人的精神抚慰。想到此,泪水涌出了我的眼眶。
爷爷走后不久的一个黄昏,我走进爷爷曾经生活过长满荒草的院子。泥土垒成的房屋,泥土垒成的院墙,夕阳把余晖洒在颓废的墙头上,四周一片寂静。这是爷爷曾经的家园,几乎和他生前一样安静和寂寞。生活中有些遗憾是无法弥补的,譬如,我总是在亲人逝去后才觉得应该给他们更多的关爱……
生命轮回,生生不息。那些逝去的亲人是否还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散落在淮北平原上的那些墓地,我们的亲人就沉睡在他们生活过、耕耘过的土地里,那里收留着他们的魂魄和骨殖,在泥土下面,有亲人们的村庄,有他们的家园。或许,他们坟前绽开的一株小花,生长的一棵野草,刮过的一阵微风,都是他们存在的方式,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传递着对我们的爱与思念,也感受着我们的爱与哀愁……
责任编辑赵宏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