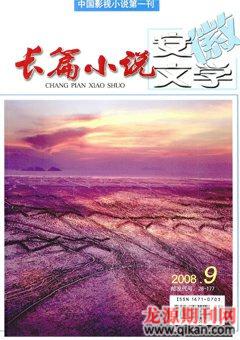丰大圩
梅素娟
一百年前,丰大圩是一片无垠的芦苇滩,浸泡在水泽里,连个名字也没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无为县遭遇灾荒,爷爷的父母带领家小,离开故土,加入到逃荒的人群。这支逃荒队伍沿长江西上,一路上忍饥挨饿,淋雨浴风。经过的村落家家紧闭门户、猫狗噤声。为了弄碗饭吃,这些异乡人偶尔也打家劫舍。一日,到了一处河湾,此地处皖、赣、鄂三省交界,由于长江多年水患,这片低洼地积水成湖,芦苇密集,野鸭成群。但并无人丁,官府对此地亦未予理会,只有北部山岗地带的土著民偶尔来此猎鸭。且说这群异乡人到达此地后落脚歇息,待了数日,未见官府或土著居民来撵,不禁欣喜异常,于是占地为村。说也奇怪,自从这群异乡人落脚于此,泽水很快退去,露出一个锅形的圩子。圩子的外围是一条古称雷水的长江支脉,此水把圩子的西、东、南三方裹在怀中,唯留出北方与一片山岗地相连。雷水两岸杨柳遍生,这群定居者决定给新村落取名“杨湾”,有个胆大的土著猎人前来通好,告诉他们说,已经有别处的外乡人将这一整片的河湾地称为“杨湾”了。于是改称“丰大”,取其年年丰收、子孙绵绵之意。然后加固圩堤,清除芦苇,开垦蛮荒,播种耕作,从此一代一代,在此繁衍生息。
爷爷是他父母的第三个儿子,他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姐姐。他的大兄有远大理想,梦想成为乱世英雄,曾是当时国民政府的一个青年新秀,但沉迷情场,得相思病死了。二兄受了莫名打击,时而清醒,时而迷糊,某日把自己悬在梁上,再没下来。四弟酷爱书本,日夜与发霉的纸张、暗弱的青灯作伴,终于二十岁时瞎了眼睛,从此不再读书,但却能预言天下大事。爷爷是智力最下的那个,所以不得父母喜爱,但他的农活做得很好,开垦的荒地极其广大,在政府注意到这个村落之前,开垦者完全拥有他的劳动所得。爷爷对开垦土地的热爱使他的饥民父母成了梦想中的地主和地主婆,似乎一夜之间,这对一直饿得前胸贴后背的夫妇突然意识到他们的前胸可以跟后背分家了,因为他们最看不上的那个儿子为他们挣下了最宝贵的财富——土地。这土地似乎有不断分娩的能力,为他们带来了充足的粮食、绵绵不断的长工、短工、女佣。再后来,爷爷率领一群雇工将一块积水低洼地挖成了一个大大的湖泊,种上莲藕,放入鱼苗,农闲时常荡舟其中。民间有“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之说,但不知何时此语之后又添了如下两句:“九个湖北佬,抵不上一个无为佬。”虽然阿三认识的无为人中并无几个做了惊天动地的伟业,但一想到爷爷的发家史,还是觉得这话有些道理。(这句话在民间有实证,八十年代刚刚改革开放时,第一批进入北京的保姆队伍就来自安徽无为,当然,将雇主家的电器大件用卡车拖走的也有无为人。无为人似乎从来不想统治世界,他们没有那么远大的理想。他们只是沉在社会的底层,做底层的人上人,他们最渴望的是富,不是贵。)
爷爷某天在去往赌场的路道上,远远见他的大姐浑身泥土、衣衫不整地爬行在村外的路上,她来告诉他,日本人来了,砍了他姐夫的头。然后日本人果真来了,很快建立了新的政府。爷爷和他的村庄似乎没有民族意识,他们只求日本人的大刀跟他们的头保持距离,他们积极服劳役,为日本人建设军事工地。爷爷为日本人挖战壕,他表现得一直很卖力,但有个跟他搭档的日本小兵常常欺负他,直到有位日本军官阻止喝骂了那个小兵。爷爷对这军官一直心存感激。
日本人被赶出去之后,爷爷以为天下要太平了,他说不管谁收租子,只要收租子的给他一条活路。但是收租子的脸孔换得太快,甚至土匪也来收租子。
有段时间,爷爷自己也做了土匪。那时土匪太多了,村里成立了大刀会、小刀会,土匪一来,两会成员赤膊上前,同时口念咒语“刀枪不入”。我问爷爷是不是刀枪不入,他说人都快死光了,还刀枪不入。看来咒语挡不住土匪的刀枪。爷爷说对付土匪的唯一办法就是也当土匪,在土匪抢我们之前先抢他们。土匪抢不过丰大圩的汉子,就逃走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奶奶,所以她是永生的。奶奶其实比我年轻,年轻得多。她永远23岁,多美好的年华。她的家在华阳河边,此河是长江中游的一条支流,又称雷水或雷池,古语“不敢越雷池一步”即指此地,她常在水边跟妹妹嬉水,虽然常常饿着肚子。奶奶姓王,行二,被唤作王二不子。二不子是此地土语,就是老二的意思。她的父亲是清末的一个落魄的秀才,无力种田,只能举家食粥,后来粥也没了,就卖了二女儿。因为姿色尚可,卖的价钱可以高一点。于是,奶奶来到了丰大圩,那年她十四岁。
她颇勤快聪明,手脚又麻利,洗衣做饭从不误时。她心地良善,待人极好,主家与工友都十分喜欢她。主家的三少爷看上了她,十五岁时就嫁给了这个大她两岁的少爷。从此,她更累了。
夫家是合族生活,人口众多,加之长、短雇工,每日有百口人吃饭。
王二每日寅时起床,用一口巨灶作饭。梅家由饥民而为地主,所以并不歧视雇工,不讲究分锅而食。王二做好饭后,就收拾家具,安排田地事宜。然后浣洗如山的衣被,再匆忙舂谷涤米磨面,挖藕摘菜,准备下一顿饭食。如此不辞辛劳,王二无一丝埋怨,反而甘之如饴。
王二的丈夫嗜赌,其他几房本家一看不妙,即求分家。王二是三房,分得两头牛、三间草屋、数亩薄田、一湾藕塘。如此,也可度日。可惜好景不长,无论王二如何劝导,三爷也不改赌性,不久,家财败尽。恰逢长江水患,夫妇逃难他乡,重为饥民。水退之后,还归家园,租地为佃,聊以继日。
王二在逃难途中,诞下一子。生活辗转,饱饥无时,产妇奶水不足,婴孩嘬吸如命,不日,乳破,疼痛异常。此时孩子不盈数月,腹内空空,日夜啼哭。王二每日以绳布将小孩子捆在背上,以一破碗覆乳,使之麻木,好减轻痛感。如此,坚持在田间耕作。间隙帮人洗衣洗被,以求换得一把谷米,给儿熬粥。丈夫虽失少爷身份,但不失少爷架子。加之相貌堂堂,就少不得女人勾引。于是,日夜不归。王二仆妇出身,对丈夫始终敬畏,难得丈夫回家,即十分欢喜,从左邻右舍借来鸡蛋米面,做好一碗,不言一语,走到丈夫身边,双膝跪地,低下头去,双手高高举碗。
天下动荡,日本人占领村庄不久,一家又被撵了出去。从此乱兵散勇,神出鬼没。乡人无心耕作,只知今日生,不知何日死,田地荒芜,家业凋零。王二无田可种,此时又诞下一女,嗷嗷待哺。丈夫亦已返家,不敢逗留户外,抓壮丁的常夜袭庄户,夫妇日夜警醒,全家大眼瞪小眼,缸中无米,腹内饥肠辘辘,庄外枪声零星,只怕性命难保。如此担惊受怕,怎奈腹响如雷,好歹做个饱死鬼,也好有力气投胎,思想已定,夫妇商议,王二出门去做乳母,三爷留家,男人力气大,有个风吹草动,也好双腋夹子,逃之夭夭。
王二含泪别子回到华阳镇,到了一户富家做起乳母。不料天有不测风云,不几日,王二咳血不止,主家疑为痨病,急忙辞退。数九寒天,王二挂个破包袱,离了主家门,徒步返家园。天寒地冻,北风呼啸,百壁之遥,王二走了整整三天。归家后,全家啼哭,苍天已死,黄天不立,左右环顾,无一援手。
一九四九年初,王二以剪破喉,魂遁无忧乡。此时,大儿六岁,小女两岁。
自从父母去世后,爷爷就被人引诱去赌博,他从来没有赢过,以最快的速度败光了土地和一切财产,只剩下一间栖身的茅屋和一只大南瓜。爷爷对着那个大南瓜看了一天,决定像他二哥一样找根绳子把自己捆起来。那时他的大儿正在村外和几个孩子一起玩耍,刚会扶墙走路的小女已卖给同乡的朱姓地主做了童养媳,他的妻子在几个月前用一把剪刀剪断了自己的喉咙,仅剩的那个瞎眼兄弟也早已分家另过,所以家中只有他一人,他有充分的时间把自己挂起来。不过,他得先给自己弄根结实的绳子,爷爷是个一米八的大个子,一般的绳子难以成全他的心愿。但绳子的事难不倒爷爷,一个高超的庄稼汉首先得是个搓草绳好手,爷爷自然担当得起这个称呼。当爷爷在破屋里认认真真搓草绳时,几个大兵低头钻进了他的草棚。大兵是来动员他去划船的,爷爷嘴张了半天才弄明白,那些震耳欲聋的炮火不是他装作聋子就可以听不见的。天下要换了,爷爷说自从大兵来家里动员他去长江的大浪里划水船,他就特别庆幸自己败光了家业。日本、土匪、老蒋都不放过富户,这新来的自然也不会例外。果不出所料,新政府成立以后,爷爷享受了光荣的贫民待遇,而那些拐他去赌场继续将家业发扬光大的几个乡绅,被拖到县府的北街冲了,一切财产充公。冲了就是被枪毙了,丰大圩的村民并不因为远离故土,就入新乡随新俗,他们的风俗与语言都没有改变,“冲了”是最原汁原味的无为话。
责任编辑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