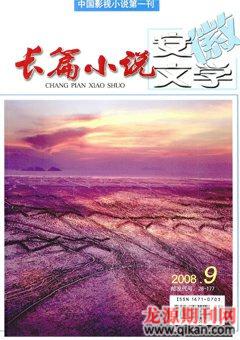我的父亲
姚中华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个年头了。三年来,对父亲的怀念不但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淡漠,反而越来越浓烈,记忆的闸门常常因看似父亲的一个背影,听似父亲的一句声音而打开。父亲走了,把思念留给了我们。这种思念不仅仅是缘于血脉里流淌的亲情,还有一个儿子对父亲的崇敬,一个步入中年者对父辈的理解。三年来,总想写一些怀念父亲的文字,每每拿起笔,却又放下。父亲的一生,我不知该从何写起。父爱就像一座山,平时只感知它的伟岸,真正走近它、审视它,却又不知选择哪一条路径。但这种情绪又总是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欲罢不能。我渐渐明白,无论我行走多远,永远忘不掉父亲那双已经放开的大手;无论生活历经的是阳光还是风雨,永远都不会忘记父亲曾给我们那温暖踏实的怀抱……
父亲出生在巢湖农村。由于家境贫寒,不满20岁他就背着一床破棉被只身一人来到芜湖,招婿到外公家。父亲一无所有,有的只是一身使不完的好力气,年轻的他能挑起几百斤的担子不歇一肩走几十里地。那时外公家种了十多亩地,为了来年有个好收成,大冬天,父亲赤着脚下河捞塘泥肥地。人家两个壮劳力合伙捞一船,父亲一人捞一船。正因为如此,父亲深得我外公喜爱。父亲不满20岁,外公就让他和母亲成了亲。
父母一生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孩子。为了把我们养育成人,在那个生活十分贫困的时代,父亲一年四季奔波在田野里,想靠一双勤劳的双手,换取生活中的希望。每年春节刚过,大地还没有开冻,父亲就扛起铁锹来到田头,筹划着一年春耕。夏天烈日炎炎,父亲带着尚未成年的哥哥姐姐在齐腰深的稻田里探苗拔草。哥哥姐姐脸晒得通红,一到晌午,就放慢脚步,想回家歇歇。父亲见了就咳嗽一声。哥哥和姐姐知道父亲没有回家的意思,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在我的记忆里,多少次,外面雷雨交加,父亲赤着双脚奔走在泥泞的田埂上,探水护苗,生怕雨水淹坏了庄稼。有一次下大雨,父亲扛着铁锹正走着,突然一个炸雷打在眼前。不知是惊吓还是其他原因,父亲一头栽倒在水田里,半天才爬起来。回家后,父亲向母亲说起这件事,母亲吓出一身冷汗。从此,每逢打雷下雨,只要父亲扛着铁锹出去,母亲总带着我们眼巴巴的站在门口,盼着父亲早点回来。一分耕耘、一份收获,父亲辛勤劳作,地里庄稼总比别人家高出一截,打出的粮食也比别人家的多。无奈那时家里人口多,我们兄弟几个又处在长身体的时候,个个跟饿狼似的,常常是满满一缸米,没几天就见了底。
生活的艰苦,往往能使人变得坚毅和勇敢。为了支撑起贫困的家,父亲什么苦都能吃,什么苦都敢吃。冬天里,生产队清塘逮鱼,河塘里的水被抽干了,鱼儿在河塘底翻着水花。无奈天寒地冻,站在塘埂上的人谁也不愿下去逮。父亲见了,脱掉鞋袜,第一个跳下去。在他的眼前,河塘底刺骨的冰碴、泥水好像不复存在。鱼逮上来了,父亲被人搀扶着爬上岸,双手双脚已冻得不听使唤。生产队的人忙抱来稻草,生火取暖,父亲半天才缓过神来。
农闲是庄稼人难得的清闲日子,父亲却从来没舍得歇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他便挑起一担箩筐赶到离家三四里外的小镇上,兑一担米,然后肩挑步行到几十里外芜湖市集市上去卖,一去一回,常常天黑才能回到家。有时,一担米才挣一二元钱,父亲也不嫌少。整个农闲,父亲就这样奔波于小镇和城里的集市上,双脚磨出一层泡来。
父亲没有学过手艺,应对生活,他就靠他那身似乎使不完的力气。母亲心疼他,劝他歇歇。他总是说,力气是浮财,走了又来。只要是力气活,他总想试试。姨夫会杀猪,父亲就帮他打下手。一头猪从宰杀、退毛、到清理,要花几个小时,全是力气活。父亲跟着姨夫从没有说过一声累。有时人家不给功夫钱,给点猪血、猪下水什么的,父亲也愿意。深夜,父亲提着猪血、猪下水,深一脚浅一脚回到家里,疲倦的脸上总是挂着满足。我想,父亲一定会是觉得家中多日没有见油腥的锅里,又能漂起油花。这是他难得的惬意。
父亲身材高大,说话声音宏亮,看似很严肃,但为人耿直,待人热情,心地善良,赢得大家的尊敬和信任。村里十几户人家组成生产队,生产队长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官,却有几家同姓的大户争来争去,互不相让。结果,大伙推举父亲,全队都心服口服。当上生产队长后,父亲更是起早贪黑,带着全队男女老少抢种抢收,组织生产。秋天卖余粮,生产队卖得最多;冬天公社号召冬修水利挑河圩,父亲组织的人最齐。生产队搞得红红火火,上面要奖励父亲。父亲憨厚地一笑,说,活都是大家干的,功劳归大家,要奖就奖一场电影吧。公社放映队果真来到生产队稻场上放了一场电影。全村男女老少高兴得像过节似的,把稻场挤得满满的。许多年过去了,村里人还津津乐道说起那场电影。
父亲没有读过一天书,一辈子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却对我们上学特顶真,家中困难,却坚持让我们去读书。大哥上学时,家里交不起学费,老师不让进教室。无奈之下,父亲花了几个晚上打了一根草绳,送到学校,给学生拔河游戏用,最终用它抵了哥哥一学期的学费。等到我们兄弟姐妹陆续上学的时候,每到开学,学费成了父亲焦心的事。对一个贫困家庭来说,几个孩子的学费是一笔巨大的开销。平时的生活捉襟见肘,家中当然没有积蓄。每到此时,父亲实在想不出其他法子就咬咬牙,从家中仅有的口粮中扒出一箩筐稻子,挑到粮站给我们换学费。当我最小的弟弟背起书包的时候,父母一下子供养着我们五个孩子上学。生活的压力真的让父母连走路都会喘气,但从没听他们在我们子女面前叹苦过一声。那时,村里和我一般大的孩子许多都下了学,在庄稼地里给父母当帮手。许多人劝说父母也让我们辍学回家,好分担一些困难。每每听到这些规劝,父母总是苦苦一笑,回答说,只要孩子们争气,我们宁愿苦点。后来弟弟、妹妹和我陆续考上了学,村里的人都说父亲不简单,有远见,让子女跳出了“农”门。每当听到这些,父亲总是苦苦一笑。只有我们子女知道,那笑容里藏着多少不易和艰辛。
兄弟姐妹像长硬翅膀的鸟儿,陆续飞出家门,父亲也一天天老了。年迈的父亲对子女们的爱,渐渐变成一种牵挂,一种从年头盼到年尾的守望。母亲去世后,父亲怕拖累我们,影响我们工作,不愿随我们一起生活,独自一人固守着家中的老屋。父亲说,平时你们工作忙,不打扰你们,就盼你们能回家过个年。每到过春节,还是腊月天,父亲便早早打年糕,备年货,在我们离开时,执意让我们带上。当我们离开家时,父亲总是依依不舍地站在老屋门前,目送我们一程又一程。
三年前的春节,我没能赶回老家陪父亲过年,心中像是压着一块石头,一直觉得愧疚得很。节后,还是抽空赶回了一趟老家。见到我,父亲没有丝毫责怪我的意思,只是眼里多了几许留恋和伤感。走时,父亲一如往常站在门前目送着我们的车子渐渐远去。不曾想,这一别竟是诀别。没过一个月,父亲突然倒下,再也没有起来。
父亲走完了他平凡的一生,没有留下轰轰烈烈的事业,甚至没有留下像样的家业,但从他那里我们得到了比家业、比财富更富有、更宝贵的东西。
责任编辑赵宏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