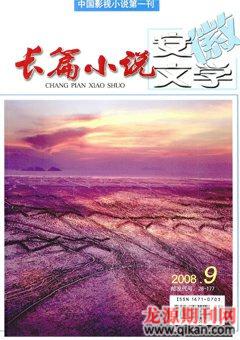废墟(外二篇)
刘学升
工作得闲,回了一趟乡下老家,无意间找寻到一段尘封的记忆……
一片废墟,荒凉地裸露在我的面前。这里杂草丛生,只有些许的基石和两根黑褐色的木梁,与坍塌的泥土相融在一起,让人猜测这儿曾经是一座土建筑。
我在废墟前伫立着,脑中的记忆却很清晰。这里原是一幢土建的、麦秸缮顶的民房。听母亲说,主人黄大,先前家中十分富有,父母死后,给他留下良田百亩,银元数千。但黄大娶妻生子,并没有守住家业。他经常聚众赌博,输掉了银元,就典当田地,结果不仅将家业输了个精光,还欠下一屁股的赌债。为了躲债,黄大举家搬迁到我们的村庄,认我的太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义父,分得一些田地,他也因此顺理成章成了我的“黄爷爷”。因是外姓,黄爷爷很自觉地在距村庄不远不近、面临淮河大堤的地方建了一幢坐北朝南的大土房。以前讲究家庭成分,黄爷爷由“地主”成为“贫农”,也算是他有“机缘”。
黄爷爷的子女们长大后,分别成家另行居住。村庄里的其他老人,闲来无事便找黄爷爷打纸牌。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到黄爷爷家打纸牌已经形成了“气候”:两张四方四正的牌桌,分别摆放在土房子东南方向枝繁叶茂的梧桐林中。打牌的时候,十来位老头儿和老太太抽着旱烟,喝着大碗的茉莉花茶,漫不经心,不争不吵,悠然自得。想想,这是一幅怎样的富有“禅意”的场面啊!
我对老人们打纸牌并不好奇,也不感兴趣。我喜欢他们的和蔼、亲切与慈祥,喜欢他们一边摸着我的头,一边笑眯眯地从口袋掏出一两块掺杂着烟丝的糖果,剥开来,塞进我的嘴里。我呢,只要得到他们的“犒赏”,便乐得帮着黄奶奶拉风箱,往灶膛里添柴,为他们烧大锅茶……这些老人的儿子、儿媳很孝顺,男人下地干活,女人在家做饭;男人收工回家,洗把脸,然后来请老人回去吃饭;老人回到家,儿媳已把饭菜端上了桌,桌子上放着一壶烫好的水酒和一只酒杯……
后来,牌友中一位本家爷爷去世了。他的去世有些儿离奇。平时从不锻炼的他,一日清晨忽然来到黄爷爷的家,说广播里播了,老年人要和年轻人一样加强运动,才能长寿呢。黄爷爷一边喝着稀饭,一边嚼着大葱夹馍:我不干,你要怕死你就去,我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折腾!于是本家爷爷一人沿着淮河大堤跑步去了……本家奶奶在家烧好了早饭,久久不见老头子回来,就和黄爷爷一同去寻,结果在大堤上发现了躺在地上的本家爷爷。黄爷爷蹲下来,推了推本家爷爷,喊了两声,见没有回应,便转头对本家奶奶说:回去叫你的几个儿子准备吧。
在本家爷爷出殡的当天晚上,本家奶奶在家中也永远地睡着了。长大后,我才从这件事中悟出:人,如果面临生命的绝境,精神往往有可能崩溃。
本家爷爷、奶奶在短短的几天里相继离开了人世,并没有给其他的老头、老太带来太多的影响。他们仍然心态平和地围坐在一起,悠闲地打着纸牌。对他们来说,辞世升天是迟早的事,只要认真地出好手中的每一张牌,与世无争,安度晚年,就满足了,根本没必要为“死”而大伤脑筋。
不知不觉,我离开老家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十多位老人先后全部作古,而最后一位无疾而终的就是黄爷爷。听说他在咽气前,说了一句话:“这些老伙计到底没有熬过我”,然后便毫无遗憾地闭上了眼睛……
这幢土房子不知在什么时候坍塌的。但从地上的泥土来看,坍塌的时间应该有好几年的光景了。而那些郁郁葱葱的梧桐林,也被砍光伐尽,甚至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早已隐匿得无影无踪。这个地方,对不知晓的人来说是无所谓的,但对我而言,神秘得像一则童话,又好似把我引入了一个陈旧且缥缈的梦境。同时对于久居闹市的我来说,这里又显得特别的静谧。我呆呆地、良久地凝视着这里的一切,轻轻一叹,无限惋惜着儿时在这里玩耍的风景已经随风而去。
眼前虽然冷冷清清,但我还是恍恍惚惚地看到了老人们避世隐居的身影。他们正围坐在一起,喝着茶,抽着旱烟,打着纸牌。一个赤着双脚、光着脊背的孩童,不断来回穿梭其间,为他们添茶续水……
有时间,我还要去看看那片废墟。
一棵树
爷爷生前多次叮嘱我,在他百年之后,只要把他安葬在乡下老家的土地里,他就含笑九泉了。
身体羸弱的爷爷终究没能熬到“百年”。在他83岁的时候,因脑肺病综合症突然发作引起呼吸衰竭,离开了我们。我们把他的骨灰安葬在家乡的土地中,了却了老人的一桩遗愿。
安葬爷爷的这块土地,远离公路,原先种着生长旺盛的庄稼,前些年因为退耕还林,现在已经绿树成荫,找不着一点儿庄稼的踪影,十分的幽静,符合爷爷生前喜欢保持内心洁净与安宁的性格,应该是爷爷永久休息的好地方。
爷爷坟墓的周围是五棵围腰粗的树,生命力显得极其的顽强。母亲说先前请了风水先生看过的。其实根本不用迷信,爷爷的离去虽然让我无限的悲伤,但这块“风水宝地”能让老人安详地休息,还是给了我稍许的宽慰。
因为,这里种植了许多的树。
树是有灵性的。你敬重树,树就敬重你。你若对树无情义,那么,你将会付出难以挽回的代价。
老家村子里有兄弟俩,他们的父辈生前栽了许多棵树。那个地方我去过,房前屋后,郁郁葱葱。冬天,那些树能够遮风雪;夏天,它们又奉献出酷暑中难得且茂密的清凉来。特别是房屋四周种植的香樟树,使蚊虫远远避开,不敢靠近,让人晚上睡上一个安稳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老父亲一直到死,都没有舍得砍伐一棵树,反而在临终前嘱咐兄弟俩每年要多栽树木,子孙幸福。
谁也没有料想到,这些本来枝繁叶茂的树,却被一种缺乏爱心和失去良知的荒唐行动所毁灭。去年,弟弟乘兄长外出打工之际,偷偷将大树全部卖掉。兄长回来后,闭着嘴咬着牙没吭一声,拿着斧头和锯子,将其余的树木一股脑儿地砍伐精光,连两株婴孩似的树苗儿也被他无情地拔掉抛弃!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木,只剩下几十个树桩。树桩中,现在生长出了许多的杂草,就是没有树木回归的迹象。因为这些树,兄弟俩反目成仇。倘若他们的老父亲有灵,不知会作何感想?孰是孰非,暂不必论,我所知道的,就是在树木砍伐精光没多久,兄弟俩已经无人居住的老宅在一个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深夜轰然坍塌,让整个村子里的人都深感惋惜,刻骨铭心。我在怀念那些树的同时,心中也不免对生命的无常有所感叹,甚至产生一种天真的奇想:什么时候农民不砍伐树木了,整个农村都是天然氧吧了,那么农村也许就彻彻底底地进步了。
爷爷离开人世已经有二十多天了,我先后去过墓地四次,每次都怀念着他对我的种种好。今天上午,我盘腿打坐在他的墓旁,内心深处忽然有一种特别亲切、特别熟悉的感觉:啊,我亲爱的爷爷根本没有逝去或者去了哪里,他其实就在我的身边呢!也就是说,这二十多天来,爷爷一直在我的身边,我却浑然不知——只是,他老人家已经隐化成了我紧紧依靠着的这棵树。
我说爷爷是不会狠心把我扔下不管的吧?仁慈善良一辈子的他根本舍不得丢下我,我至今仍然没有离开他的呵护。我知道,爷爷希望我好好地活着,成长着,直到我在生命的里程中长成一棵实实在在的大树!
小白
小白在六十岁生日的前一天,离开了人世。
小白是个女人,她是我拐弯抹角叙得上的亲戚。小白并不姓白,而是因为她七拐八弯比我长四辈,属于“白毛”。我本应称呼她“太奶奶”,但她认为自己年轻,一直让我喊她“小白”,说叫“小白”更贴亲。
三十年前的小白,细细的眉毛,白白的皮肤,肌体丰腴,喜里喜气,是村子里有名的大美人。我打记事起,就觉得嫩面俊俏的小白性格很开朗。与人谈话聊天,不管是老头还是顽童,她总爱带口头禅“我的个肉嘞”。由于她的辈分高,老少爷们敬重她,不计较。
大概在我六岁上的那年午季,村里人将收割的麦子用牛车从庄稼地里拉到打谷场上。我在小白家的打谷场边玩耍时,不留神摔绊在她家水牛的肚子底下,小白慌得连忙丢掉了手中扬场的木锨,跑过来把我拉起,掸掸灰尘,搂在她汗津津的怀里:“我的个肉嘞,没被牛伤着就好,你把我的蛋都吓凉了。”她男人大白在一旁“扑哧”就笑:“说错了,说错了!”小白不服:“我咋说错了?”大白的嗓门赛张飞:“你的蛋?你的蛋在哪儿,让我瞧瞧!”正在场上忙活的人,听后纷纷哈哈大笑。小白粉脸红得像桃花,顶他:“好你个没正经的,看我回家不把你的小老二给拽下来!”我不明白,问她:“啥是小老二呀?”小白将我从她的怀里腾出来,照我的头“啪”地就是一巴掌,嗔怒:“你知道屁,滚去玩吧!”众人笑得更欢了。那巴掌虽打得脆响,我却没感到疼痛。直到长大些,我朦朦胧胧地懂得,才陡然开窍——小白在当时“本分”的年代,敢同大白肆意笑闹,算“开放”了。
小白生了一男一女俩娃儿。老大柱子是男孩,比我大一岁;老二小欢是女孩,比我小一岁。我不喜欢脏兮兮、脸上挂着鼻涕的柱子,经常到小白家找白嫩嫩、面盘干净水灵的小欢玩。小白对我说:“小欢若不是你奶奶辈的,长大可以给你当媳妇。”同样的话她对我说过不下于两次,每次都是她在锅屋蒸馒头、烧稀饭时跟我讲的。讲这话的时候,小欢正坐在灶膛前的小凳子上,帮衬她妈添柴火,拉风箱,还抿着嘴笑。小白不像在逗我。我站在灶门口,宝里宝气且一本正经地告诉她:“不管。我妈让我以后找上海大辫子姑娘做老婆。”我一句没深浅的实锤子话,惹得小白将手中正搅稀饭的铁勺朝锅沿一敲,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声音的分贝:“我的个肉嘞,听说上海在东南,远着哪。你妈就知道要强!”
柱子和小欢如花蕾般噌噌地成长,吱吱地绽放,分别娶了妻,嫁了人。小欢没有嫁给我,因为我先她结婚娶妻。只是,我的妻子不是上海人,她的娘家在西南。小白的儿媳、女婿都是本村我不近不远的姑、叔辈,也是小白拐弯抹角的孙子辈。婚后的辈分自然晋升,都喊小白“娘”或“妈”,喊得小白直乐呵:“这是我儿子、闺女挣来的,个个让我疼。”没几年,儿子、闺女又陆续为小白生了三个花蕾般的孙子、孙女和外孙,整天似跟屁虫在小白的身边绕来绕去。一大家人的日子过得热热乎乎。
后来,小白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控制不住对钱的欲望和向往,不愿再呆在仅管温饱的家里了,就商量一同到南方“淘金子”。临行前,他们把孩子托付给小白看管。小白照单全收:“你们只管放心去吧,我保证把乖孙们照顾得细微。”儿女一走就是七八年,很少回来过。
去年刚过中秋,小白得了病。到医院检查,是肝癌,晚期的。小白想儿女,被病魔折磨的她,只要一睡着,便梦到儿女出现在她面前。然而,除了女儿小欢单独回家看望她,儿子、儿媳和女婿总是托辞眼下正是挣钱的当口,回不来,甚至懒得再打个电话。钱倒是三百五百地从邮局汇来,却没能治好小白的病。
小白非常想儿子,但一直没见到。年前临终时,她躺在床上,遗憾地摆摆颤抖的手,深陷的眼窝泛了潮:“唉,我的个肉嘞,这个挪了窝就忘娘的崽子哟,没心没肺,养条狗还晓得摇摇尾巴哩……”
柱子回家奔丧,衣着虽然光鲜,脸却白得像纸。看着柱子的自咎相,大白感到心口有股撕裂般的疼,耐性被逼到了极限,终于冲低头打蔫的儿子暴发山崩:“要钱管个鸟用,不还是没把你妈扳过来!”
责任编辑鲁书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