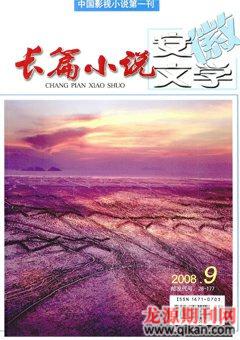走进老街的心脏
许松涛
谁没有来自地域的天然联系?回答应是肯定的,不然就我所在号称桐子国的地方,何以因文化而兴盛至今,贪得美名?自唐宋以来出了四百余进士,历史上久负盛名的“桐城文派”作家就有一千二百余众。连曾国藩也愿作门下走狗,那日夜耕读、诗书传家的风气可是非常罕见的奇观啦。在城市老街的每一处,我都能捕捉到文脉流长的气味,一副对联,一处字画,一砖一石,一草一木,我都能感知先人的遗风尚存。时光并没有因为历史的流逝将其荡涤,这是个活的城,它不会因为遗迹的渐失而消亡,你看那一眼眼亮泉仍在活泼泼走过城墙根,总有一种慌悚感。我徜徉在那西城区老街幽僻的曲巷里弄,见到一道道光滑的井痕就怦然心动。最近我特地去给东大街、南大街、北大街留些存照,更是被那远古的气息所染。不禁要问,一个人的出生与他的出生地有着本能的融合不是?你看那滞留在木柱上将要剥落的紫漆顽强地抵御风尘的侵袭,你再看那高高的老灰墙逼起的仄巷依然回荡着当年的蛩音,你看那粗大的虬龙般的紫藤依旧荫翳了古院,你看那一块块霉味浓烈的砖头铺叠着明清诗韵,只要想想这些穿过时光的马车、匆匆的行色、暗香的墨意、淡淡的脂粉味,顺着木楼倾听去,是那书斋的吟哦、是那闺房的女红、是那飞向天空的烽火墙、那玲珑的有着韵律的风铃、那小口的六角形的天窗,不是望归人,也是望情郎……这些都藏在时间的褶皱里,我在这里稍事逗留,就切切实实看了个明白。也许人们不能从一张图纸上获得关于它完整的概貌,但只要走进来就完全可以把它还原。它濒江而立,既非古徽州那样水墨酣畅,柔媚过足,又非中原大地民居那样简约朴质,不拘细节。作为丘陵地带的特殊地理环境,这个在南北过渡带上的玲珑剔透的城池,它的建筑风格,它的民间遗俗,它的思维定向,无不打上特殊的烙印。在战争、疾病、天灾的合力戮杀洗礼下,这里的人民忍辱负重,以可歌可泣的奋斗精神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史,续写了一篇篇值得咏叹的诗章。
老街作为城市的根,很苍凉地凸显在过往人们的视野里,飞檐上的小兽因年深日久而现出丝丝黯淡。朱红的阁楼紧闭着小窗,打开它的人已然远去,故事也已然模糊,楼上的雕花栏柱,不见了那个头插金钗的云鬓凭栏远眺,楼梯上那个提着长衫的男人,出行于茶马古道上的险途,也许也在相思,也许又寻新欢,也许是在吟哦着“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句子,也许已死于盗寇的乱刀之下……恍惚间,我来到前朝与先人对酌小语。这楼时而闭死了,然大户人家的气派不减,门口的上马石应该是为那些出仕做官的学子备下的吧?今天,我所见的只有剥落的大门沉沉地合紧了那个世界的是非。瓦楞上的草松在这个季节是干枯的,灰黄细弱的植株多么无力,天气好的时节,一线残照抹在寒凉的身体上,会明显地觉察出回暖的血色。我走在东大街的青石板路上,竟是有份狂喜,石头在作证我的到来,也在把这微不足道的寻访看作过眼烟云,这是些阅历很深的石头啊,如果是雨天,如果是少年,如果还被几首歪诗蛊惑着,这里流淌的就是别样的诗情画意,加上那条春水滔滔的龙眠河。可是石头真的在诗境的空灵里失去了厚重吗?它的延伸像那个年代的一条链子,它同样在提醒脚下的路要在承受的重载中打造,硌痛行走者的双足。
一条季节河把东大街与南门街、西门街、紫来街环在怀里了。由此可知东大街仅是条外街,既是外街就是新区,也是商肆发达的交往中心地,还是护好内城的一个屏障,轻重在于功能的分别了。事隔若干年前,李自成部将张献忠来破城,久攻不下,也不得不暗自长叹:“真是铁打桐城。”撤兵而走。这座高达丈余,宽可四辆马车骈足并行的城墙,墙脚下的三方环水一面靠山的城,就那时的进攻装备而言岂非固若金汤?且不说那紫来桥的古朴是连接内城的唯一退道,就撇开那凝重窒息的战火味不说,把心情交给安居乐业的盛世,这里依然闪烁着文化的灵光,到今无法可考的联句:“紫来桥下水,龙眠山上茶”,既一语道破这里的地理、人文状态,又不乏安然乐士的情趣,人们的怡然自乐和对大自然的钟爱,心态的清朗,及生活的情调都跃然字里行间,是值得今人光大的。紫来桥下昔日行船摆渡,换成了今天的橡皮汽艇,而且这里已不再供人车来往,改造后有城市重心前移,把历史还给看风景的人们,在少人的时候,偶尔带着亲朋好友来品咂观赏不失为一方好去处。那夹岸的刺篱,狰狞砌岸的红沙石,绵延的矮垛,成片的汉瓦接起的白墙,可以令人恍然隔世忘了俗务,桥面上的数丈长一根的麻条巨石你很难想像是怎样的凿出,运到,又是用什么办法架上桥墩的。多少年过去,又是何以见其当年的繁华盛况的,只有这嵌得两寸深的条石见证,那车辚辚马萧萧的局面是多少岁月存下的一笔深辙啊,从樵夫渔父到车辇华盖,从拖儿带女找生计的下层人到役使如云,锦衣玉食的豪门望族,这样的现实没有谁去改变,也没能力更改,也同样嵌在历史里。在今天的环城大道上带着满足的精神购物的女人们,是不会去关注一座城墙的消失的,那厚厚的城墙砖头的一夜间不见踪影,对于一个和平开放的时代而言顺应了时势,可对于一座城的来龙去脉来说却是一个无法弥补的缺憾。自唐真正有建制以来,历千年而不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城池,也就是在1938年日本人的飞机对桐城狂轰滥炸时拆除的。当时的县长既惜民命又珍财力,听说鬼子飞机要来,而城墙是阻碍城民疏散的最大隐患,工程浩大,按部就班组织人力撤肯定来不及,他来个急中生智,下令拆下的城墙砖谁拆谁要。这真是聪明而大胆、惠民又行之有效的高招啊。尽管我们为城墙的不再而痛惜不已,但也应该为一个为民请命的县官而感到骄傲。这是一段苦涩的佳话,我们今天活得自得的人又岂有资格指责他呢?
紫来街,船夫来过。我要报着对一方水土的敬意提到它,是因为它曾经是那么的奢华过,又是那么令人所不齿,恰应了国人只做不说的丑陋。火红的嘴唇,映了一河的浆声灯影吧?那些商贾,你可在这灯红酒绿的香艳里歇足,或者耗掉你的银两,我不能不叙述它,不然就不真实,就是对历史的阉割。不管怎样,这里需要的是一种特殊的营生,一个假死的安定。假如我道貌岸然做伪,那就不是君子所为。既然那些什么生计都没有的女子,她们的选择就不能被唾弃。把她们放在暗处,你都要用一副柔软的心肠来看待,因为她们毕竟留下一条街,她们取最纯的龙眠河水为你煮茶,又以最好的青春催你安眠,泡得你骨头酥软,让疲惫不堪的奔波之途消解在孤身只影的寥落里,捕获稍纵即逝的一丝安慰。那些漂泊的人,多变的生活遭际,需要有句温暖的软语抵御脆弱,暂且把那朦胧中的人看够,那可也是一叶挡风的墙,尽管它天明之后崩塌,但街的总长留下了。文博馆的人告诉我,也许是加了这么一段,才是至今保存下来的全国第一长度的地方老街,这样的作用还小吗?
北大街该是一条最有人文气象的街。这条街当然的是一条名门街了,它不但历史最为悠久,重要的是昔日的政治中心,县衙的一处房产保存完好。而街的两边聚居的都是当地的几大旺族,他们屋脚相连,檐廊相望,各成一体,一律的深宅大院,又各各不同,豪门大楣,气象万千。马、王、姚、左、方等家族蒸蒸日上,他们是自元明以后渐次发迹直到后来声势日隆的。不似东大街上商肆林立百工交汇,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还浸润在它的繁闹和琐碎中。打铁的、弹棉花的、卖泥货的、理头发的、编竹器的、吊酒的,无所不有,让人眼花缭乱。北大街就显得清爽,雅致,每户的房屋建筑全是大开大合,屋宇连片,阁楼、厢房、耳屋、天井、书斋、大堂、脚屋、马厩等设施齐备,木构穿枋,前后几出几进,可见当时何等富贵荣华,不同凡响。在这些家族中确实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人物来,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就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在我国哲学、历史学、物理学、数学和医学上的贡献都是空前的,他在音韵、诗词及琴棋书画方面的特长,也是为后人大为称道的。近代有一代美学宗师朱光潜先生,他的煌煌大著折服多少天下高人,不愧为当代美学的奠基人。再有就是左忠毅的出现,把一个肝胆相照的忠臣永远记录在历史的正传里,宁可挖肝扒胆也不要辱没门风。仅姚氏一族就有姚鼐这样承清朝两百年的“桐城文派”领军人物。坐落在今老广场正中子午线上的文庙是对这些士子颠沛人生的最好注脚。他们深怀理想,积极举世,热衷功名,抱负天下,只要科举高中就必踏棂星门,跨上状元桥,走向大成殿,向大成至圣先师孔子顶礼膜拜,寄望厚为,可是王天下的皇家又是怎么给他们以回报的呢?方以智激烈的人生态度和传奇式的人生经历叫我不得不把这位先贤视为另类,他尽管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智慧超群,可他生在明朝覆亡清朝大举进犯的岌岌可危的时局之际,只能屈才含愤,空有报国之志,对前王朝的迷恋和对新王朝的不合作态度最终把他逼上绝路。他在秦淮河上的寻芳踏翠浪子作乐和在选择浮山一隅独筑禅房苦研佛经的风马牛不相及的强烈反差,他的坚决弃绝顶戴花翎的诱惑与甘愿引刀献首的痛快,演绎了人生多极状态下的慷慨悲壮,五十九年的人生短途在他的挥戈里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英雄一样要向天地谢幕的,英雄也会哭泣的,但他总是那么潇洒地穿过人生路,演出真性情,是猥琐凡胎望其项背的。他的玩世不恭我行我素的态度,已把自身超脱出红尘蝇苟之外,这就难免他的内心总是那么无怨无悔地笑对命运的不测。远离家乡的台湾护军将领姚莹,也是带着被诬告的怨屈上路去的,他的清廉恰是别人替他筑就坟墓的祸端,最后客死他乡成为一缕烟魂。唯有姚鼐位居朝廷而激流勇退,他没去朝里做官时却渴望投身庙堂,一旦如愿以偿才知不是久留之地。四十岁的人了,人近中年,幡然醒悟,有种立地成佛的洞彻,毅然弃下官袍,靠回乡收徒糊口,那要多大的勇气和胸襟来承纳乡人、同党的目光!他辞官回故里,是一次对自我与世事最清醒的梳理后的淡定,他抛弃了大红翎子,穿起了便衣,戴上小帽走向乡间的私塾,开始杏坛生涯,最后集桐城派文学理论之大成,他的猛然转身难道不是对为事者的一个启示?惟有戴名世的死才是最可怨的,《南山集》的出版已是他考中榜眼的前十一年的事了,如果说他真与政治势不两立,倒不如说他的秉性才气因为缺乏应有的官场规则素质,最终为异己的力量所吞噬罢了,其实质是,在康熙帝牢牢一统江山的神经质的作用下,戴氏的一世聪明做了帝王杀鸡骇猴招术的牺牲品,奸人的恶意正好迎合了皇帝借人头镇天下的妙囊之计,当然顺理成章的一呼一应了,你说一个书生死得可是糊涂不过?对于皇帝,那场罕见的文字狱中戴氏应是他巩固江山的以少胜多之战役中的功臣。如今他的文学贡献在当地城里仍然叫许多人难以摆上桌面,还一个作古者公允的评价,我以为是应该的。在新近建起的现代广场的文化柱上,戴名世理所当然地应作为代表人物忝列的,然而他却不在其间。文化大革命中屈死的著名黄梅戏艺术表演家严凤英也不在其中,真是叫人匪夷所思啊。戴氏的账到乾隆时已算结了,这是皇帝的高蹈谋术,对戴并没加罪如何,而严凤英更是早还了清白。如果这样的大家都不能立柱于世,而将那些并非本土而在我地确实树起丰碑的人物雕刻在上,这不是明显的自卑或是努力要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创造者冷落了吗?我相信后生打开自己的文化史时一定要追问这是为什么?难道就不怕他们唾骂吗?其实,还是历代的血腥的政治运动的影子在我们有些人的脑子里根深蒂固,他们只是为明哲保身而这样屈就自己,非常匆忙而不负责的向历史作一个仓皇的交代,丢下一个十分委琐的尾巴。
成功人士是有的。南门的宗伯地、司马地,还住着许多户人家,这里原都是康雍乾时期父子两代宰相或其子嗣的庄园。一直向南绵延才见商号,酒肆,住户,这里都是有来头的人,住进城享受那少数人才能过得起的日子,再不咋的都是有些身份的,否则,这里的地皮也不是没眼睛的。而著称于世的就是宰相的家人与邻人吴氏争三尺墙基的美谈,一直炙手可热。大凡来者都要面墙凭吊,兼有怀思或反省的味道。这是高官与平民的一场较量,结果显而易见是平民获胜,像德皇与小磨坊主的那个传遍全世界的经典故事,告诉人们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家人弛书宰相,怀着必赢的信念,且现实也该使他们充满底气的,结果却让人十分意外,因而这才是新闻变为故事得以传扬的动因,在封建时期的中国个案中这很特殊。毛泽东接见尤金时还特地提到这个故事,可见宰相的雅量和对世事的窥视确是高人一筹,这两个不可比的门户在一纸家书的划定下陡然达到暂时的平等,似乎阶级的概念没有了,而这样的暂时就永恒地载入了史册,我们不觉有些可笑?不过我们还是要理想地放大具体事件的意义,起码是一种令人满意的开端到来了,起码我们再次读出了家天下的皇权时代,一批正直的官员他们是不会与民争利,依权仗势草菅百姓的,正是因为有他们在,才有了国家政权的稳固,才有了黎明百姓暂时的安康。小宰相张廷玉晚年执意归乡,也许正是功成告退的自悦之举,而这种姿态恰合平民之道,真是圆满的人生退场。栋梁之才,平民心态,有此大境界的当然不是等闲之辈,暗合了他的身份,进退自如,是他把握自己的修养所得,死后能融身清帝家庙,那是极致的哀荣啊,满族的皇帝能这样善待唯一的汉臣,无论你怎么猜测,都不能否定他在为官中的举重若轻的能力和忠诚。这样的结局当然是最理想的,可是从这里走出的士子,哪里都能这样的幸运,他们的人生坐标本就不同,他们的理想和个性的差异,他们的生存环境与成长空间的先天有别,导致从棂星门走出的人形态各异,甚至作为单个的生命而言,制造了不愿看见的悲剧。
今天我们走在他们曾经成长,曾经生活,曾经辉煌或黯淡的里巷里,群星璀灿,光照九州,他们是不朽的,只要我们还在这条路上走,更多的人还要来瞻仰他们的生地,他们含蕴了这里的文化厚土,没有文化的土地是死亡的土地,而这里的土地正生机勃发。
责任编辑陈晓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