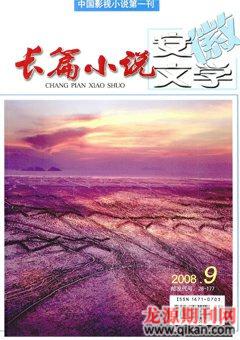在春天生长的动词
金肽频
行春
在长江南部的一些地区,沿袭下来一种很古老的习俗:行春。人们不分男女老少,都要在立春的头天,像迎接新娘一样迎接春天的来临。这种仪式的庞大,有时涉及几个乡镇,有时是一个县市,人们用各种幽默而愉快的举动,为春天表演。
我少时曾亲身参加过这种“行春”的活动,至今仍无法忘记那些立于山野之间的队伍,随着山水起伏,伴着柳树舞蹈。活动没有官方的主持人,主要是地方上有号召力的长者操办,有时纯粹就属自发的。女人带来自制的彩幡以及那些刚从田头山野采集的野花,男人则牵来家里的耕牛,沿着田埂排成两溜子,男男女女嬉笑相逗,互相打趣,一副平时少见的悠闲自得的模样。这时,首先会唱歌的女人就要甩开嗓子唱上几首,少数调皮的年轻人便拍打着脸盆,算是应和。我去看“行春”活动的那年,才十岁左右,只有看热闹的份儿。挤在人缝里,手还被村邻牵着,几经央求才挤到了队伍的前面。妇女们唱的大多是民歌民调,我半懂半不懂,但她们摇头晃脑的神情至今仍深刻在我的脑海里,有种毫不褪色的力量。唱完了歌,还有一个重要的仪式:彼此交换一下牵来的耕牛,互相摸一摸,在农村的口谚叫:“摸摸春牛脚,赚钱赚得着。”少数不听话的牛,这时难免有发怒的行为,踢上你一脚,但被踢的人也都咧着大嘴嘿嘿地笑,决不朝牛发脾气。放完鞭炮,接下来就是“舞牛”的精彩把戏了。
后来我曾在明朝诗歌里读到过江南这种舞牛活动的渊源。周希曜在《宝安春色篇》(即今天的深圳──作者注)里写道:“春牛高拥巡陌上,瑞麟婆娑影盘桓。”现代人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古人们拥到山野之间,用纸扎的春牛和麒麟高歌狂舞时那种兴奋的情景。我少时在江南看到的这种“行春”仪式,就是古老习俗的延续,在民间娱乐中享受丰收和新春的喜悦。精彩的“舞牛”中,人与人同乐,人与牛共舞,少不了人仰牛翻的镜头。有的是十多个人围着牛,一边走动,一边整齐地喊着嘿育嘿育的声调,在田间地头久久回荡。数百人一起热闹的场景是生动的,也是深刻的,将我幼小的灵魂激荡起来,让我远离那片土地后仍割舍不掉怀念的情结。每当我看到人们迎春的种种活动,就情不自禁想起少时在江南看到的行春的方式。去年我去江南苏州的松江一带出差时,无意中又有幸亲眼目睹了一次行春的经历。
现在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行春时已多出一项新的内容。
这天的天气很晴朗,我乘坐一辆中巴车去一景点,在拐过一座不高的山冈后,突然发现有好几百人的队伍,热闹非凡。大家大都穿着新衣,一位像官员的人在做主持,好奇心极强的我,再加上记者的职业习惯,就下车了。呵,原来是“行春”,这好家伙!几十条黄牛穿上了彩色背心,已列队站在田野。旁边还插着一杆国旗,排列着一行乐器。参加行春活动的人,除了自唱、对歌之外,还举行了牛的奔跑比赛。紧接着,是我熟悉的“摸春牛”习俗,男女老少都争先恐后地上去摸一摸,有个小伙子还很滑稽地亲吻了一头大黄牛的前额。活动结束,有人端上了“七彩汤”,即用七种蔬菜做成的菜羹汤,色泽丰富,鲜美异常。大家随便端起就喝,没有什么规矩,并有热心的人告诉我:“喝了这迎春汤,你可就是春天的一颗心了!”的确,在这种特有的行春仪式中,人给予了自然一种极高的礼仪待遇,自然也会给予人们以真诚的报答。
听春
有关春天的感觉,是从听开始的。春天的第一声,是冬雪落在大地上融化的声音,是小草用毛绒绒的手指弹拨泥土的声音,是风爬过了屋檐跌落到小路上的声音。总之,它很轻,只有在人们的细密观察中才看到她的来临。
春天的来临突然而神圣。就在前不久,我还穿着很厚的冬装,把自己裹得犹如“套中人”,但二月二龙一抬头,沉睡中的万事万物也都抬头了。最让人感觉不到变异的是冬春之交,那时候人们成为季节的附庸,做着季节的奴隶,只有当听到春的一声来临,我们才成为季节的主人。我们在冬天去抚弄冰渣,觉得它是生脆的,尖锐的,到了春天,你再去抚弄时,你就感觉它是柔软的,有着某种温馨与记忆。冬天的风就像是你的死对头,不知好歹地往你怀里撞,但到了春天,它就变成了“红酥手”,风过处留下一片浪漫。结冰上冻的河水里,一层层裂开的声音在小心地传递;积雪从松针上顽皮地跳下来,在跌落的过程里还玩起捉迷藏的游戏;七星小瓢虫在爬行时,故意地用上节奏;迷了路的蜜蜂一不小心就落进桃花姐姐的怀抱,所有这一切,我们只有靠自己敏锐的听觉,在身边的细微处发现春天!
我很喜欢去听春天,在听的过程中使感觉得到升华,使生命变得年轻。听一片脆绿的叶子在夜晚里轻曼地歌唱,听一粒种子在花的怀抱里悄悄开放,听一位夜行者清脆的咳嗽声。春天的小鸟站在树的最高端,以瞭望者的姿态与我们人类一起倾听着。“沾衣欲湿杏花雨”,这是听出来的一种情景;“春风又绿江南岸”,这是听出来的一种场景;“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这是听出来的一种心景。在我的家乡就有一种“听鸟”的习俗。人们不分男女老少,在“人日”(正月初七)这一天,赶到水塘边或林子里听鸟。以鸟听年,从鸟的叫声来解析新的一年。譬如,喜鹊先叫有祥瑞,麻雀先叫有丰稔,水鸭子先叫有水患,火头鸟先叫有荒旱,乌鸦先叫有凶煞,猫头鹰先叫有瘟疫……那时少不更事的我们,就是先听到了猫头鹰的叫声,也总喜欢说是喜鹊和麻雀的叫声。现在想来,这种传统的“听鸟”实是寄托着农民深层的文化愿望和理想,他们以倾听来期望实现年成的祥瑞和丰稔。
听春是一件无限快乐的事。无论是听残雪消融,还是听溪流淙淙,或者听细雨润物,都是精神的愉悦与追求。西方哲学家王尔德曾说:“唯有诱惑,我不能拒绝。”春天对于人们,谁又能拒绝?尽管她来时喜欢以一种悠长的方式,但她却能成为听觉感官上的归宿。只有人的感官满足了,才使灵魂得到满足。所以,我们听水,希望是听到流水;我们听风,希望是听到影子;我们听星月,希望是听到光润。
尽管春天没有夏天火热的气息,也没有秋天丰硕的收获。但春有着内心的激情,她可以使生命重新燃烧,这是人们尊敬她的理由。孩子们在春天来了的时候,身上可以增加一层鲜活。城市在春天来了的时候,可以听到它快速有力的成长。街道复活过来,汽车的鸣笛也格外清脆,城市里的春天四处回荡着人群流动的铿锵之音。“春江水暖鸭先知”,在感知自然属性上,鸭有先见之明,而人也同样是灵敏的,睿智的。人可以听风而知季节,听雨而知绸缪,听雪而知丰稔,听春而知奋发……听天与人、心与心、物与物的互动,听信心的坚定不移和智慧的脱颖而出,听一种意外的、让你大喜过望的启迪与提示,使春天变为每一个人、每一棵草、每一条河、每一粒种子、每一个思想都可以感知的细胞意义上的春天。
踩春
“踩”是人们迎接春天的第一个行为动作。自很小在家乡开始,直到今天我在城市的角落,都不时看到与“踩”有关的动作,春天就像是人们一不小心踩出来的。
在中国古代,春节是一个农业性的概念。它相当于春季的“立春”,只要它张开了口子,整个春天就开始萌动。所以,在我国民间,春节总是贯穿了太多的行为意识。在家乡我就见过最典型的几个“踩”的动作。首先作为孩子的是我们踩高跷。找两根小手臂粗的竹竿,在竹竿腰上扎两只短木棍,然后扶着墙壁,歪歪倒倒地上路。看到有一个孩子这样做了,不到半天工夫,就会有好多孩子来赶“高跷会”了。大人们乐得围在一旁观看,也时有大人接过我们小孩脚下的高跷,被摔了个屁股朝天的。还有一种叫做踩灯笼的游戏,这是有点奢侈的游戏。我们在大人写春联的剩余红纸中,找些碎小的,用竹茎糊起小小的灯笼,排在石头上,然后像“蜻蜓点水”一样,从石头上飞身而过,脚踩处,爆出劈劈啪啪的响音,像鞭炮,似气球,感觉春天犹如脚底下的“神行太保”,是专门来和孩子赛跑的。这时让我们感到最神气的还是那种“踩花轿”的大型活动,整个村庄都踩动起来。几十架各式的花轿,在男人女人的手中,老老少少在花轿内外跳来跳去,也是踩来踩去。抬花轿的人,他的每一步都会踩出花样,有时像百步穿杨,有时似天马行空,总之抬花轿的人他的步伐越“花”,喝彩声就越多。现在想想那种踩在大地上的感觉,至今仍有一团火在脚底下涌动。
春节过后,农忙开始。这时一项有关季节更本质的“踩”的活动,在田野间挥洒开来。家乡农人习惯于将冬季长出的杂草和紫云英,全部刈割,然后一家大大小小全上阵,一脚一脚地踩进田里,叫“埋青”。这些踩进田里的春草杂花,在土壤里腐烂发酵,是最天然的肥料,把春季和夏季的庄稼喂养得又壮又肥。原来就这么简单的“埋青”,却孕育了这样重大的主题,任你凭空想象不出的。春天是从土壤里向上蹿起的力量,而“踩”这个动作是使劲向下,人们的这一“踩”犹如打开一个季节的阀门,一片春天的喜人景象也就此打开了。
现在在城市,我们也时不时看到这些“踩着春天”的行为,只不过有些是在人们的无意中进行的。你没有注意去踩,就感到了它的价值。如人们喜欢的“踏青”。这里的“踏”是一个比较文雅的说法,其实说得简白点,就是到外面的世界里走一走,踩一踩,然后带着乡野之气进城,过上一段舒心的日子。前几天,有朋友邀我去跳舞,说春天来了,人也该松动松动骨头。我这把骨头虽不是老骨头,但也是经历了四十个春天的一副架构。当我和朋友一起兴奋地扭动着老腰,我感到脚下的感觉真是美妙。踩在地板上,地板就有一种颤动;踩到别人的脚上,别人就喊“疼!疼!”有天,我终于带着一家人来到郊外的一片田野,和我小时家乡差不多的田野。下了车子,我一脚踩在田野的青草下,感到脚底下一软,陷进一层鞋底的深度,像踩在地毯,又如踩在人的肚皮上,让人的双脚在柔软中感到一种透过脚背的力量。我立即俯身朝脚下看了看,担心从田野里拔出的鞋沾满太多的“野味”。当我提起鞋子细察鞋底时,竟然没有粘上泥土。奇怪不?是不是春天有特别神妙的个性?直到城里夜晚的灯光全部亮起,我行走于坚硬的水泥街面时,依然感到我的双脚充满异性的温柔。
踩着春天,春天不但与你一道醒来,还会为你留下一双完美的脚印。踩着春天,春天把它的神经链接到你的脚下,让你的双脚充满坚实的力量和迈动的节奏。
责任编辑赵宏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