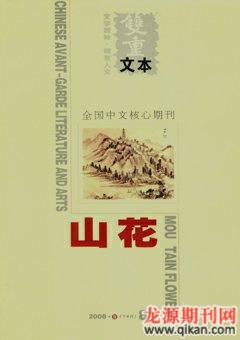日本汉学研究的三个时期及其特色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汉学逐渐成为国际上的一门显学。一般认为,汉学发轫于16世纪末的西方,经历了确立期、发展期,到20世纪逐步进入繁荣期。虽然人们认为汉学起源于西方,但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完整。因为日本人自隋唐起就开始引用中国的典籍制度,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应该远远早于西方,可以说日本与中国汉学的渊源最为深远。由于中日两国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际地位的变化,最终导致了日本在审视中国文化时态度上的变化,因而导致日本的汉学研究经历了由汉学、支那学到中国学的三个时期的转变,各个时期的汉学研究呈现出各不相同的态 势。
一、汉学时期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吸收
汉学时期是指公元六世纪到明治维新前的一段时期,这一期间表现为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单方面的汲取。日本吸收中国文化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历史过程,如果详细分析,在这一阶段的各个时期,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内容也各不相同。
奈良时代主要学习中国的制度和文化。那时,日本朝野以模仿唐朝的一切为时尚,模仿唐朝的律令制建立了日本的政治制度,就连平城京也是模仿长安城的格局建设而成。此时期形成了以宫廷贵族为中心学习汉文的热潮,人们不但学习汉文,而且还用汉文创作诗歌。并且在使用汉字记事的基础上,日本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标记日语的音和声,创造了“万叶假名”,并用之创造了和歌集《万叶集》。至此,日本结束了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历史,这是日本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此外,佛教由中国传到日本后,为朝廷所利用,受到朝廷保护以至成为国教。以奈良药师寺为代表的佛教艺术,成为当时日本文化史上的一大景观。
镰仓时代大量引进中国的思想文化,是日本佛教史上的重要时代。此阶段出现了不少佛教文学,有佛教说话集和随笔集,如鸭长明的《方丈记》、吉田兼好的《徒然草》等。它们大多用佛教观念对贵族生活进行尖锐的批判,给传统守旧的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的感觉。由于中国的新佛教禅宗的传入,此阶段的汉学出现了新特点,突出体现在禅院文学上,形成了以廉仓五山和京都五山为中心的“五山文学”。镰仓建筑以佛教建筑为主,随着中国禅宗的传入,宋代的建筑风格也极大的影响了日本建筑界,使镰仓建筑在日本建筑史上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
1603年开始进入江户幕府时期。江户时代历时260余年,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成熟期也是崩溃期。江户幕府为了政权的稳定,把程朱理学作为国学,采取保护政策,于是,朱子学成为当时的正统思想,被视作国学,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得到大力推广和普及,成为人们日常精神文化生活的行为准则,对日本的国民性和民族精神构造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中国的儒学成为江户文化的主流,特别是朱子学取得独尊的地位,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推动日本精神文化的发展。
纵观从奈良时代到明治维新,即从建立古代国家到封建社会结束的整个历史时期,日本在一直不停地引进,吸收和消化中国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和发展了日本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汉学不单单作为一门学问,而是对日本的社会文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把中国文化或者说汉文化比做母体的话,那么汉学就是播种机,它在日本这块土地上播撒了汉文化,孕育和催生了日本文化,如果没有汉学,两种文化之间就失去了沟通的媒质或桥梁,也就不会产生今天的日本文化。日本人崇尚汉学,视汉学为自己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学习、研究和继承。但汉学时期严格说来不存在所谓的“中国研究”,只能说是对中国典籍或思想的认识。每个时期的具体内容尽管因为中国本土的流行或日本社会的需要有所差异,但它一直是处于维护上层统治阶级的文化工具的地位。
二、支那学时期中国研究的政治化倾向
明治维新是日本社会近代的开端,也是日本脱离亚洲向西方列强看齐的过程。在国家全面文明开化的氛围下,学术界也开始引进西方的科学方法,鼓吹建立具有客观性的知识。对中国的研究开始挣脱旧汉学的哲学、史学、文学范畴,纷纷追求自身学科的独立性,于是出现了在方法论上持实证主义的“支那学”。支那学在学术源流上受以法国中国学为代表的中国学以及清朝的考证学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较为注重严谨性。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内藤湖南可以说是中国问题研究的大家,他在研究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变化后,断言中国的君主制将灭亡,共和制将到来。他把宋代以后的历史划归近代,肯定了近代平民的运动。内藤湖南的严谨而科学的研究,为“支那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并对后来的中国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跟以前的汉学相比,他们的学术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正如刘岳兵所言,“支那学”就是要真正“从传统汉学的旧套中摆脱出来,对古典文本不仅仅局限于同情地解释,而且强调一种批判的眼光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毕竟“支那学”是在日本国势日渐增强、中国国势日渐衰落的大形势下产生的,于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中明确表现出排斥中国文化的迹象。实际上这种迹象在“支那学”产生之前的明治初期早已存在。用福泽谕吉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和朝鲜一样,是日本东方的“恶友”,不但不应与之交往,而且是应予以“回避和谢绝”的。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通过对朝鲜、中国的侵略逐步实现了近代化以后,对亚洲国家,特别是对中华文明的鄙视也越发凸显。受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当时的汉学家们在其中国研究中对也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蔑视,其中国研究目的政治化趋势比较明 显。
作为知名的中国专家,内藤湖南对待中国的态度是相当轻蔑的,他的一些研究对日本的对华政策也有着一定的影响。他在《支那论》一书中称中国应放弃中国周边的领土,仅保住本土就够了,因为中国人缺乏国民国家的政治能力和造成国民国家的资质,而且,日本人不能漠视英美对中国的瓜分。他在另一本《新支那论》中还提出了“文化中心移动说”,他认为日本是东洋文化的中心。由此不难看出内藤是在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寻找根据。
白鸟库吉在1904年7月在《世界》上发表了题为《我国之所以强盛的原因》的文章,他认为东亚各国衰败的真正原因是由于位于南方的农耕民族在被来自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征服的过程中,失去了民族认同感和爱国之心。同时他认为日本是一个特例,日本拥有区别于其他亚洲国家的文化取向,尚勇的精神传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万世一系的皇室的存在,是大和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之处,同时也是日本强盛的原因。白鸟的这篇文章充分体现了他的思想倾向,表达了他对日本皇室的忠诚,同时,白鸟的研究也说明了日本“支那学”的一个特征,那就是强调学问要服务于政治。
支那学时期一直持续到战前,此时期的中国研究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也有系统的、先进的研究方法,但在当时日本社会形势的影响下,逐渐被军国主义利用,其研究目的政治化趋势比较明显。
三、中国学时期中国研究的新特色
二战之后,在美国督导下的日本民主化道路的进程中,汉学和支那学日渐衰微,代之而起的是新兴的中国学。日本现代中国学的起步应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49年10月“日本中国学会”宣布成立,由于该学会过多地继承了战前汉学和支那学的传统,研究成果还是以古典为中心。1951年起步的“现代中国学会”与前者不同,它以对现代中国的关心为出发点,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学,是一个综合性的现代中国学会。1986年“东大中国哲学文学会”经过改组成立了“中国社会文化学会”。此外还有九州大学的中国哲学史学会等各大学、各学院的专业学会,这些学会成为现代中国学的主要阵地,从事着现代中国的研究。
战后的一个时期内,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学者们试图以日本的战败和中国的胜利的历史事实为依据,探索中日两国在西洋文明的冲击面前各自的反应,并探讨其潜在的思想意义,以中国的近代化来批判日本近代社会,从而寻求日本的出路。因此,战后一个时期内的中国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多是处于对日本近代化的批判。从他们的中国研究可以看出,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并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学者们试图通过对中国的研究与分析,为日本探寻出一条全新的社会变革之路。
进入80年代以来,日本中国学研究呈现出新特点,即随着研究队伍和研究领域的壮大,中国学研究呈多元化趋势。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经济取得了飞跃的发展,日本的中国学也迎来了高潮。特别是近年来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得到了从政府到民间的广泛重视,1996年,日本政府曾将有关中国的研究课题列为国家级重大课题。从研究队伍上看,研究人员已不仅仅是大学的教师,政府部门、新闻媒体、金融机构、实业家、民间人士等各行各业人员都积极加入到中国研究队伍之中,从研究领域上看,已经突破了过去那种以文史哲为重点的局面,扩展到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社会、外交、艺术、军事、环保等各个领域。日本的汉学家从不同的侧面客观的研究中国,对中国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特别是当代汉学家沟口雄三的多元化研究视角让我们耳目一新。
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研究方法的缜密。他们的教授多数都只研究某一本古籍或一个人物。要研究某一本经书或某一个历史人物,就要尽可能收集有关的全面的资料,然后对材料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整理工作。由于版本多,收集就要花很多时间,整理也需要很长时间。然后再进行校勘,更正错误,或者存疑,经过长期研究,产生出自己认为尽可能完善的定本。在这个前期准备工作的基础上,才能开始进行思想研究。而这个基础工作一般要花一二十年的时间。陈尚君教授曾赞赏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传统悠久,成果丰富,重视从踏实的基础研究入手,慨叹“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如果给中国学颁发诺贝尔奖,大半要颁给日本人”。由此可见日本人的中国学研究之专、之细、之深刻。
四、结语
或许对于西方来说,由汉学到中国学,只是新旧称谓的变化,本质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对于日本来讲,汉学和中国学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日本汉学经历了“汉学——支那学——中国学”的历史变迁,而这种变迁既折射着中日两国的关系史,同时也包含着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态度,以及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变化。早期的汉学研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研究”,只是对中国思想和典籍的认识;支那学时期的研究,虽然受西方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也有系统的、先进的研究方法,但最终被军国主义利用,缺少客观性,政治化趋势明显;新时期的中国学研究不仅研究范围广,而且研究视角新颖,呈多元化研究态势。
参考文献:
[1]冯昭奎.“日本人如何研究中国”[J].世界知识,2008.
[2]张西平.“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启示”[M].中华读书报,2007.
[3]刘岳兵.“‘京都支那学的开创者狩野直喜”[J].读书,2003,(7).
[4]张如意.日本文学史[M].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
[5]连清吉(日).“日本汉学的特征”[M]. 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
[6]诸葛蔚东.战后日本舆论、学界与中国[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
史艳玲(1970-),河北徐水 人,河北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日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