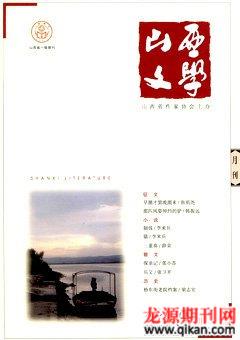制钱
李来兵
1
抢疯了。
推土机密集的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像炮弹扫射向天。浓黑的烟雾喷溅出来,把一群凌空而过的麻雀吓傻了。它们在半空支棱住身子,随即,丢下几片羽毛,风一样四散刮去。
被风兜旋了一圈的雾霾伞包般虚扁下来,向那些因为弯倒显得有些雄壮的脊背罩上去,然后再在他们站起的瞬间,雪沫似滑到地上。他们掏出来的手,依然激动不安,红胀得就像一张张做错了事的脸。上面混合着见了水汽的泥土,黏糊糊的。那水汽是他们头上甩下去的汗。
那个终于杀出重围的人佝偻着腰,双手抱得紧紧的,忽颠颠跑远了。有几个去追他,没追多远又回来了。他们都怕自己走了推土机又动起来。只有原先站在牌楼下的老孟没回来。
推土机就像一个使脱力气的壮汉,油黑的烟囱哈哈地喘着白气。实际上,推土机的力气永远都不会使脱。驾驶室里的王三这时拉开玻璃,探出脑袋喊那边的张智尧:
“哎!”
张智尧排开众人,抓着脑门上湿成几绺的头发走过来:“怎么不动了王三?”
张智尧是王三家邻居,两人不间断打一场牌。
王三笑着掏一支烟给他,“歇一歇,喘口气。”
“刚才又是一个整罐?”王三边点烟边向远处探头探脑,那个跑掉的人连影子都看不见了。
“抱得就跟他妈的牌位子似的!还不知里头有没有货。”张智尧哼一句,不小心把烟呛进了肚子,吭吭咳出两眼泪。
“早前不是已经弄过一罐?不能每个银元都给你吧?”王三说。
“×!不是知道得迟,亡羊补个牢,还不待见这些银元呢,知道多少人都拆出瓷器了?银元和瓷器比起来,那还算个东西?!”
“有钱难买早知道。知道这片破烂底下黄金白银的,贷高利贷也要买它几处。”架在车窗上的胳膊颤了颤,让烟灰掉下去,王三又说,“你说也是,懂得真枪实弹留点纪念,就不懂顺便留个字条提醒提醒?让人耻笑这群傻瓜他们就不寒心?!”
张智尧笑喷了:“字条?还让他们从几百年前给你打手机呢。”
那边许多人都彪圆着眼望他们,王三把头往回缩了缩,又悄悄塞一支烟给张智尧:
“光顾开这玩意,好事都给别人做了。老张,你这回站个有利地形,给兄弟也抢个,哪怕就一个?”
人们涌过来,手指头搡得像刺刀丛林,王三看到头发白花花的清华叔,竖起脖子站在最前边,他说什么没听到,被一片嘈杂声淹没了。
王三猛拉开玻璃又猛关住,喊张智尧一句:
“哎!记着啊老张,一个也行!”
2
北坛东街现在叫迎新街。迎新街的规划长度是五公里。在向东走了还不到一公里的时候,陡刹了一下,挺起一座高大的牌楼。老孟的皮卡就打在牌楼下。迎新街狭长而华彩,人们从这个门出来,又扎进那个门,像一条被催动的水流。往前,人们还能看到牌楼后密密匝匝堆挤的那些老房子,现在,似乎顺这楼谷吹去一股劲风,一下吹出一片广袤的空阔。老房子们像长了翅膀,一夜间瓦砾无存。实际上,老房子都是零零碎碎给拆掉的。
老孟也零零碎碎在这儿守两个多月了。
老孟操着一口漂亮的普通话,人们都说不上老孟是从哪儿来的。老孟自己也闪烁其词。他不让他们知道是有道理的,假如他一旦消失,人们也无从找起他。但老孟还是尽量和他们打成一片,他经常揣着许多钱,他也知道人们都知道他是装了大把钱的。他尽可以带一些精壮的后生当保镖,但实际上他只带了自己的老婆,有两天还把女儿接来了,给人的印象,就像他们是来旅游度假的,收旧物只是副业。他也不和他们一起哄抢,总是规规矩矩站在牌楼下,笑眯眯看他们饿虎扑食一哄而上。然后等到得主过来,很抠门地双方杀上一阵价。
只有空地上的喧嚣散尽,老孟才会踱着步,走到他们中间。一人丢一支烟给他们,然后搂住衣服点着,就着到处撕咬的黄风,低声讲一些历史。人们也低声问他一些知识。一当那儿又热闹起来,老孟必快步走出去,怕自己沾上什么嫌疑似的。位置也似乎永远不变,牌楼下,皮卡上。
开始的几天,老孟收过一件宋代官窑的青花瓷瓶,以后他就再不收了。他住的旅店后面就是文管所,文管所的老刘每天都和他一样,是混乱中最四平八稳的人。有天,老孟主动找到老刘说他对大件不在行,不敢再胡乱收了。老刘很高兴,还请他喝了酒。老孟把皮卡玻璃上贴的打着“收瓷器”的白纸撕掉,进附近的美工部换上“专收银元”,显示着日子越过越惨淡。也标明在收买旧物这件事上,和老刘彻底划开了分野。实际上,等房子全倒,瓷器的气数已尽,银元的春天来到,但老孟还是极为谦逊地征询过老刘的意思,老刘说,古币他也是不懂的。
老孟最值得骄傲的是收过一块元代金元宝。此后,就尽皆是各代银元。这回,他追上的这个人罐子里的都是制钱。在那人的家里,他很仔细地翻看了一会儿,先说为敬:“我给你三十,让我随便挑五个,或者五百,把这一罐都留给我,你看怎样?”
那人想想,吸取先前和老孟老刘打交道的经验,回价说:“不行,最少得八百。”
老孟说:“八百有些多了。你们都是空手套白狼,我吃住在你们这儿,每天光成本也不是个小数,能不能按六百八,一路发,大家都顺?”
那人回头看坐在炕上的老婆,老婆没主意地笑笑,于是,那人把还没落尽的汗一抹,痛下决心,说:
“不行!八百,少一个子儿也不行!”
老孟满脸苦气提溜起罐子,直说:“唉,谁让我注定亏也亏在这上头!你们吃了这个甜头,劝你还是收手,人们都抢红了眼,看出来了,非到打出脑浆才安生。”
老孟又给了他们二百,合成一千,叫他们赶紧离开。这人是租房户,住哪里都不误到街上卖羊肉串。
回到旅店的“家”里,老婆问他这么一些小制钱,八百也就算了,何苦还白给他二百?老孟正掌着一瓶碧绿的北京二锅头二两装,脸红扑扑的,说:“好几个月,白渡你这个徒弟了。知道这是什么品质的制钱,什么年代?什么币材?什么形制?告诉你,我随便掏几个,就能把那一千划回来。”老婆很温存地把头一歪,停靠上他的肩头。他回手在老婆的脸上拍拍,很幸福地小声呵口气。
当晚,老孟就又把“专收银元”撕掉,换成“专收制钱、银元”。银元时代也该零落了。
3
当晚,王三去东隔壁找张智尧,出门,看到西隔壁的清华婶出来泼泔水。他们现在都租住在拆迁区外围的另一片平房里。
“婶,清华叔今天也去工地了。”
“没有呀?他在床上躺几个月了,脑血栓你不知道?听说好多人都在那儿淘到东西了。”
“咦!这就奇怪了,明明看到他的,还嘴叨叨着,不是他说,我也懒得理那帮人。几时动还不是由爷说了算。”
“真没有去!三,你肯定看花眼了。”清华婶泼了水,歪着腰往家走。站到了门边,又扶住腰,回身问:
“你媳妇快生了吧?”
“肚鼓得像个地球,就担心它一不小心给炸了。”王三笑嘻嘻的。
“临盆的时候记住叫婶一声,那些医生,看起来个个好像七经八验,我看他谁都没婶这个老手
脚在行。”老街上的人都知道,年轻时,清华婶就是个接产婆。
王三答应着,去敲张智尧家的窗户。张智尧家是那院子临街的两间小房,他老婆还开了个小卖部,但没什么生意,人们有的买,走两步,都到牌楼下的集贸市场去了。他家的护窗板就早早打上了。
张智尧老婆从猫眼看到是王三,朝里大声说:“王三来了。”然后把门一点点推开,好像那门也有百叶。王三跟着她走进去。
小小的一片家里点着蜡,盘碗散了一炕,那只老猫蹲伏在炕盘中间,看见来人,嗖地蹿下地,跃上对面的衣柜,继续俯伏着,眼睛紧盯住王三。张智尧盖被子躺在墙角,一张瘦脸汗水津津的。
“怎么了老张?”
“这不,上了一趟工地,带回邪气了。我说那天上掉下的东西就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还不听。”他老婆说。
“老张你最后又拿回什么了?”
张智尧张了张身子,看样子是想往起坐,王三按住他。
“你在也知道,又不是每一铲刀下去都能见金见银,那金钱还不真如粪土了?”张智尧企图笑,看样子,还是很为难,王三不好连他的嘴也封住,“扫兴了。再不去了。再去,让老祖宗把我也拽到底下去。”
“人们又抢腾了一回,好像。我从车上看见的。”王三想想,说。
“就是个好像。”张智尧说。
王三还想问问他下午看没看见清华叔,见张智尧已经又躺下去了,嘴角很痛苦地抽着,叮嘱他老婆中邪一定要找大仙爷,老街坊里的胡二爷就不错,就是不知人现在在哪,还一定要少说话,一定多躺几躺。
“你们点根蜡吃饭挺有情调。”王三最后对出来关门的张智尧老婆笑一笑。
“×!明知道旁人靠不住,亏我还花了两根烟。”又走了一截,他对自己说。
回了家,王三给在西区住的王四打电话,要他明天无论如何过来一趟。王四在电话里问说有什么要紧事,“你知道我们请假都要扣工资的。”他老大不情愿。
“你过来。我给你发一天工资。”他哥加大声说。
“你真要老四过来给你抢呀?不就是一块银元。”王三老婆摸着大肚子,隔一会儿伏上去听一听,她只能把下巴支在上面。
“要不是看你肚子挺得像个地球……”王三咯咯地笑着,他觉得这实在太好笑了,像个地球。
“你还打算让我帮你抢呀?”老婆说。
王三说:“有老四就不用你了。都是老祖上留下的,凭什么有别人没我的?抢不到一个我就睡不着觉,吃不下饭。”
“可你也没少吃。”老婆有些害羞地低声说,“别的什么也都没少做。”
“前三后三。你以后再不能了,会小产的。”
王三把老婆拉过来,在她充满妊娠斑的脸上亲了一口,“你就不怕把我憋坏?你就不怕你往后想了,我都憋坏了,你现在不让?”
躺下后,王三说起今天看见清华叔的事,“可清华婶说他根本没去。”
“清华婶那么说,那清华叔就是肯定没去。”
“可我明明看见是他站那儿,”王三说,“这真是见鬼。”
“难道真是我看花了眼?”他又说。
4
王三把推土机开到工地,下来背着手,踱步往牌楼下的早市去吃饭。工地上已经集结了不少人,热烈地对昨天进行战况回顾,并更加热切地期待今天。王三故意从他们面前摇过,他们似乎根本没看到他,有人甚至还朝他脚后啐了一口,以为那是一块石头。
“×!”王三心里骂。
在一个馄饨铺子前,王三看到坐在那儿已经吃完、正抽烟休息的老孟夫妇。老孟斜着脸,王三从他的变色镜上,看到一枚小小鲜红的太阳樱桃般给从云层吐出来。
王三想,既然张智尧不肯说,向老孟问问昨天后边的情况也是一样,谁拿了东西都会接住找他。但他还从未正式和老孟说过一句话,他实在不知该怎么和他说。在王三眼里,也许只有老孟才是个不那么市侩的人。但要是老孟能主动说起来,那就轻松多了。
王三要了一碗馄饨,坐在和老孟一条的长凳子上,又起来,往老孟那边去够香菜。他的头发都要垂到老孟的眼睛上了,老孟好像瓷在了那里,除了烟雾是流动的,别处一动不动。王三看到他暗沉的眼球一眨不眨紧盯住天空,并没打算因自己的头发快要钻进去有所改变。
“装×!”王三又骂。
他快速地把馄饨搅进嗓子,见王四骑自行车过来了。
“来,四,吃碗馄饨。”王三喊。
王四摇头摆尾的,端着馄饨就像端着一碗农药,“我要是多加一小时班,还能多拿几十块钱呢。”
“几十块?”王三问。
“二十五。”
“我给你一百!”
“你凭什么给我一百?你让我做什么?”
“你就给我站在铲刀前,”王三看了看走远的老孟夫妇,他们没上旅店,向商店里走进去了,“你给我死死守在那儿。”
“我守那儿干什么,我等你把我也当土铲起来?我怕你把我的脚给铲了。”
“我没事铲你脚干什么?”王三又看看那边站着的那些人,王三能看到一些人脸上莫名其妙打着漂儿的笑。
“你没事你叫我干什么?”王四简直要哭出来了,他看看表,“只有十分钟了,十分钟你怎么让我骑到厂子去?”
“你不懂!你×也不懂!”王三说,“我说过了给你一百,就是买你一天不上班。一会儿你给我老老实实站在铲刀前。”
王三的声音很大,分量很足,把王四震住了。他把自己团成一团影子,随在哥哥身后。
上车前,老板打来电话,告诉王三今天应完成的区域。“主要是那棵树,那棵老松树!无论如何今天一定要铲倒它!”在保证书里,王三也是这么应承过的,除了不能怠工,还有就是指哪打哪。
王三想起老松树正是自己家的门口了。他记得他小时候常和王四一起爬上去摘松果,王四总爬不上去,他就故意把松果从上面扔得到处都是,让他四处奔跑着去拾。结果,他还是爬不上去。
“四,你就站在松树下等我过来。你守得好。”王三说。
王三上了车,拉杆向后倒了几米,又一推杆,铲刀像一只伏虎,猛沉下去,锁住一堆砖石,然后,哼哼呀呀向前推进。铸钢的履带发出错综的倾轧之声。人们远远观望着铲刀的倾向,并不向驾驶室里投去一眼,砖石都是表皮,在这一环节,所有人都还有机会再攒一把劲。
待土层出来,他们汹涌着往前了。
就在这时,王三看到了人群里的张智尧。王三跳了下去。
“哎!老张!”他喊。
“你这人怎么回事?怎么动着动着又不动了?”张智尧急匆匆走过来。
“你不是中邪了?”王三笑着,点一支烟,没给张智尧,“不是怕老祖宗把你也拽到底下?不是说不再来了?”
“中邪就不能好?这么多小鬼,老祖宗拽谁非要拉扯上我?我长得有那么孙子吗?我这两天手气差,求求你,赶紧动弹起来!”张智尧摆着手,又往人群里扎去。
“爷今天不动了!爷今天还就不挣这份窝囊钱了!”王三说。
“算了老三,你还是赶紧吧,”张智尧笑说,“我看到那边你把老四都动来了,你用他那么容易?你本来就没必要让我给你什么‘就一个,咱是好汉,就不能在关键时候吃豆腐。咱们牌局上见输赢,有本事。”
“这可是你说的,老张?”
“是我说的。”张智尧说。
张智尧重新站到人堆里,并摆好了一个冲刺的姿势。霸起手,每一根指头都红楞楞充血。要是有人从他两旁往前冲,总得先过他胳膊这一关。
人们也都是前呼后拥,一浪一浪的,仿佛美好的东西已然在望。实际上,王三一直没动,王三要等得人们决堤,等到人们耐心溃烂。最好是他们都过来求他,但这些迟钝的人,他们显然没有这样的打算,他们的目光烫豆子一样集中在推土机压着的地面上,把那儿灼得一片焦热。
王四跑过来了,“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让我来就是看你表演一动不动?牌楼也一动不动,我去看牌楼也比看你这样好受!”
王三拉开玻璃喊:“你可不能走,四!你乖乖站好那儿,等我过去你就往前冲!”
王四咬牙切齿地走回到松树后,自从单住出去,又结了婚,又有了自己的房子,又上了班,他就再也不想听王三的了。可他总是想到王三那两条钢管样壮实的胳膊,总是一闭眼就看到它们生硬地飞舞,就像小时候的多次。
“无聊你王三!”王四说。
推土机动了。
5
老孟胳膊上挂着老婆,像一叶扁舟,游进迎新街的商场。商场被外墙巨大的广告牌所挡,里面都开了灯。商场里的人个个光鲜亮丽。他们从电梯一层一层升上去,又一层一层降下来,然后在地下烧烤城坐了一会儿。
老孟说:“时间差不多了,该上班去了。”他让老婆仍然留在商场,或者回旅店去看电视。分工上她管钱,面上的事都不用她。
老孟回到旅店,把皮卡开出来,打到牌楼下,探起身,细细地擦起玻璃。偶尔回身察看一下那边的动静。
没有什么动静。人们像篦子插在那台推土机前,敌退我进,敌进我退,严实地形成一个圆。那棵老松树在广阔的空地上显得孤俏而不安,树冠像一头乱发,间歇抖动起来。老孟清楚了推土机是向着老松树去的。
老孟忽然想起什么,不再擦车了,转身钻进杂货店,提了一个袋子出来,又跑着往松树底下去。
“你们停一停!你们都停一停!”他站到推土机和人群中间,大声说。
人们都想看看这老孟要干什么,纷纷围了过来。王三也出来了。
张智尧讥诮他说:“不后边乖乖等着渔翁得你的利,跑这儿来找×的什么事?”
老孟看看张智尧,不接他的招,说:“你们知道这是棵什么树?松树没错,可它不是一棵普通的松树,它都有几百年了!它的骨头里有你们祖先世世代代的灵魂,它是一棵灵树。你们看这房子墙都倒了,就它还站着,它这是要最后看你们一眼!”
人们嘁嘁嚓嚓的,都觉得老孟有文化,说得对。张智尧也往后缩了缩。
老孟的话好像在什么地方触动了王三的心,他的眼眶有些湿。幸好推土机还没推到树。
王三走过来说:“老孟你说对了,这树就在我们老房子院门口,一直顶天立地的。老人都说他们知道的时候树就这么粗这么大,怕几百年也不止。”
老孟眼梢扫一下旁边突出来的王三,好像很给他的插话打断了思路,愣一下,马上又转向众人说:“既然是一棵灵树,谁都不能对它大不敬。今天要拆倒它,不得不拆倒它,那也有办法。”他从袋子里拿出一沓黄表纸,又拿出几板香:
“焚香烧纸!以谢祖上!求得应允!求个心安!”
众人都说:“听你的老孟!”
于是,老孟把香分开,让大家分头插在松树周围,他拿着黄表纸,一脸郑重地点着,膝盖一软,扑通跪在地上,双手分撑,向树叩了三头。
人们这才发现自己还痴痴站着,纷纷也都跪了下来,看老孟的节奏,一拜,二拜,三拜。
王三看到人们的脊背给老孟的脊背指挥着,像一只虚松的大手上下忽扇,就故意慢半拍给他们看。人们的内心仿佛被虔诚贮满,根本置若罔闻。最后,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是那么可耻地不合拍。
趴在他旁边的王四说:“这都遇到的什么事?铲树就铲,还给树磕上头了。”
王三说:“你住口!”
那天一上午都没什么成效。一个上午,老松树仅仅给顶翻了。真正的难度在它的根须,真正的玄奥也深藏这儿。人们早早就吃过午饭,聚在一起,议论这棵树当年附近的居住状况,他们的祖上又出过什么人,以此提出树下埋伏的可能性。老孟也参与其中,但人们征求他的看法,他都拂手一笑:
“你们的祖先,你们熟。”
王三把王四叫回家,王四很惊讶嫂子的肚子已经那么饱满:
“几个月了?”
“就差十来天。”他嫂子说。
她出去后,王三忍不住又笑了起来:
“你看它那样子像不像个……地球?”
“地球?”王四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们总不见面,两人喝了不少酒。王四本来不能喝,但是他喝得很舒畅,就喝了不少。到工地后,他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精气充盈。
王四已经知道这工地是怎么回事了。他没想到这地底下会有那么多宝贝。但他实在想象不出宝贝会是什么样子,要是让自己看走了眼,那可坏了。他一下变得很紧张,他想要是能有个地方先尿一泡那就好了。但他须臾不敢离开半步,他旁边的人都已弓起腰,捏紧拳,眼睛喷薄着平常难得一见的光亮,全身绷得像随时准备射去的炮弹,这又让他兴奋。王四左瞅右瞅调整着自己的姿势、步态,一会儿把左胳膊抻到前边,一会儿再把右胳膊抻到前边;又一会儿把左脚踩到前面,一会儿把右脚踩到前面。
光顾了这么着,没觉视线里一空。觉到了,人们已经蜂窝似堵到他的前面。
王四举着胳膊晃了两圈,怎么都看不到前面,他真恨自己怎么会那么轻敌。他简直是轻浮的。他往后退退,懊恼自己不能变成一阵风,从他们裤裆下穿进去。没错,他这么想到了。
所有人都没防住王四会从他们下边爬进来。他差一点就撞到铲刀底下去。
铲刀底下隆起的一堆土缓慢地翻撒着,像是那只铲刀也在找寻里面的隐匿。也许是王四启示的缘故,好多人都一下扑上去往怀里抱。当他们发现自己只是抱着一块石头后,王四又已不见了。
6
牌楼下的老孟被撞了一下,眼镜差点迎住皮卡的保险杠。他扶住车站起来,看清了那个疾奔的身影。那身影的熟悉程度让他微笑。
老孟开了皮卡,上车前,他还点了一支烟。在这几个月中,他还是头次开车去追一个客人。他判断这次肯定又是制钱。皮卡越过迎新街道路两旁一株株漂亮的松柏,越过阳光下环流的人群,又在新华路跑了一段,终于在一个书店旁,把自己横在了那人前面。
老孟看出他不认识这个人。实际上那里的所有人他都记不住他们,如果不是在工地,有“从工地出来”这样的标识,他大抵不会和他们多说一句话。而即便这样一些人,也很快会成为他的记忆。他敏感地觉察到,制钱时代也要寿终正寝了。
老孟笑眯眯下来后,还哈哈狂喘的王四看到了皮卡上贴着的“专收制钱银元”几个字,懂了老孟不是那些要围追他的人,喘息渐匀。
王四坐在台阶上,仍然把罐子抱得紧紧的,“收制钱?”
“对。”老孟说。
王四警惕地瞅瞅四周,觉得这可不是说话的地方。老孟似乎看出了他的担忧,让他上车:
“我是老孟。”
王四看看他车里的设施,没有暗藏的武器,又看看老孟本人,他上去了。
“你把我送到西区。”
“西区是哪儿?”
“我家里。”
老孟笑笑,这也许就是最后一个整罐了,即使为此多费周章也是应该的。他开了车,向着王四的指引而去。在车里,他一直谈笑风生,他看出,这年轻人可没有先前的那个好说话。
老孟给他讲太平天国。他隐隐感到,这和先前那罐一样,亦是太平天国最普通的小平钱。老孟说,太平天国钱币很有特点,钱文“天国”代表至高无上的天朝,“国”字取其简写国字,玉字去点,而代表“国中之王”,这个“王”当然是自称天王的洪秀全了。所以凡是太平天国钱币,国字皆无点,有点则为伪铸。
“你先随便取一枚看看有没有点?”
王四掏出一个,对住亮处,老孟见果然是小平钱。“对呀!是王不是玉!”王四惊叫,立即对老孟的信任增了一层。
“这就说明你这个罐子是靠谱的,但也不能完全确定。你再看看,制钱正面是不是有‘太平天国四个字,背面有‘圣宝两个字?”
王四再看,说:“正面是对的,背面这是什么字?不认识。”他举给老孟。
老孟看了说:“就是圣宝两个字,繁体。繁体才对了。”
王四愈发佩服老孟了。回了家,他干脆把罐子翻过,哗啦啦都倒了出来,让老孟一一过目。
老孟拿起一枚,他的眼睛随着拿起这个动作而逐渐明亮,他觉得,隐藏起来那句话是多么英明,“我路上和你怎么说来的?繁体才对,你看看,这个简体,你该认得出来了?”
“那是假钱?”王四显得很懊丧,他也快速地扒着,一直找到三个这样的简体“圣宝”,“还好,就三个。”
“看来这家人家也不怎么样,留这么多真品,却搭上三个伪币。”老孟很可惜地把那三个制钱放在掌心,掂了又掂。
他藏的那句话是,简体“圣宝”非但是真品,更是珍品,因为少,世间仅见。
王四的心简直要有些凉了,“讲个价钱吧。”
“先前那个得主我给了他八百,没有一个是伪币。你老实,又好学,我出一千,算我一份仁义。这三个伪币呢,你留着也是干惹一顿不舒服……”
“拿去拿去!”王四挥着手。
王四没想到,这么一抢,竟给他平白抢来一千块钱。他只想快点出手,快点拿到那一千块钱。
王三的电话就是这时打来的。他问王四怎么回去了,“我就知道你小子抢到东西了!”
“没有!”王四大声说,“我喝多了我累了我不能回来?”
“我就知道你抢到东西了。”王三说,“你等我过去给你一百块钱,你把东西给我。”
放了电话,王四搡着老孟赶紧把那罐子抱走,“你可别说你从我这儿收过东西。”
“我不会说。”老孟笑着,又是一声叹息,然后像丢石子一样把那三枚“伪币”丢进上衣兜,“你最好还是别去那地方了,那地方乱。”
“我再不去了。”王四搡着老孟。
晚上下工,王三果然过来了。王四的老婆正在做饭,她热情地让着很少见面的王三上去坐,“你别理他!他是来催命的!”王四说。
“我怎么是催命的,四?我花一百块钱雇你一天,你看这是一百块钱,”王三把一百块钱放在桌子上,“你把东西给我。”
“问题是我没有东西,”王四推了一下那张钱,“我也不要你的钱。我就是给你白守一天,我也不能要你的钱。谁叫你是我哥。”
“你现在知道我是你哥了?你知道我是你哥你就该把钱收下,把东西给我。”
“问题是我没有东西,我有什么东西?”王四心跳得咚咚的。那一千块钱他还没细细数,他一定要细细数一遍后,再拿给老婆。
“我见那人堆里没有你,又见牌楼下老孟不在了,这两个事情一联系,我就断定你把东西拿回来偷偷卖老孟了。”
“谁是老孟?哪来的老孟?”
“就是和你收东西的那个老孟。”
“就是让大家跟着他给树磕头的那个老孟。”王三强调。
“没有人和我收东西!我就是在你家喝酒喝多了,我累了我回家躺着。你要不信,你问问什么老孟,你问他他认识我?他知道我是谁?”
“这样,”王三换了个姿势,“不管东西是两个三个,咱们一人一半,咱们是兄弟,那一百块钱我还给你。”
“我给你一百块钱,我请你走!我请你不要再理我,你看行不行?”王四快要哭了,他掏出一百块钱,甩给王三,“我贴一百块买你个走行不行?”
王四老婆站在那儿,她好像看明白了,脸色一下阴暗下来。“他哥,老听说你为大仁义,你就饶了他吧,你就不要再逼他了吧。你们好歹都是兄弟。”
“我们是兄弟!”王三说。
“我用了你一天,说给你一百块钱,有没有东西,都给你。”他把钱压那儿,出来了。
“我们是兄弟!”走在黑灰的巷子里,王三狠狠地,有些悲凉地说。
王三一直从西区走回到迎新街。晚上的迎新街可真漂亮!各式各样的灯光像是灯光的盛会,把每一个角落都照得纤毫毕现,像能照到它们的骨头里去。每一个角落都坐满了人,喝着啤酒,就着烧烤,大声地,或窃窃地说着什么。
王三拣一个凳子坐下。
“要什么?”服务员过来问。
“啤酒。”
“还要什么?”
“烤串。烤羊蛋。烤羊排。”
“别的呢?”
“啤酒。”
7
此后的很多报纸在形容到第二天的拆迁工地,都会用上“天现巨坑”这个词。那个坑的确很深很宽广,像是真的能把整个天都装进去。作为开发商的老板,他们很难解释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雇了王三,像遥控一架玩具飞机随时随地给他派发任务。他们的约定里,并没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坑。
公安局技侦科的同志后来测量过那坑的高度,十米。长宽各有二十米。这是一个海量掘进尺度,那人是怎样玩命才在一夜间挖出这么大一个坑?他们也都觉得不可思议。
坑的三面都是直立的。只有一面,能看出开始是一个斜坡,后来才让坡慢慢直立起来。
王三就是从那个坡把推土机退上了地面,然后停在坑边上的那座土山前。这一切做完,太阳正好升起来,他就着太阳拍了拍手,看到自己的推土机就像一只宠幸了许多母鸡的大公鸡那么傲然。他到牌楼下去吃馄饨。
老孟夫妇依样坐在那儿,王三并不和他说话,王三和卖馄饨的说。王三说:“工地上好像撒了许多制钱。这么大,都写着太平天国。”
卖馄饨的当下就撇了勺子,连围裙也没摘,就往工地上跑。工地上已经又蓄起好多人,其中有张智尧,还有清华婶。他们好像都瞅到了那坑里有东西,试着怎么跳下去。
老孟再也坐不住了,他让老婆还是回“家”去看电视:
“太平天国‘圣宝差不多都找齐了,有一款‘通宝那才叫极品,你知道现在存世是多少?15枚。这地方小,却出稀罕。好在没把这些教给他们。”
“你也没教给我呀!”
“回来。回来。”老孟笑着,在她背上摸一下,奔了两步,还是稳步泰然向坑的方向走去。
也怪卖馄饨的叫得响,他一过去,就扯起嗓子大喊:“坑里有‘太平天国!坑里有‘太平天国!”好像给自己壮胆似的,结果,让张智尧先顺斜面出溜了下去,后边的人都跟着往下翻。
清华婶下的时候,下边许多人已经像饿牛见嫩草,换了一片又一片,到处是耸动的脊背。
“您不能下!”清华婶快要下到底的时候,仰头看见王三站在那儿。
“我怎就不能下?”
“您还得给我媳妇接孩子,她就这几天了!”王三说。
“谁接不一样?我上去给她接。”
“您还有清华叔,您要照顾他!”
“就是见他从这儿拿回去过东西……”清华婶再说什么,王三一句都听不到了,她已经下去了。她“麻雀在后”地趴在人们身后,王三看到她手里已经攥了不少制钱。
王三又跑到那边:
“哎!老张!张智尧!”
“张智尧我跟你说,我跟你打牌赌输赢!我跟你就赌银元和制钱!”
张智尧欢实得就像一条鲨鱼,在众多的脊背中游过来游过去,他好像根本听不出上面有声音。
“哎!老孟!孟辅陶!”王三一圈一圈,转过来转过去地叫着,人们都不知道,只有他知道老孟大名叫孟辅陶。孟辅陶哪儿的人都不是,就是他们老房子一个老街坊的儿子。十岁那年,他因为和家里闹不和,离家出走后再没回来。那时候,他还没有漂亮的变色镜戴。
“清华婶清华婶!”
“张智尧老张张智尧!”
“老孟老孟!孟辅陶孟辅陶!”
王三又一圈一圈地跑过来跑过去,一圈一圈地呼喊着那些熟悉的名字。没人能听到他的呼喊,他们都被抢夺的兴奋攫住了。他们因为获得的幸福而浑忘一切。
“清华婶!”王三流着泪喊。
“张智尧!”王三流着泪喊。
“孟辅陶!”王三流着泪喊。
泪花把他的眼彻底遮住的时候,王三不再喊了。他全身酥软地踉跄到推土机前,又爬了上去。又点了一支烟。又把烟扔了。
“清华婶!”推土机抵住了土山,王三流着泪又喊。
“张智尧!”土山在徐徐移动,王三流着泪喊。
“孟辅陶!”土山翻滚着向前,王三流着泪喊。
人们充耳不闻。人们浑忘一切。因为获得的幸福。
责任编辑:陈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