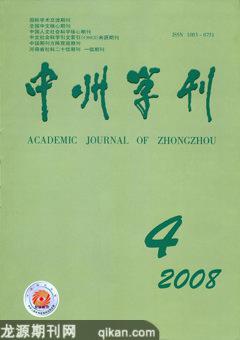圣人与乾坤:易学史上的象数与义理分途初探
摘要:易学史上象数与义理的分途,其实质是其所表达的义理究竟是圣人的义理,还是乾坤或者说卦爻象数的义理。孔颖达的《周易正义》与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分别代表着圣人神明与乾坤大旨两种不同的易学旨趣,后者意味着象数的神明,象数繁芜却义理平实而易于把握;前者则彰显出圣人之意幽微难测,其旨玄奥高远而切己受用,这就是不同的易学旨趣所导致的象数与义理的分途。
关键词:象数;义理;圣人;乾坤;易学
中图分类号:B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8)04—0156—06
收稿日期:2008—04—13
作者简介:曾海军,男,四川大学哲学系讲师。
象数与义理之学相分立的提法在易学史上由来已久,在古代思想史上也是一个常识。对于象数与义理二分的思想脉络,易学界已多有探讨。本文则是想以孔颖达的《周易正义》与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之间的比较为例,探究一下易学史上出现这种象数与义理分途的实质是什么。
一、引论:两种不同的易学旨趣
《系辞》开篇所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对此孔颖达的《周易正义》与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所做出的处理是完全不同的。孔颖达认为,《系辞》开篇“明天地之德”、“明天地之体”、“论天地之性”①,并强调虽言天地,却是“总兼万物”②而言。天地尊卑是言其德,卑高是言其体,动静是言其性,由此天地之德、之体、之性而获至《周易》当中的乾坤之卦、贵贱之位、刚柔之性。而沟通天地万物与乾坤卦爻之间的无疑就是阴阳二性,由天阳地阴过渡到乾坤卦爻的系列特性也是易学史上一贯的做法。看得出,经过孔颖达的一番处理之后,《系辞》开篇所云显得相当系统而条理。
与孔颖达从天地万物到乾坤卦爻的思路相比,李鼎祚的《集解》恰恰是完全分做两橛而言的,其言天地就不及乾坤,其言乾坤又不涉天地。像“天贵故‘尊”、“天地卑高”之类,远不如孔颖达所云“天以刚阳而尊”、“动而有常则成刚”③来得有内涵。但问题就是为何李鼎祚在《集解》当中要做这种选择,孔颖达在《正义》当中处理得更为丰富而圆润,李鼎祚作为思想大家不可能读不出来。但李鼎祚偏偏要选取内涵单薄而牵强的虞翻、荀爽等人的注,这其中必定是有缘由在的。事实上,李鼎祚在《周易集解》中保持着相当一贯的易学思想立场,他对注解的选取完全统一在他的思想立场上。在《集解》的文本当中,可以看出李鼎祚是强烈反对孔颖达以圣人设立乾坤卦象的这一易学思路的。
对于《系辞》所云“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孔颖达的《正义》注曰:“此则赞明圣人能行天地易简之化,则天下万事之理,并得其宜矣。”“成位况立象,言圣人极易简之善,则能通天下之理,故能成立卦象于天地之中,言
并天地也。”④“易简”是就圣人而言的,圣人能行天地的易简之化,而使天下万事各得其宜;或者圣人以易简之善而通达天下之理,故而可以设立卦爻象数于天地之间。这里的关键内涵在于,圣人是从天地到卦象的一个桥梁,是圣人通达了天下之理而设立卦象。在这个思路里,圣人是一个核心的担当者,如果没有圣人,不但卦象设立不了,天下之理亦无以通达。然而,李鼎祚的《集解》则引虞翻云:“‘易为乾息,‘简为坤消。乾坤变通,穷理以尽性,故‘天下之理得矣。”⑤注解当中没有出现“圣人”的字眼,“易简”是就乾坤卦爻而言,是乾坤卦爻自身在穷理尽性,而天下之理就呈现在卦爻象数之中。
可见,在李鼎祚的《集解》中,并没有一个圣人在起一个从天地之象到乾坤卦象的桥梁作用,实际上,李鼎祚是十分自觉地避免这样一个圣人的角色出现。他之所以要抽掉圣人这个桥梁,即出于要强烈反对孔颖达以圣人设立卦象的易学思路。在李鼎祚的《集解》当中,乾坤卦象就呈现在天地物象之间,完全不需要圣人来创立。可以说,这两种立场不但代表了两种风格迥异的易学思路,而且彰显出两种绝然不同的易学旨趣。这两种不同的易学旨趣所导向的正是象数与义理的分途。下文将进一步以两部著作中的注解为例展开比较,逐渐揭示易学史上出现象数与义理分途的实质所在。
二、圣人神明
就《周易》的形成而言,《系辞》直接提到过伏羲氏作八卦,其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诸如后世所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⑥,或者还有别的说法,大体上就是在《系辞》的基础上形成的。虽然这些传统说法的框架基本上遭到了现代人的否定,但笼统而言《周易》是由圣人所作,仍然可以从思想层面上立论。而在《系辞》文本中,更多的是笼统地言圣人作易,诸如圣人“立象”、“设卦”、“系辞”的言说相对充分。正是在这种《系辞》言说圣人作易的基础上,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做了更为充分的发挥,极大地凸显了圣人在易的形成与运用上的主体地位。
在《周易》形成的问题上,《系辞》直接表达过圣人作易的说法。其云“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就涉及圣人“设卦”和“系辞”两个方面。孔颖达的《正义》于此注曰“谓圣人设画其卦之时,莫不瞻观物象,法其物象,然后设之,卦象则有吉有凶”⑦云云,看来圣人是通过“瞻观物象”而设卦,卦象有吉凶而系辞以明之。与此同时,当《系辞》并未直接言说圣人作易时,却并不妨碍孔颖达往这上面去注疏。如《系辞》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下之道”时,孔颖达注曰:“圣人作易,与天地相准。谓准拟天地,则乾健以法天,坤顺以法地之类。”⑧这就是说,当《系辞》言及“易与天地准”时,在孔颖达看来此“易”即是圣人所作之“易”。如果是这样的话,《系辞》文本所言之“易”,经过孔颖达的注疏,均强调为圣人所作。从孔颖达的《系辞注》部分来看,其对“易”的注疏思路确实就是这样,处处凸显为圣人所作之“易”,下文将引的众多材料都可以表明这一点。
前文所及孔颖达注《系辞》中“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云“圣人极易简之善,则能通天下之理,故能成立卦象于天地之中”⑨,很显然,天地与卦象原是两回事,天地当然是本有的,但卦象则是由圣人设立的。而圣人设立卦象当然不是无中生有,所谓“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⑩,卦象即是由天地间的物象而来,圣人就是从天地物象到乾坤卦象之间的桥梁。同时,此注还表明了圣人何以就能设卦系辞,原因即在于圣人事先是通达天下之理的。圣人设卦系辞而作易,无非是要通过作易而将天下之理表达出来,或者就是说要将天下之理表达在易之中。可见,圣人作易必先通达天下之理,也只有圣人是完全可以通达的。孔颖达在注《系辞》过程中,确实在尽量地添入“圣人”这样一个主体的角色,凸显出是圣人在通达天下之理后,由天地物象设立乾坤卦象而系辞作易。另外,除了“圣人作易”,“圣人用易”是孔颖达的《周易正义》所凸现的另一个内容。
圣人用易与圣人作易只是一事的两面,圣人作易是圣人法天地自然之理而设乾坤卦象,圣人用易则是圣人法此易道而成就万物。这可以通过孔颖达所注“圣人法自然之理而作易,象易以制器而利天下”来理解。此注是说,圣人作易之后,又象易而制器物。但前文又分明说过圣人是“瞻观物象”而设卦的,如果两者要保持统一的话,就必须将此处的“物象”理解为天、地、风、雷之类的自然物象,并与具体的器物之象相区分。这就是说,圣人是观天地自然物象后立象设卦而作易,而后又象易而制具体器物。与此相应,圣人便是在法天地自然之道而作易,而后又法易道而成就天下万物,亦即所谓“用此易道以化天下”是也。孔颖达注《系辞》中“曲成万物而不遗”曰,“圣人随变而应,屈曲委细,成就万物”。但天下万物之理必定是相当隐微而幽深,圣人得法此易道极幽探微。总之,圣人用易也是孔颖达所着意凸显出来的一个内容,这就与圣人作易一起,是孔颖达就圣人与易之间的关系所涉及的两个不同的方面。由天地物象而至易再由易而至天下万物,始终是圣人在起着一种主导作用,圣人既由天地而设立卦象,又由易道而成就万物。如果没有圣人的存在,这一切就都无法展开。
不过,即便是圣人作易,又如何可能凭借区区六十四卦所组成的易系统来承载天地之道?易道弘大而幽微,神妙而不测,其所能获得承载天下万事万物隐幽变动至理之功效,全系于圣人的神明作用。所谓圣人的神明,即圣人须得能通神之性而后可具神之明。圣人之能洞悉万事万物隐幽变动之至理,正在于其具备神之明。孔颖达注《系辞》“与天地相似”云:“天地能知鬼神,任其变化。圣人亦穷神尽性,能知鬼神,是与天地相似。”可见圣人可与天地相似,即在于穷神尽性而备神明之能。赋予圣人以如此充分的神明性,使得圣人通达天下阴阳变化之理而作易,易由此而通达神明之德。孔颖达疏云:“万物变化,或生或成,是神明之德。易则象其变化之理,是其易能通达神明之德也。”在另一处又云:“言万事云为,皆是神明之德。若不作八卦,此神明之德,闭塞幽隐。既作八卦,则而象之,是通达神明之德也。”圣人以其神明之能作易而承载天下万事万物的生成变化,由此而通达神明之德。圣人作易而通达神明之德,又离不开易道的“神妙不测”。圣人毕竟只是作易,易道是天地自然无为之道在易当中的呈现,而自有其神灵妙用。即便是圣人穷神尽性而与天地相似,也只是法易道而已,故孔颖达疏云:“明易道变化,神理不测,圣人法之,所以配于天地。”
总之,无论是圣人的设卦系辞及其所作之易,还是由此呈现在易之中的易道,圣人的神明作用无疑是一个关键点。从天地物象到乾坤卦象而作易,再从易道幽微而至化成天下,都离不开圣人的神明作用。孔颖达在注《系辞》中“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时云:“此乃自然以变化错置于民也,圣人亦当法此错置变化于万民,使成其事业也。凡《系辞》之说,皆说易道以为圣人德化,欲使圣人法易道以化成天下,是故易与圣人恒相将也。以作易者,本为立教故也,非是空说易道,不关人事也。”这可以说是一段极具总结性的话,圣人法自然之道作易而错置变化于万民,或者易道以圣人德化而化成天下,这是事情的一体两面,其要即在圣人作易本为立教万民,以化天下。于此过程之中易与圣人两相交织,没有一种脱开圣人而存在的易,反之亦然,即所谓“恒相将”是也。
然而,与孔颖达的这种“易与圣人恒相将也”相比,李鼎祚似乎有意脱开易与圣人的这种血肉关联,甚至完全不顾圣人的存在,而径直将易显示在天地之间。与圣人在孔颖达那里的主导地位形成直接对应的是,在李鼎祚的《集解》文本中呈现出的则是乾坤二卦的崇高地位。虽然乾坤二卦在六十四卦中具有核心作用的传统由来已久,但在孔颖达那里,由天地之象到乾坤卦象必须由圣人来设立,没有圣人,乾坤二卦必定无由存在。而在李鼎祚易学当中,乾坤二卦的地位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它们的存在并不由圣人来设立。可以说,真正充分言明乾坤大旨的还是在李鼎祚易学之中,与孔颖达充分赋予圣人以神明相比,李鼎祚则是致力于明乾坤大旨。
三、乾坤大旨
与孔颖达正相反对的是,李鼎祚所收录的注解设法消解“圣人”的存在,同时,“乾坤”被置换进来,其意义显得更为重大。这两者是相辅相成,同时进行的,这在整个《集解》文本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与孔颖达凸显出圣人的主体作用一样,李鼎祚也完全就是在设法凸显乾坤的地位。如注《系辞》首章中“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引虞翻曰:“乾高贵五,坤卑贱二,‘列贵贱者存乎位也。”或者注“物以群分,吉凶生焉”引虞翻曰:“坤方道静,故‘以类聚。乾物动行,故‘以群分。乾生故吉;坤杀故凶,则‘吉凶生矣。”在这里,诠释爻位的贵贱或者爻象的吉凶,均以乾坤二卦之道来实现。这无疑还是有传统的,从《系辞》所云“乾坤,其易之蕴邪”下来,到其后京房、郑玄等人都十分强调乾坤的核心地位。在《集解》当中,承接这种乾坤为易之蕴的思想资源是十分明显的,如引虞翻曰,“《乾》以二五摩《坤》,成震坎艮,《坤》以二五摩《乾》,成巽离兑,故‘刚柔相摩,则‘八卦相荡也”,或引荀爽曰,“‘男谓乾初适坤为震,二适坤为坎,三适坤为艮,以成三男也。‘女谓坤初适乾为巽,二适乾为离,三适乾为兑,以成三女也”,都是以乾坤生六子的说法进行注解的,而这在《说卦》当中就已出现,可谓由来已久。乾坤生六子的卦变说或者十二消息卦的卦变说,都是汉易以来影响深远的象数学说,其内容都不离由乾坤衍生众卦这一思路。不过,在李鼎祚易学当中,远不止是对这一资源的传承。几乎就与孔颖达处处添入“圣人”一样,李鼎祚所收录的《系辞》注解文本当中,也是处处增益“乾坤”二卦。如注“易简”是“‘易为乾息,‘简为坤消”,注“刚柔”是“‘刚为乾,‘柔为坤”,注“鬼神”是“乾神似天,坤鬼似地”,注“昼夜”是“‘昼者谓乾,‘夜者坤也”,甚至注“知崇礼卑”是“‘知谓乾,效天崇,‘礼谓坤,法地卑也”等等,这种注解在李鼎祚的《集解》文本当中可谓俯首皆是。这还只是以乾坤对举来注解,而以乾坤二卦相互变动之道展开进行注解的就更多,此处不再一一枚举。应当说,在李鼎祚易学当中,这种以处处增益“乾坤”二卦来展开注解的做法,已经不是乾坤衍生众卦这一传统思路能够概括的。以乾坤之道来贯穿对《周易》文本的注解,是李鼎祚着意凸显“乾坤”而努力展开的。
当然,仅仅举证李鼎祚对“乾坤”的增益还是不够的,如上文所言,对“乾坤”的凸显与对“圣人”的消解是同时进行的。李鼎祚认为乾坤卦象是天地物象之间所本有,而并非由圣人设立出来。《系辞》首章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李鼎祚在《集解》中引虞翻曰:“谓日月在天成八卦,震象出庚,兑象见丁,乾象盈甲,巽象伏辛,艮象消丙,坤象丧乙,坎象流戊,离象就己,故‘在天成象也。‘在地成形谓震竹巽木、坎水离火、艮山兑泽、乾金坤土。在天为‘变,在地为‘化,‘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矣。”
这注解读起来十分难懂,比《系辞》原文显得复杂得多,几乎不知所云。所谓“震象出庚,兑象见丁”之类,运用的是魏伯阳的月体纳甲之说。“魏氏月体纳甲说的本质特征,即是认为在一月间月形的圆缺之象与八卦卦象颇为相似。”可见,剥开这一套术语的外衣,表达的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月球在一月间所呈现的不同圆缺之象,而这种月形的不同圆缺之象也就是《周易》的八卦之象。这样,《系辞》所云“在天成象”就成了日月(其实只是月而已)在天直接显现八卦之象,而“在地成形”由于没有相应的学说支撑,说得也就相对直白得多,所谓“震竹巽木,坎水离火”之类,直接由八种不同的事物显现为八卦之象。这样,无论是天上地下,八卦都是由天地事物的形象本身所直接呈显出来,换句话说,八卦卦象就直接呈显在天地之间,而并不是由圣人所设立出来的,从而取消了圣人观象设卦这样一个主体作用。
不过,李鼎祚在消解圣人的过程之中,必定需要完成一些具体的工作。由于《系辞》原文当中出现了不少对于“圣人”的直接言说,李鼎祚在注解过程中就必然要面对如何处理的问题。从注解所收录的情况来看,有一个策略是很明显的,即尽量将“圣人”还原为具体的历史人物。如注“圣人设卦”曰“‘圣人谓伏羲也”,注“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象也”曰“‘君子谓文王”,注“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曰“乾称‘圣人,谓疱牺也”,注“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曰“重言‘圣人,谓文王也”,以及注“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曰“谓伏羲画卦,穷极易幽深;文王系辞,研尽易几微者也”,等等。这与通常将具体的历史人物上升为圣人的做法恰好相反,充分说明李鼎祚确实在努力消解着圣人这样一个设计师的角色。即使是对于《系辞》所明确说到的伏羲设立八卦,那也不是问题。这在《集解》中的虞翻看来,“八卦之象原本就在天空中,即日月悬八卦之象于天空……日月所成八卦之象,在伏羲之前已经存在,而并非是伏羲所创造。称伏羲之作八卦,仅仅是说伏羲把日月在天所成的八卦之象,以卦爻象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至此,八卦并非由伏羲所创,而是直接呈显在天地物象之间就完全透显出来,所谓“圣人”其实是指称一些具体的历史人物,于是“乾坤”二卦从圣人的主导中最终凸显出来,而圣人的地位也由此遭到彻底的瓦解。
李鼎祚既然消解了圣人的这种主导地位而取之以乾坤的崇高性,圣人的神明作用无疑也就随之崩塌,那么由乾坤二卦所统领的卦爻象数来承载着易道的幽微,其间的神明功用就只能由卦爻象数本身来完成了。应当说,李鼎祚所彰显的乾坤之旨固然亦不离易道的神明与幽微,却分明是希望以更为具体而明晰的方式去把握神秘的易道,从而达到对天下万事万物之道的掌握,而这一易学思路确实有着孔颖达的《正义》所无法替代的特点和优势。遍读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文本,一个总体的特征就是力图将《周易》里的卦爻辞一一落实到具体的卦爻象数上面。这一特征在《集解》当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即便是以现代哲理的眼光看来显得最为抽象的论说,《集解》也力图一一化为具体的诠释。这样一来,原本读起来感觉到十分恢宏、磅礴而又难以把捉的高调,在《集解》当中呈现出来却变成具体、细致而又明确的言说。这种现象几乎通篇都是,此处试举一典型的范例以明之。如《系辞》有云: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下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及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这一章在《系辞》里面其立论之高远、陈言之高昂,堪称经典。虽然读起来可谓受用,但要明确把捉,恐怕就相当缥缈了。这种言说十分讲究生命体验层面上的受用,至于究竟能够把握到什么,就只能由各人自个去领悟了。说到底,这其实就是一种圣人的言论,既然是出自圣人,也就毋须让所有人能够以普遍的方式明晰地把握。然而,李鼎祚的《集解》似乎不这么认为。与这种缥缈玄远的高调相比,他更倾向于表达一些明确的内容。“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下之道”,其中的“易”无疑不再是圣人所作之易,而是天地间所直接呈显的易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正义》疏云:“仰观俯察,知无形之幽,有形之明,义理事故也。”以“无形”“有形”解“幽明”是韩康伯的做法,其注曰:“幽明者,有形无形之象。”而《集解》引荀爽曰:“‘幽谓天上地下,不可得睹者也,谓《否》卦变成《未济》也。‘明谓天地之间,万物陈列,著于耳目者,谓《泰》卦变成《既济》也。”与“有形无形之象”相比,谓“不可得睹者”和“著于耳目者”就感觉到浅显明确得多。至于其后谓具体的卦象,据李道平疏云,“《否》变《未济》,离日坎月失位,故幽”,“《泰》变《既济》,离日坎月得正,故明”,是将《系辞》的“幽明”落实到具体的卦象上面。可见,“知幽明之故”或“知死生之说”经由《集解》呈现出来具体落实到卦象上,就显得明确清晰得多。
按照李鼎祚的思路,乾坤卦象是直接于天地万物之间言说的,而并非是经由一个圣人所设立出来,由此《系辞》所言种种道理也就并非表达一种圣人的声音,而是直接呈显在天下物象之中。道理是圣人的言说还是卦象的给予,这也是孔颖达的《正义》与李鼎祚的《集解》之间的根本差异。前者玄奥幽微,在领悟之中走向圣人之境;后者直白显易,在习读之中掌握天下之道。可以说,尽管汉代易学庞大复杂,但实际上比起其后极富玄学色彩的魏晋易学却是直白浅显得多。
最后,上引材料中“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之类的结语,其旨高远可谓登峰造极,但《集解》所注依然不愠不火。无论是“范围天地之化”还是“曲成万物”,都不过是阴阳乾坤之道的作用,是体现在卦爻象数中的功用。将辞经过在象上的一一落实之后,即便是“神无方而易无体”也显示出相当的明晰度。“神”是自阴阳言,“易”是自乾坤言,“神无方”谓鼓万物而无常,“易无体”谓应变化而无定,其辞不同,其旨实一。与那种冠以圣人的神明作用相比,《集解》的乾坤之旨就在于明确浅显而易于把握,它给人一种于卦象的实际处可以把握得到的感觉,而不是让人进入那种于卦象之外玄奥空灵的高远境界。这正是在孔颖达的《正义》与李鼎祚的《集解》之间,同样是面对着易道的神明与幽微,所呈现出迥异的易学旨趣。
四、易道的象数与义理分途
可以说,不同的易学旨趣所导向的就是对易道的不同把握方式,由此而导致易学史上象数与义理的分途。对于幽微的易道而言,究竟是直接通过对卦爻象数的推衍可以明确把握到,还是借助于卦爻象数需要在领悟之中获得某种把捉?这就是李鼎祚易学与孔颖达易学的基本分际,对于前者来说,象和数本身就具有某种神明性,或者它就是某种神灵之物,可以通神通天,只要通过卦爻象数的推衍,就完全可以达到对易道的把握,由此而通向象数易学的道路;对于后者来说,具有神明性的是圣人而不是象数,是圣人以其神明功用设立了卦爻象数,易道才得以彰显出来,要通达易道就少不了对圣人之意的领悟,由此便导向义理易学之途。
可见,易道的象数与义理分途的实质在于,其所表达的义理究竟是圣人的义理,还是乾坤或者说卦爻象数的义理。也就是说,实质就在于表达的是圣人的义理还是象数的义理,呈现的是圣人的神明还是象数的神明。乾坤大旨意味着象数的神明,象数繁芜却义理平实而易于把握;圣人神明则彰显出圣人之意幽微难测,其旨玄奥高远而切己受用,这就是不同的易学旨趣所导致的象数与义理的分途。
由两汉象数易学以来而至李鼎祚的《集解》,所走的易学之道就是致力于对象与数的观察和扩充、推衍和运算,由此而达到对易道的把握。在象数易学一系看来,天地万物之间所呈现的象与数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天道完全可以通过对这些象与数的运作去进行把握。与此相应的,通过运用呈现在卦爻之间的象与数便可以获得对易道的把握,这与天地万物间的象数以及天道是完全同构的。虽然《周易》文本已经相当清楚地展现了卦爻之间的这种象与数,但显然还不是足够充分的。两汉象数易学以在“象”与“数”两个方面同时进行大规模的拓展而著称,它将当时的天文、历法、气象之学的成果都囊括进来,建立起庞大的象数系统。尽管诸如天文历法之类的问题可以衍扩得相当复杂,但与那种玄远之境相比,却显得实在得多,显示出易于明确把握的方向,其所具备的明确具体的实在特征,使得这一易学理路并不会因汉易陷入死胡同而丧失生机。李鼎祚敢于在孔颖达的《周易正义》之后收录他的《周易集解》,必定是出于对这一易学理路的特征所具备的不可替代性抱有充分的信心。
不过,自汉易以来,为了让《周易》的卦爻象数更为完备地表达出天下万物之道,卦爻象数确实被过度地推衍和扩展了,以至于最后演变成庞大繁芜、难以收拾的局面。这有其内在的某种必然性,单以区区六十四卦的卦爻象数,来应对各种复杂的人事变动现象,便难以避免出现这种结局。汉易的繁琐与迷妄可谓众所周知,反动于汉易而出现王弼、韩康伯易学的简约玄远之风,无疑具有思想史上的合理性。对于王、韩的义理易学而言,象数的神明功用转由圣人来承担,圣人通达天道之后,再通过观象设卦系辞而彰显易道。由此,立象设卦系辞就只是借以彰显的手段,如果离了圣人它本身并不能尽了易道神明。这一情形在王弼那里以一个筌蹄之喻生动地表达了出来,并充分显示出卦爻象数已从汉易的中心位置颠覆出来。作为筌蹄式的象数也不再具有什么神明功用,领悟“圣人之意”才是通达神明易道的不二法门。虽然到了孔颖达那里,王弼对象数所抱的极端立场已经获得某种矫正,但在树立圣人的主导地位上还是与王弼的易学理路一脉相承。可以说,这一易学旨趣所导向的义理易学在反对汉易的繁琐和穿凿上相当成功,而且尤其是在孔颖达的纠偏之后,与儒家的圣人教化传统也衔接得十分紧密。不过,尽管如此,义理易学的理路并不能取代象数一系所具备的特点和优势,易道的象数与义理分途形成了易学史上的一个基本分际。尽管现代易学领域的分化出现多元化的趋势,但象数与义理之学的对峙框架依然明显。
注释
①②③④⑦⑧⑨《周易正义·卷第七》。⑤《周易集解·卷第十三》。⑥《汉书·艺文志》。⑩《周易·系辞》。《周易正义·卷第八》。刘玉建:《两汉象数易学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988、989页。《周易集解·卷第十四》。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中华书局,1994年,第554页。
责任编辑:涵含中州学刊2008年第4期亚里士多德对主谓判断关系理论的探讨2008年7月中 州 学 刊July,2008
第4期(总第166期)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No.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