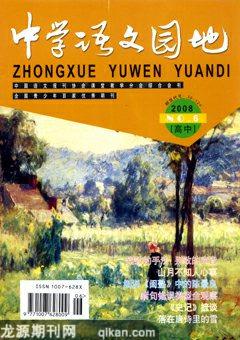细说《闺塾》中的陈最良
黄晓明
《闺塾》这出戏描写了小姐杜丽娘、侍女春香初次在闺塾听塾师陈最良讲课的情景。汤显祖以其生花妙笔,塑造了这三个呼之欲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相对于光彩照人的杜丽娘、率直泼辣的春香而言,陈最良只是配角。教参中对其做了如下论断:“一个十足迂腐的道学先生”,“严格遵守封建教义”,“逢迎家主”,“有一定的虚伪性”。这些话语将陈最良定格为一个活脱脱的“反面人物”。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不妨根据文本,一一细说。
说陈最良是“一个十足迂腐的道学先生”,“严格遵守封建教义”,那什么是“迂腐”呢?《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言谈、行事)拘泥于陈旧的准则,不适应新时代。从《闺塾》这出戏中,陈最良言语之中的“迂腐”表现为:一出场,他便咿咿呜呜地吟哦,潜玩《毛诗》;教导学生“以读书为事,须要早起”,后来更是用人人皆知的古人勤学的事例加以论证;授课从《诗经》入手,宣讲“后妃之德”与“思无邪”;当杜丽娘要为师母绣鞋上寿,请问鞋样时,他却引用孟子之言以虚对实;他满口封建礼教,说女子“止不过识字儿书涂嫩鸦”,“女弟子则争个不求闻达”。行事之中的“迂腐”表现为:严格作息时间,授课依注解书,教学手段和教学过程单一化,不识“闺房四宝”,对学生的追问极为不满以至当春香引逗小姐有花园“好耍子”时抡起了荆条等等。这些表现,的确说明陈最良是一个喋喋不休,满口酸话,一本正经,行为可笑的“冬烘先生”。
但从文本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几处矛盾:他虽不满学生的追问,但却学做了鸠声,以满足学生对知识的需求,充分表现了儒家所提倡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观点;他虽是依照杜府老爷杜宝的要求从歌颂所谓的“后妃之德”的《关雎》讲起,但并未抛弃人学,还是将此诗当成爱情诗来解读,开启了杜丽娘的春心;他虽不识“闺房四宝”,但对卫夫人传下的“美女簪花”之格大加赞赏;他虽认为女子不应参加应试,但还是表示要“和男学生一般儿教法”,且从时间上对她们做了严格要求;他虽认为春香会带坏小姐,要对她加以惩戒,但却说“又引逗小姐哩!待俺当真打一下”,一个“又”一个“当真”,就表明了他内心对这种现象是放任的,虽抡起了荆条,并非真心动武。另外,面对春香的一闹再闹,他也是一忍再忍,说明他的课堂教学并非“一言堂”,他的课堂纪律并非不可撼动。
凡此种种,我们只能认定,陈最良是一位思想上接受封建礼教熏陶,言行上尊崇雇主意旨,率真坦诚,心地善良,有着高度职业道德的人。
说陈最良“逢迎家主”,“有一定的虚伪性”。所谓“逢迎”是指“说话和做事故意迎合别人的心意(含贬义)”。“逢迎家主”表现为:他一上场就以“极承老夫人管待”而自得,教完课,又要“和公相陪话去”。这两句话,表达了陈最良对男女家主的无比感激和极力奉承。其实,我们只要通读了《牡丹亭》,就会发现其中的原因。在《腐叹》一出中,陈最良出场,作自我介绍:“12岁进学,超增补廪。观场一十五次。不幸前任宗师,考居劣等停廪。兼且两年失馆,衣食单薄。这些后生都顺口叫我“陈绝粮”。”一个60来岁的老先生,经历了多年的科场失意和“灯窗苦吟”,以及为“稻粱谋”而寄人篱下的教书生涯,即使变得如此世故庸俗,能说不是社会和环境造成的吗?另外,《延师》中,杜宝明确表示:“昨日府学开送一名廪生陈最良。年可六旬,从来饱学。一来可以教授小女,二来可以陪伴老夫。”和“公相陪话”是陈最良的职责之一,能说是“逢迎家主”吗?
所谓“虚伪”是指“不真实,不实在,做假”。具体表现为陈最良答应并接受了家主的条件,要将小姐杜丽娘塑造成符合封建礼教要求的“德女”和“贞女”,而实际上在坐帐授课的第一堂课上讲解《关雎》,所得的效果却与杜宝老爷的要求截然相反。这是陈最良故意做假不执行杜宝老爷的命令形成的吗?当然不是。充其量也只能说明陈最良的教学能力有限。
当然,在《闺塾》中,陈最良还表现出知识储备的欠缺,如对“好”、“逑”和“不知足而为屦”的望文生义的理解;还表现出他做教师在能力上的欠缺,如并不能依靠自己的学识来说服春香等等。
如若从《牡丹亭》的主题——“情”与“理”的矛盾冲突——来解释陈最良的所作所为,我们就能更清晰地发现:一个接受了几十年封建理学思想灌输的、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儒生陈最良,对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那些教条,说的和做的并不一致,在他的身上,“情”是起主导作用的,并最终是战胜了“理”的。
(作者单位:江西省吉水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