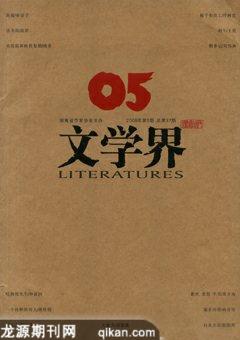大姐夫
羽微微
我一直很害怕大姐夫,他的出场总像带来风暴来临前的压力。他戴着眼镜,但仍可以看出有一只眼睛跟另外一只不太一样——左眼是假眼。这假眼后来因为和大姐夫的身体产生排斥而取了下来,那眼皮也因此而半闭着。但我还是觉得,大姐夫很冷峻、很帅,一点也没有残疾人的意味。连那只空洞的眼窝也带着一种“存在”的尊严。
大姐夫个子不高,腰板很挺。他有着鹰似的鼻梁和鹰式的傲气。大姐夫的父亲是一个药房老板,娶了大概七八房的太太,反正只留下了大姐夫这一男丁,像是二房吧。由于家境那时殷实,用他的话来说,“我是站在沙发上长大的”,他不吃蕃薯和芋头,姐姐对于这些食物的喜爱,他很是不屑一顾。但他热爱手工,现在大姐的房间,还保留着他设计和制作的小衣柜,里面横着小木条,可以用来放领带。床与墙壁的间隙架着木架,用来摆放音带和CD,很像是现在所提倡的智能式家具设计。
只是他的房间总是充满了药味。他一生嗜烟,经常只需划一根火柴点着烟,其后便以烟点烟抽个大半天。大姐那时对他这样抽烟很是有些担心,可他生来是不受束缚的,“我爱你,但和戒烟没有关系。”于是大姐总是想些法子,譬如说,大姐夫有时兴起弹起吉它,大姐就会说,很好听,不要停,继续弹吧。
弹吉它没法连续抽烟。大姐夫不知道这是一个甜蜜的陷阱,总是乐于上当。
我没说是甜蜜的谎言,是因为大姐夫弹吉它的确弹得很棒。他曾在市里的电吉它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大姐夫有许多的第一,包括全市的珠算比赛。他是在广州念的财会中专,那年头的中专生,比现在的大学生还要威风呢。他自学了油画,家里墙壁上挂了一些他的作品,周恩来坐在椅子上的那幅,周总理的英俊及隐忍,仿佛就悬浮在与画面很近的那层空气。还有一些风景画,还有一些他儿子小时候的肖像。
这个失去一只眼睛的生命,换了别的人,也许会令它的主人自卑及放弃。但在大姐夫的身上,却显得是那样的才华横溢,坚强不韧。而且他的坚强,像是并非来自抵抗外物,而是他本身就是这样的自给自足。他的身体不好,是因他嗜烟如命,后来还加上酒。这对他的身体是一种严重的摧残。他后来得了肺癌,大多因大量地抽烟而起吧。
小时候我闻到的药味,是因为他已经肺炎了,吃的是中成药,还有许多的药油,所以房间里总有一种中药的味道。一个才华横溢的中年人,加上傲气,加上药味,产生了一种很让我奇怪的敬畏之心。他负责市里的军乐队,因为单位的一些工作关系,经常在市下面的县出差。每次放假住在大姐家里时,难得遇他一面。偶尔碰上了,我就很紧张,吃饭也低着头,夹菜吃到嘴里时,反复听到菜在嘴里嚼的声音。
有一次是我和哥一起在大姐家玩,吃饭时间,没料到大姐夫突然回来。我和哥一来是因为害怕而低着头,二来是因为那时有个坏习惯——不捧起碗吃饭。在年纪小时,家里的饭桌刚好就是到嘴巴的高度,不用捧,直接把饭划拉进嘴里就是了。后来一年突然长个,一下子没适应,还是把头稍微俯着就着碗吃。大姐夫那次看到,大声吼了一句:“碗是死的,人是活的。怎么能人就碗!”我和哥吓了一跳,赶紧把碗拿起来。他吼了这句后,我和哥就把这坏习惯彻底改掉了,再也没犯过,以前父母说过多次,还是一直没改得彻底。
当我和哥十几岁读初中时,他开始和我们说一些笑话,很有一点把我们当成大人的样子。他天生是说笑话的人,因为他在表情上,在抑扬顿挫上,在掉包袱上掌握得很好。一般是吃饭的时候,他随意讲一些,然后我和哥听了笑得直揉肠子。怕他,听了他说的笑话又好笑又不敢笑,最终还是忍不住要笑。
说笑话的那个人,在上一个世纪,1999年,已经不在了。
大姐和我同父异母,比我大差不多20岁,她的儿子彬仔和我同龄。彬仔是除了体育和数理化及格,凡是文科都要补考。我倒是一直文科过得去的,于是在放寒暑假时,我便奉命前去做小老师。我每天清晨听到的,便是大姐夫咳嗽的声音,因为经过了一晚上,痰会聚集在喉咙里,一早起来,要先把痰咳出来才会舒服。
到后来大姐夫决定去做手术时,彬仔已中专辍学在家一段日子。他是自理能力很差的人,大姐因而叫我去她家住一段时间,等他们去广州后,我可以每天替彬仔弄点吃的。大姐夫决定去做手术了,家庭的关系融洽了许多,这是让我回想起来,感到欣慰的一点,至少大姐夫去世之前,应该是感到幸福的吧。在这之前我是常听到他们吵架,大姐性子急躁,而大姐夫经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没空理会她。彬仔从小生活在双职工的家庭,放假不用去幼儿园的时候,只好把他反锁在家,我听说过有一次,父亲去市里找大姐,门锁上了,彬仔从铁门下面塞出去一张矮木凳,然后俩爷孙这样坐着聊天等大姐回来。
彬仔一直认为自己缺少父母的关爱,因此而恨他父母亲。可对于他父亲,有着一种奇怪的尊重,他是恨着尊重父亲。年纪越大,他就越不想再跟他的父母沟通。这是大姐的心病,也是傲气的大姐夫的心病。但在大姐夫准备做手术的那段时间,三口之家的关系缓和下来了,彬仔可以和他的父母亲说笑什么的。大姐和大姐夫,也很是相亲相爱。
大姐夫原没想着去做手术。他知道他的病情很严重,医生后来说,不做手术,可能还活几年吧。大姐夫不怕死,他很有一种生死由命的心态。但大姐担心,她一直在说服大姐夫。后来据大姐说,有一次大姐夫不耐烦的应道:“好吧,答应你了行不行?我去做手术了行不行?”
那一段日子,大姐夫恢复了抽烟。也小小的有时候喝了一点酒。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他隐隐觉得,手术对于他来说,是一个迈不出去的坎。大姐因为他答应去做手术,也就不再管制他的抽烟。所以我觉得,大姐夫临走前还是有一点幸福的,可以抽他喜欢的烟,喝他喜欢的酒,特别是他的儿子,和他不再斗气了。这是他最欣慰的吧。
联系好了广州的医院,有一天晚上他们动身了。那是三月份,天气还有点冷。大姐夫穿了一件暗格的西装。他穿西装很帅,一般人很少能把西装穿得那么笔挺。我和彬仔送他们到了楼下,彬仔提着行李箱,我和他都以为要送他们到车站,但大姐叫我们回去,是夜班车,他们提前了一段时间出发。我想了想,他们夫妻俩好不容易关系这么的亲密,两口子一起坐着等车,不知道会有多少知心话要讲呢,也就没有再坚持。大姐夫接过行李箱,走了几步后,回头看我们还站着,就挥了挥手说:
“再见!”
后来手术的进况,一般从二姐那里得知。手术做后当天,二姐那边传来的消息是:切掉了半个肺,都是脓泡。但手术很顺利。
我们听了很高兴。手术后第二天,二姐,还有大姐同母异父的兄姐,都去了广州看望大姐夫。
回来后,二姐说,大姐夫那嘴唇白得像没血色一样。吓死了。她摇着头。
第四天,大姐夫单位的人突然派了车过来,让彬仔收拾一些东西,说大姐夫的病有变化,现在深切治疗部观察。当天传回来的消息,是病情控制住了。
第五天,父亲很希望能去广州看望一下大姐夫。可他年纪这么大了,出趟门不容易。大哥那时还在国企,无论如何也拿不到假。所以就派了我作为家里的代表去一趟广州。我匆匆收拾了一些东西,然后按留下的电话——那电话是姐夫在广州的大姐的——拔了过去。
电话通了,我说您好,我是宇薇啊,我是宇芳的小妹。那边传来一个很沉着的声音:哦。
我说:我要去广州看一下大姐夫,他住哪号病房啊?
“你大姐夫已经走了。”
我愣了一下,已经出院了?
我说:“走了啊?什么时候出院了啊?”
“不是。他走了。”
“走?到哪里了?”
“你大姐夫死了。”
直到我哭出声来,我才听明白这个“死”字的意义。我双手紧紧捏着话筒大声地哭起来,有一刻,我觉得世界因为大姐夫的去世而变得突然空旷。这屋子好大啊,这屋子好冷啊,我在这个屋子里一直旋着哭。
我听到自己嗷嗷的哭声。后来大姐夫的姐说了一些什么话,我记不太清,只记得她一直很冷静,还说“你不要哭了,你姐在这里,她要跟你说话。”
大姐在电话跟我讲了一些什么。我当时像是一点也没听懂,只知道用手拿着电话筒在哭。
哭了不知道多久,停下来。再一次发现,这屋子真的好冷啊,这屋子里的主人不在了,这屋子像突然有了生命又失去生命那样,好冷好冷啊!
我才想起要打一个电话回去跟父母讲,我一想到要父母讲这个消息,又忍不住哭了起来,一边在屋子里转着,一边哭。看到屋子里哪样东西都要哭一场。
到了后来,我拿起话筒,母亲接的电话,我说我是小妹。母亲急着问,怎么还没有起程?
我说不用去了,然后我就哭了起来,想她不伤心的,哽着嗓子哭。最终还是对着话筒用了全身心去哭,在母亲面前,这失去亲人的委屈和疼痛,这个哭可以得到最好的安慰。母亲听我哭,就在那边哭了。母女俩就这样在电话两旁啊啊地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放下电话后,慢慢想起来,大姐在电话里跟我讲,让我整理好大姐夫的遗物,“我也好回去不用那么的伤心,我想我是整理不了了。”我哽着答应。
下午出了门,眼睛肿得很疼。骑着单车,到外面买了蓝白胶袋。回到大姐家,把大姐夫的衣服从衣柜一件一件拿出来,放到洗衣机里,重新洗一遍。我一直洗到很晚,洗衣机一直轰轰地响。我把它们晾好,然后再把衣服放进去。再洗。
大哥终于能请到了假,去广州,把大姐夫的魂,领回来。他已经很安静,不用咳嗽了。不用照X光了。不用怕抽烟和喝酒了。他变成了灰和一些碎碎的骨头,装在一个小坛子里。哥一直把燃着的香伸到车窗外,魂跟着香走,遇到过河或过桥,彬仔就撒一把硬币,不要再刁难大姐夫的魂灵呵,这么远的路,他要走好久。
是我开的门,迎接大姐夫的魂灵,回到他的家。那一刹那,又是许多的泪水。小偏厅里,设了姐夫的灵堂,陆陆续续的,一些亲朋好友来看他,来哭泣,来安慰他的未亡人。
我有过一段时间,心里对大姐有着恨意。如果不是她一直劝着大姐夫去做手术,也许大姐夫不会走得那么早。医生不是说可以再活几年吗,也许能活十年!人有多少个十年啊。他才五十几岁,还没有退休,没有好好的享过晚年之福,就这么走了。
但大姐已憔悴得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我看她在大姐夫的斋期,虔诚地跪在蒲团上,一遍又一遍地念着往生经;我看她嘱我到外面买些素花,每天精心地插在灵堂的供瓶上;我看她跟着来悼念的人们说“只希望他这一走,算是解脱了病魔之苦。”我想,在这个世上,有谁能比她更爱大姐夫。当年他的成份不好,父亲曾剧烈地反对他们的结合,怕他的女儿会遭罪,可不到二十岁的大姐还是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当时一贫如洗的大姐夫,“嫁过去,屋子里只有一个米缸”大姐曾说。
她深深地爱着他,希望他能够活更长的日子。这个结局,她比我们任何一个,都更难以承受。
大姐夫的母亲,已经去到了广州,可她还没来得及去医院看她的儿子,噩耗已经传来。她没有再动身去医院,而是选择了起程回福建。她说:“我是来看我活的儿。人不在了,我还去看什么?”她安慰大姐:“你不要哭,你要恨他,恨他撇下了你,撇下了彬仔,不照顾你们。你要恨着他,不要哭。”
这个坚强的老太太,就这样走了。不肯见她儿子最后的一面。她要见她活的儿,白头人送黑头人,何等的悲怆。她不去见这最后一面,她的儿子在她的心里,就将一直还是活着的。
责任编辑:远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