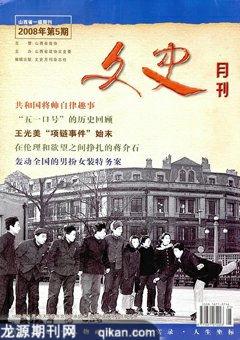难以抹去的记忆
焦祖尧
(四)
1969年初,我们在“群专”的人员统统被打发到“五七”干校。
大同市有两个“五七”干校,党群系统在离城6公里的同家湾猪场,叫“一干校”;政府系统在离城10多公里的奶牛场,叫“二干校”。
这两个系统的革命群众和专政对象,一起到干校去,一边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一边搞“斗、批、改”。
猪场的任务就是养猪,养猪要解决饲料问题。于是一部分学员去养猪,一部分到粉房加工粉面,一部分去种菜、苜蓿和饲料。报社文联的人大都进了粉房。把土豆洗净、切开、磨浆、过滤、沉淀;土豆渣子拿去喂猪,沉淀出的土豆粉面外销。这里最重的活儿是挑粉面。粉面沉淀成粉坨,一个粉坨重七八十斤,一次挑两个。我除了干别的活,挑粉坨是我的任务。那时才30来岁,正是有力气的时候,干这营生我乐此不疲。当时,我和市委办公厅档案处的老吴是被公认为有力气的(这是指被“专政”人员之中,革命群众中肯定有力气更大的),凡有重活的时候,老吴和我常被叫去干,譬如汽车来了,要卸车,一麻袋小米180斤,我背上就走,50斤一袋的白面,我一次能扛4袋。旁边有人说,这家伙看起来身体单薄,力气倒还不小。我听了也有几分得意,你们以为我是白吃饭的?所以有卸车这样的营生时我总会在场。有些事情对我也挺触动的,有几间猪舍的檩断了,需要整修,得先把断了的檩取下来,再把好的檩换上去。一根檩100多斤,没有起重机,怎么把它放置在房顶上?我虽是学工出身,厚厚的书本啃过不少,在这个难题面前却一筹莫展。没想到几个养猪的工人把这问题解决了。他们在两边山墙上打两个洞,利用杠杆原理把一根新檩顶上去,再取下折断了的旧檩。一根两丈多长的木料,一头横搁在一块石头上,靠近石头的一端垂直竖起另一根与房顶等高的木料,石头是杠杆的支点,横放的木料尾端上使点劲,垂直的那根木料便能把重物支起来。杠杆原理在中学的物理课上就学过,在实践中却不懂得应用。
真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我承认自己需好好改造。“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身上的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是需要认真打扫的。
造反派那种胡乱上纲上线的批判我无法接受,但我诚心诚意接受思想改造。劳动就是一条改造的途径。我不觉得掏粪是一种肮脏的营生,冬天我跳到粪坑里去刨粪,结了冰的粪粒崩到脸上、衣领里,还是照干不误。重新工作以后,文化局的一位老局长告诉我,在干校看到我在粪坑里使劲刨粪,他相信我在认真改造。
到了干校,我好像只剩下劳动和学习了,干校成立了专案组,我的日记都交到了专案组,由他们作进一步审查。我等待着结果。
常常有有趣的事情发生。有位老兄因历史问题被审查,和我“享受”同样的待遇,也在粉房里干活。每天,这粉房要提前开门,把小锅炉里的水烧热,上班后有的工序要使用热水。掌管粉房门上钥匙的人,不愿意多费那点辛苦,就把钥匙交给这位老兄,叫他早上去开门烧水。这位老兄有点受宠若惊,因为革命群众信任他,身份与我等就不一样了。早晨一溜小跑进了锅炉房,忙着生火烧水。上班了,大家发现水还是冷的,打开炉门,炉膛里火星也不见。问老兄是怎么回事,他说锅炉坏了,放了不少劈柴,也生不起火来。大家一看,原来炉篦上厚厚的一层“骨辘子”(烧剩的煤渣)没有去掉,他就在上面放劈柴点火,风上不来,劈柴哪能点着呢?再说劈柴上已经压了一层煤,他手忙脚乱好一阵折腾,还是点不起火,所以说锅炉坏了。看见大家都在朝着他笑,他就越发成了“丈二和尚”,一时摸不着头脑了。有人说,你连这点知识也没有,还大知识分子呢!好好改造吧!不好好改造真要成废物了。老兄连连点头,唯唯称是。
还有件事老兄也被别人笑话。拉土的小平车没气了,叫他打气,打气筒的出气口接不上轮胎上的气门芯,只好让别人来打。打了一阵,人家让他看看气打足没有。他没有去捏轮胎,而是两指去捏轮觳上的辐丝,捏了捏说,挺硬的,气打足了。
这两件事在干部学员中成了笑话。
有时,老兄也做出些叫人哭笑不得的事。我们一室住4个人,其中有位报纸编辑莫名其妙地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揪了出来。因为“认罪”态度不好,到干校后经常被揪斗。一天,要竖个篮球架让大家玩球活动,这位编辑被派去挖坑,任务当天必须完成。那天,我们收工后回去躺在铺上休息,编辑还没有回来。前面说到的那位市委副书记收工回去,见屋里有人在开会,不便躺下休息,就在外边转悠,转到我们屋前,从窗口看见编辑的铺位上没人,就进门躺下了。副书记上了年纪,劳动一天浑身疼痛,就想躺下来缓缓,一直躺到编辑挖坑任务完了回来才起来。
第二天,老兄就把这件事给干校领导组作了汇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躺在反革命分子×××的铺上,他们暗中肯定搞什么勾当。当天晚上,编辑便遭到批斗,叫他交代两人搞什么勾当。编辑说,×××躺在我铺上是不假,我一直在挖坑,如果我在屋里躺着,他又怎么能躺在我铺上?我一回去他就走了,能搞什么勾当!
在特殊环境中,人性中这一面或那一面就显露出来了。老兄在这件事上干得很不漂亮,在人们心目中进一步矮化了自己的形象。
1969年6月8日,干校领导组长宣布“专政对象”可以回家了,也就是说你自由了。
从1968年5月31日被隔离专政到次年的这天,我失去人身自由整整1年零8天!在这一年多时间里,除了思想,一切行动都在人们监管的目光之下,失去自由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
家里已接到通知,妻子包了饺子等我回家。干校离家也就是六七公里路,一阵小跑就到了家。单元门前,半张通缉令还在墙上,列数的“罪状”中还能看到一条,说“文革”前写小说为资产阶级复辟制造舆论(指长篇小说稿《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稿子在抄家时也被抄走了,成了我的“罪证”之一),“文革”中又“写小说控诉文化大革命”,这是指我酝酿写煤矿题材的长篇小说。站在半张通缉令前,我只有苦笑的份儿了!家里已变了样子,原本是一套两居室的单元房,现在一间屋子归了别人,厨房和厕所两家共用。原先两间屋里的床铺等家具塞在一间屋里,走路都困难了。原来岳母被赶回老家后,厂里房产科就把那间屋子收回去,分配给了一户工人。妻子说,对面那家搬来后,两家处得挺好。有时她上夜班,人家还帮助照看孩子,安顿她们入睡。
那天睡到半夜,敲门声大作。急忙起来开门,门口站着五六个人,说他们是厂里的保卫队,白天接到市里的通知,我被放回来了,回来后必须老老实实,不得乱说乱动,要按时回干校去。警告了一番他们就走了。我却再也无法入睡,瞪着眼直到天明。本来以为是自由了,原来这自由是有限的!
星期一,清晨起来就回干校。
(五)
1970年春节一过,干校的学员除了少数安排了工作,多数到农村插队落户。
插队之前,我们这批人中,大多数被宣布为人民内部矛盾,因为专案组审查尚未得出结论,我们还不是“革命群众”。我就是以这样一种特殊身份,被“革命群众”“夹带”去了农村。“夹带”一词,宣布时就这样说的。插队的地点,是大同市南郊区高山公社业家村。
1958年我曾下放农村锻炼,当时我在工厂搞技术工作,本来不是下放对象,因为爱好写作,想了解北方的农村生活,提出了要求下放的申请。我的申请被批准了,下放到山区南信庄乡的南信庄村。后来南信庄乡合并到了高山公社。应该说,这一带我并不陌生。
插队干部以连排的建制下去,连部在高山,报社文联算一个排,落户在业家村。
业家村只有60多户人家,一部分在梁上,一部分在沟里,2000多亩薄田,都挂在山坡上。没有副业收入,每个工分只有两角多钱(据说公社所在地高山的一个生产队,1969年一个工只开7分钱)。农民家里,除了一盘土炕,炕上两床又破又脏的被褥,就是锅碗瓢盆,几个瓮瓮缸缸,别无长物。10多年前在南信庄看到的是这样,现在在业家村看到的也是这样!
我们自己起伙,住在老乡家里。房东周子官夫妇和两个孩子,还有个70多岁的老娘挤在一条炕上,腾出一间房给我们住。和我同屋的是报社的两个干部,一个姓张,一个姓韩。
那时正在打战备地洞,“深挖洞”不仅在城市,在偏僻的山沟里也得“照办”。要从一个崖面上往里打洞,干这活计当然很累,累活当然就有我这个被“夹带”来的份儿。洞子已打进了300多米。洞高一米五六,宽不到一米,我和两个农村青年负责担土。我身高1.76米,担着土当然直不起腰,稍一挺腰就碰脑袋。两筐土有百十来斤,装浅一点也有90来斤。在洞子里猫腰挑百十来斤东西,比地面上挑一百五六十斤还吃力。在干校时,粉房里的粉面坨子,两个就有一百七八十斤,我挑起来也并不觉得吃力。
在打洞时却失败了。洞里只有两盏电石灯,一盏在刨土的工作面上,另一盏在洞子拐角处。光线实在太暗,担土往外走,一路不免磕磕碰碰,还摔倒了几次,趴在地上找眼镜。一次眼镜也摔坏了,于是成了半个瞎子,出来倒罢土再进洞的时候,眼前就只有一片黑了;走着走着光往洞壁上撞,弄得头上、脖颈里尽是土。
有时担着担着,我发现肩上的分量渐渐轻了,装土的正是我的房东周子官,和我一起担土的还有他的女儿俊女。周子官一边装土一边说:“少担点,这营生苦哩!慢慢来。”是很苦。但他们就不觉得苦吗?俊女才十八九岁,有时担得比我还多。老周不让我多担,我又抓起铁锹往筐里加了点土;等我放下铁锹,俊女却抢过扁担,挑着走了。
在周子官家的土坑上,深夜醒来后,听着山风在屋顶上呼啸,刮起的沙土一阵阵撒在窗子上,我辗转反侧,在难以入睡中悄悄舔着心上的伤痕。我至今还被人视为“异己”,业家村朴质的农民并没有歧视我,没把我当作“有问题”的人;“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5年,他们知道挨批挨斗的大都是些什么人。周子官的老娘经常这样叨叨:“丢下一家妻儿老小,来这穷地方受苦,可怜见哩!一家人在一搭块,喝汤咽水也暖和……”
我心里已经暖和了。人感到寒冷,不仅仅因为衣衫单薄,抵挡不住寒气。这一家子除了问起“几个孩子,女人干啥”之外,从不打听我的身份。他们自己的光景过得也很凄惶,午饭不过是两笼屉红面或莜面加上山药蛋丝的“墩墩”,一盆酸菜,早饭晚饭就是玉米糊糊和山药蛋了。一次我病了,周子官老伴儿却擀了面条,还打了两颗鸡蛋端到我炕头!那时我们集体起伙,轮流做饭,都是“半路出家”,没有一个“里手”,连油盐也掌握不好,打回一个月的食油,半个月就吃光,只能用酱油炒菜;有一次还把矾当作盐,炒出的白菜又苦又涩。往日还能对付,病中吃这样的东西就难以下咽了。房东不知怎的就知道我病了,把自己舍不得吃的一点点白面拿出来给我擀面。端起那碗面条时,我禁不住泪下两行。
1958年下放南信庄锻炼,那劳动确是认真的。冬天地里没有什么活儿了,白天可以搞水土保持,打圪塄,出肥土,晚上打井;一天记8分工,我们常常一天挣16分,都是你追我赶的。这次下来,说是插队落户,户口并没有下来,每月工资照发。到地里干活,就不那么认真了。有时到地里比划两下,就算半天劳动。村里知道我们下去并不是什么插队落户,过一阵就会上去的,也就不给什么具体任务,想干多少就多少。我们能为业家村做些什么?有一次我爬上一个山头,脚下就是流着一股水的黑嘴沟。我凝视良久,忽然想到,如果能把黑嘴沟里的水提上来,只要200来米管子,就能把水引上村后的高坡。这里是全村的制高点,修个蓄水池,修条渠道,水就能自流进村,搞个“土”自来水,也能浇村东的400亩地……
看来我并不缺乏想象,后来村里党支部还采纳了这个想法,或者他们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于是在黑嘴沟搞起了提水工程。
值得高兴的是,我还能用“副业”为业家村人服务:我买了把理发推子,当起了剃头师傅。
山里人理发是没有周期的。平时,业家村人理发要去高山或更远的峰子涧(也是另一个公社所在地);农忙季节,剃个头要跑十几里路,没人能耽搁得起。能为他们干点什么,这对我实在是无上的愉快。场院地头,他们劳作休息时,我便耍开了手艺;饭前饭后,我挎着小包上门服务。饲养员离不开牲口棚,我就在棚前为他们推头;马村的铁匠来干活,打铁炉旁也可以修理脑袋。他们不需要围单,不需要镜子,不需要躺倒刮脸的转椅;当然,他们也从不计较我的手艺,推完一个头,便会摸摸脑壳,连声说不赖不赖,这下精神啦!
他们喜欢自己是“精神”的,“精神”了不就美吗?他们是向往美的。过年之前,我把梁上凡是男性的脑袋都修理了,最后是长年卧炕不起的一个老汉,不时“吭吭吭”的咳嗽,吐出一口口浓痰。他让孙子扶他坐起,希望自己过年也能精神一些,我跪在炕上给他推头。梁上完了我跑到沟里去,路上碰到孩子们,见我就喊:老焦给我推推头!其实他们已推过头,不过是用这种戏谑的玩笑,对我表示亲热。后来,与业家村一沟之隔的左云县丁家村,也有孩子跑来,让我给修理脑袋。孩子们头上像一堆乱草,不仅沾满尘垢,还有虱子在头发里蠕动。
业家村的村情也不复杂,除了少数人在别村的小煤窑里背炭,多数人就靠种地为生。比较起来,外出下窑背炭的人家经济上稍好一点。村干部也比较团结,就是村支书与前任支书有点隔阂。说起来,两家还有点亲戚关系,村支书把前任支书叫哥,两家隔壁住着。哥手里的权叫弟掌了去,心中总是有个疙瘩。过年前曾发生过一件趣事,弟叫哥帮他杀猪,哥说行。那天,另一家的猪钻进了他家猪棚“串门”,支书忙村里的公务,平时也不喂食,认不得哪只猪是自己的,只知道自家的猪喂得比人家的早,抓住那头大的回头问哥:是这一头吧?哥说:我看不差啥!于是把猪拖出来,摁倒,弟弟一刀捅下去,拔出刀血也喷了出来。这时手揪着猪尾巴膝盖按着猪腿的哥说话了,用的是一种不快不慢不愠不火的声调说,伙计我看你是杀错了吧!这只猪头上有撮黄毛,不是你家的。
书记不认得自己的猪(猪都是老婆喂的),前任书记却认得,事先不声张,还说是“不差啥”;等到书记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才说“杀错了”。这是个心计很重的人。书记杀了人家的猪,拣大个的杀,这会造成什么影响?书记当时也慌了,赶快找到人家,连连道歉,说错杀了,真对不起!那家男人也很豁达,说没事儿,反正要杀了过年,请人杀还要三升黄米,书记给我省了,要谢你哩!
完全是小说里的情节,很有趣。我们在业家村生活得并不枯燥。
过完年回村,我们请村干部吃饭。知道我这个南方人还能做几个菜,就让我掌厨。年前就说好,年后回村要买些什么菜带去。那天碗碗碟碟竟也摆了一炕桌。连村干部12个人,竟喝了8斤白酒,不是一般的白酒,是拌种子的烈性白酒,60度以上。我不胜酒力,第一个醉了,由人扶着送回住处,路上就吐了。回去躺了一阵,没什么不舒服,又回到伙房去。他们还没散席,只是不见和我同屋的老张和老韩,我问他们去哪了,有人说回去了,已经走了一阵儿了。我说他们没有回去,就拉了另一个人去找。村里村外都找不见,找到井棚里,看见两个人正趴在井口。隆冬季节,山区晚上的温度在零下20多度,白天从井下打水上来,水兜里漏下的水都成了冰,井口的冰越结越高。他们趴在井口,吸井下冒上来温湿的水气,可能感到舒服,却忘了冰上很滑,一不注意会栽到井里去,那场景真叫人害怕!原来他们也喝醉了,胃里难受,不知怎么就到了这里,趴在井口吸井下的水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