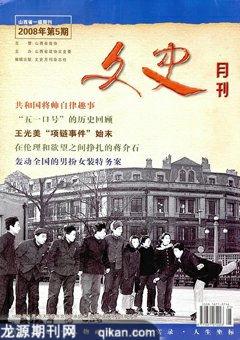天镇“八八”惨案
王其永
摘录两条国际法
《关于陆战法规和习惯的章程》规定:
第二十五条 禁止攻击或轰击不设防的城镇、村庄住所和建筑物。
第四十六条 家庭的荣誉和权利、个人生命和私有财产及宗教信仰和活动,应当受到尊重。
1899年7月29日订于荷兰海牙
签字国:日本国首席全权代表林董男爵
中国首席全权代表杨儒(余略)
天镇城沦陷
1937年8月中旬,国民党汤恩伯部由绥东前往南口抗击日军,激战数日,南口失陷;二战区第七集团军司令傅作义率领增援部队,在张家口、孔家庄与日军遭遇,几经交锋后全线溃退。此后,日军沿平绥路西进,继续吞食我大好河山。山西危急,天镇告急。
天镇是山西的北大门,集游览胜地和佛教圣地于一体的盘山,又是天镇东门户的屏障,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军东条旅团和伪蒙军先头部队进入天镇县境内,攻击重点直指盘山;阎锡山部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命令他的亲信干将、四○○团团长李生润据守盘山。9月6日侵华日军用飞机、坦克、大炮对盘山进行狂轰滥炸;夹击盘山的前哨阵地朱家屯、石家庄据点,猛扑朱家沟、大桥,直插盘山脚下。接着又出动飞机对盘山防御工事轮番轰炸,在炮兵排炮的激烈炮火掩护下,日军对晋军阵地猛烈强攻。四○○团大多是20多岁的热血青年,面对日军的进攻,誓死坚守阵地。这场阵地战打得异常激烈,从早晨打到中午,全团伤亡500多人;一营长席宝山身负重伤;二营长高保庸被一颗子弹横穿胸部,当即阵亡。李生润两眼呆呆地瞅瞅血肉横飞的部下,又望望活着的几个官兵,发狠地一跺脚,垂手溃退下来。坐阵阳高城指挥的李服膺不得不紧急下达全线撤退的命令,在天镇固守的4个团仓惶撤离,试图在大同集结。
1937年9月12日(农历八月初八),盘山失守,天镇城告急……
这日五更天,溃败的国民党第六十一军部队在一片混乱中潮水般地涌出西城门。城内死一般地寂静。到了清晨,城内一些绅士、商人和富户纷纷跑上街头,打探战情,一听说日军眨眼就要打进城来,全都惊慌失措了。东北街街长王国安蛊惑各家各户烧茶备饭,门上插小纸旗,对日军要以礼相待。他逢人就说:“日军也是人,人心都是肉长的,你给他个热脸蛋,他还能给你个冷屁股?你敬他一丈,他能不让你个十尺?”在他摇唇鼓舌的蛊惑下,200多名各类人士举着小纸旗,敲锣打鼓到北城门外迎接日军进城。
侵华日军痴愣住了,不敢贸然入城。从卢沟桥一路刀光剑影杀过来,还没见过这样的阵势。就先令坦克开路,汽车跟进,窥得城里毫无动静,这才长驱直入,进到城内。一个骑着大洋马的军官,手握指挥刀,扫视以王国安为首的满脸堆笑、毫无恶意的欢迎队伍。他狞笑着打了个手势,哗啦啦,一队日军恶狼般地围住迎接的人们,用枪托戳、刺刀逼,把还没弄清咋回事的人们撵进了瓮城里。
“不好,小鬼子要杀我们!快……”
没等西北街居民侯裕的“跑”字喊出口,其脑袋就被鬼子一刀砍落。懵懵懂懂的人们登时像炸了窝,发疯般地往北岳庙的碾道、门口逃去,哀叫呼救之声响彻县城。但城墙上早已站满了端着刺刀、凶神恶煞的日军,城门口架着一排机关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簇拥在一起的人们。又是那个手握军刀的军官一个手势,机枪立刻“哒哒哒”地吼叫,子弹像雨点般向人群射来,人们在一片绝望的哀嚎声中,栽倒在血泊中……200多名徒手的人们没有一个生还,连庙中的一位和尚也未能幸免。
日本兵还在尸体间巡查,发现有未死者,就用刺刀往胸口上戳,有十几个人就是这样被子弹射中后倒地,又在刺刀下断气的……其状惨不忍睹!
县城完全陷落,这是日军制造的第一起集体屠杀暴行。
屠城
如今的天镇县洋河生态公园,各种流光溢彩的华灯把广场映得如同白昼,人们聚拢在这里跳舞、扭秧歌、纳凉、散步,处处荡漾着欢歌笑语。然而,1937年的农历八月初八,就在此地,仅隔一条窄窄的洋河,不足百米远的霜神庙前,鲜血曾染红河水,庙旁一条沟渠里横七竖八地堆满了500多具无辜百姓的尸体……
王振文老人就是霜神庙集体大屠杀的幸存者,那年他19岁。他父亲兄弟6人,还有他的一个堂弟,合伙在大西街路南开了个面铺。
他说:“小鬼子气势汹汹闯进我家面铺,一个鬼子用刺刀尖儿顶着我的胸口,另一个鬼子伸出手,把大拇指和食拇指弯成个圆圈在我眼前晃动。我直当是他们要铜钱,就赶忙从钱箱里拿出两个小布袋,鬼子一看是铜钱,气得叽哩哇啦地叫骂,飞起脚把钱袋踢到墙旮旯,接着又冲我比划着那个手势。我这下明白了,他们是要银元。家里倒是有一些,可早让我爹和我二伯埋在了地下。我拿不出来,只得磨磨蹭蹭地取出纸烟、鸡蛋、西瓜给他们吃。鬼子们把烟卷揣进怀里,大口大口地啃西瓜,每啃完一块,就把瓜皮朝我的脸上甩打过来。我爹从衣兜里摸出少半张麻纸,抖着手在上面写了‘手艺人面匠,家中无大洋几个字递给一个鬼子。谁知那鬼子瞪着牛眼在纸上端详来端详去,猛地随手从地上抓起一把斧子,对准我爹的脑门儿就劈,我爹吓得腿肚子一软,跌跪在地上,斧子擦着我爹的头顶飞过,正巧打碎挂在墙上的镜子,‘啪啦一声响,反倒把鬼子们吓了一跳。朝我打手势的那个鬼子凶狠狠地一摆手,将我家两代8口全押出家门……
“上午10点,我们被押到东街公安局院内,院里已关了200多个和我们一样的黎民百姓。鬼子看见一个扎着红布裤带的小后生挺显眼,就把他从人群中揪出来推进屋里,我认识他,叫李喜和,17岁,新婚还不到10天。不一会儿,鬼子用红裤带蒙住他的双眼推到院中间,一个凶恶的鬼子冲过来,朝他的脖颈窝就是一刀,他没来得及叫出声就“扑通”一声倒在地上,由于气管还连着,嗓子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鬼子接着又劈了一刀……人们吓得一阵骚动,不约而同地拥向大门口,但马上又被鬼子们用刺刀逼回来。鬼子怕我们跑了,强迫我们解下裤带把双手捆在背后,没裤带或裤带不结实的,就用铁丝绑起来。下午4点,我们这200多人被押出北城门外,又像赶牛羊一样被驱到洋河北岸的霜神庙前,这里已聚集了被反捆双手的300多人。这时,有几个鬼子军官在庙的前后转悠,大概是找埋死人的地点。我手上捆的是一条新牛皮裤带,硬撅撅地捆不紧,我便悄悄地抽出了双手,还把紧挨我的王君的双手也解开了,接着我又给四五个人解开了结扣。一个叫张四如的老汉大概是料到凶多吉少,就大声喊道:‘哥哥兄弟们,小鬼子要杀我们了,能跑就赶快……
“他的喊声没落,就被一枪射中,栽倒在河畔。人们一阵慌乱,鬼子就用刺刀乱戳。我们这500多人又被押到庙西的一条长30多丈、深约3尺的水渠前,10个鬼子站一排,一次用刺刀扎10个,扎死后踢进水渠里,再扎下一批,简直如同杀狗宰猪一般。我清楚地记得,我和我二伯、四叔、堂弟是一批被刺的,鬼子拿我开刀,我被扎第一刀后眼前一片漆黑,昏死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昏昏沉沉中我感到脑袋像被针扎一样地疼,我微微张开嘴,觉得有黏糊糊的东西住嘴里掉,原来我额头上的血流到了嘴角。我强挣扎着挪动身子,再一瞅,整条壕沟内堆满了死尸。我是肩胛骨处和右肋下被扎了两刀,可能是流血过多,又昏过去了。后来在迷迷糊糊中,觉得有人在剥我的褂子,我的眼睛强睁起一条缝,细细一瞅,原来是王君。他光着上身,想从死人身上脱件衣裳,见我还活着,就把我背出壕沟,连夜逃走……”
就在王家面铺的男人们被押往东街的时候,南街又被鬼子擂门砸窗地撵出500多名男女老幼,他们被押到南街路东的马王庙前。庙分里外两进院落,里面的院子有一个长约25尺、宽和深都是15尺左右的深坑,是晋绥军留下的防空掩体,谁也没料到,这里竟成了平民百姓葬身的坟墓。丧心病狂的日军把男人们分批押进里院,每批进七八个,一排端着亮晃晃的刺刀的鬼子兵立在坑边,鬼子兵将刺刀捅进他们的背部,从胸前穿出,两膀再一用劲,把尸体挑入深坑……
日本兵杀累了,就就地喘歇、吃喝一气,然后再站起来屠杀一阵。后来他们嫌人们穿着衣服扎起来费劲,便逼着他们在进庙前脱光上衣,裸露出胸膛。有的人被连捅十几刀,最多的被捅了32刀才断了气。个别没被捅死的,跌入坑内也被上面的尸体压死了。
大坑被尸体填满了,日本兵就用棉被盖住,上面压上大石头,然后继续杀。他们嫌尸体堆在院内碍手碍脚,就留下七八个人,命令往庙堂内堆摞尸体。日军从上午10点一直杀到黄昏,尸体又堆满了三间庙堂。那七八个堆摞尸体的人,或仰面或朝下都被刺死在院中。后来经收尸队证实,马王庙内就有340多具尸体。
幸存者高弼回忆说:“那年我9岁,跟随大人们被押到马王庙前。我死死抱着妈妈的一条胳膊,站在一堆女人里;我哥13岁,随我爹站在男人堆里。等到半前晌,有个会讲中国话的日本兵向女人们喊话,让她们先统统地回去,小孩子也被统统带回去。奶奶、妈妈、二婶儿忙把我裹在中间带回了家。然而,一进门我们全被吓呆了:炕上有两个没穿裤子、躺在血泊中的女人,头发乱蓬蓬地遮着眉脸,认不出是谁。屋里被弄得缸倾炕塌,奶奶一看没法儿住,赶紧引着我们到了赵家巷我舅爷家。
“奶奶她们一天没吃一口饭,也没喝一口水,一直呜呜地哭。我知道,她们是惦记着我爷爷、我爹、我二叔和我哥。到了夜里,我六奶奶急慌慌地跑来,一进门就抓奶奶的胳膊,哭着说:‘她……她四婶儿呀,可……可不得了啦,男人们全……全被杀在马王庙里啦……六奶奶说,‘常佐身带8处刀伤,跑回来说,他还在庙院里看见我哥,满身是血,疼得直打滚……听到这儿,一家的女人们抱头哭成了一团。夜静后,奶奶圪拧着小脚同我们去马王庙寻我哥,刚一踏进庙门,就看见我哥死在半截子的缸沿上,上身扎在缸里,一只手在缸外,还握着半瓢掺血的污水。我跟着奶奶她们又在庙院内左寻右找,但我爷爷他们一个也没寻见,只看见靠墙根儿的地窖里堆满了尸体,窖口被一只挨一只朝着天的脚板子插得密密麻麻。我们把我哥用门扇偷偷地抬回来,装进一个破柜子里埋了……我奶奶整天披头散发地哭,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在马王庙大屠杀的同时,云金店前的集体大屠杀也在进行。云金店位于城西门路南,店前是一片开阔的场地。日军从西南、西北两街道的小巷中,押出来300多名成年男人,全都集中在这块空地上。押解的鬼子们迅速后撤,架在店门前的重机枪猛烈地向人群扫来,无辜的百姓一片片倒下去。一刹那间,积尸成叠,尸堆下淌出来的鲜血,染红了半条街。
住在该店附近、双目失明、年过半百的侯二,被拖出来惨杀了。一个叫张进恩的瞅见枪口一吐红火,便拔腿冲出人群,不料被一个小鬼子抽出军刀砍掉一条腿,血流如注。他怒视着鬼子喊道:“禽兽,给爷爷个痛快吧!”那个小鬼子举起刀,大吼一声,把他从头劈为两半。
大屠杀的幸存者张根花说:“我们张家是门大户,全家原有12口人,爷爷、爹妈、两个姐姐、四个哥哥、两个弟弟。云金店大屠杀前,我爷爷、我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弟弟没来得及躲藏,让小鬼子押走了。我爹叫张凤有,一向老实本分,他傻乎乎的当是搜查过就没事儿了,正好缸里没有一口水,就忙着挑起水桶出去担水,我的两个哥哥不放心,出去追我爹,到了西街路口,恰好碰上从东面过来一伙小鬼子,他们不问青红皂白,端起机枪就扫,可怜我爹和两个哥哥被打死了……算上云金店的大屠杀,我们张家拢共8个男人都遭惨杀了……”
张根花失声痛哭起来,后来她止住哭声,用衣袖擦干眼泪,又说:“我大姐夫叫吴唐,开了个车铺。他跑来看我们时,正赶上我们四个女的抱头哭得恓惶,还没听我们说完,他就气得一跺脚,从门背后提起一把旧锛子奔出门。他不是回车铺,而是直接到云金店寻小鬼子拼命。可他路过车铺时,正好有六七个小鬼子撬开车铺门闯了进去,他急跑了两步冲进车铺,二话不说,抡起锛子就砍,一连砍死4个小鬼子,一个鬼子惊慌失措地从背后朝他开了两枪,他摇晃两下,倒下去了……”
开个人诊疗所的幸存者周炳,一向推崇医道万能,有人劝他:“鬼子打进城来,见人就杀,赶紧跑吧!”他却不以为然,自信地说:“你们跑呀躲呀,全都对!可我不,知道为什么吗?我是医生,不管哪个国家、哪个军头儿来,就没个负伤的、得病的?只要有,就得请医生治。只有傻瓜蛋才跟医生过不去。”因此,县城沦陷后,他没跑没躲。不料小鬼子不买他的账,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他抓走了。他用他的亲身经历教育了自己。
周医生回忆说:“八月初八上午,十多个日军把我和40多个成年男人从东街押往西街,我一点儿也不害怕,一路上我边说边比划,告给日军我是医生。他们不仅不理会我,还用枪托戳我的脊椎。我气得把拳头攥得格格响,心里忿忿地骂:‘小鬼子,等你点头哈腰请我治伤时,看咋给你刮骨疗毒!我们被押上石桥,老远就瞅见云金店前死尸成堆,血流遍地。我的心一下子紧缩起来,心想:看来小鬼子逮住人就往死里整,根本就不需要医生。这下可完蛋啦,小鬼子不审不问,就在这儿送我们上西天了……我着实惧怕了,颤抖着腿走到尸体边,谁知他们没让我们停下脚步,而是把我们押进西城门瓮城的一个城墙窑洞前。”
他继续说:“小鬼子们用枪托戳着我们的屁股,让往洞里钻。我弯下腰钻进后,扭回头一瞧,我的本家哥哥周炬和吴正德在最后面,喊着、骂着就是不肯往洞里钻,我眼睁睁看着他俩被鬼子开枪打死。这一下,人们害怕了,抱着脑袋拼命往里挤。我被挤在洞口一根厚实的门框里动弹不得,这时,鬼子架着机关枪“哒哒哒”地对准洞口猛射,人们在哀嚎声中倒下一批又一批……我幸好有门框遮挡,只是暴露在外面的右胳膊中了两颗子弹。鬼子扫射过后,又扔进两颗手榴弹,炸死了不少人。深夜以后,我和另外五六个侥幸活着的人爬出洞口,其余的都死在里边了。这回我算明白了,对侵略者、杀人狂不能心存一丝幻想,烧、杀、奸、掠是侵华日军的常态,可怕呀可怕!我再不敢回城了,跑到村里躲了起来。”
日军的集体屠杀地点,主要集中在北门瓮城、霜神庙、马王庙、云金店前、东北城墙角、西城门窑洞等地。有材料证明,仅9月12日这一天,鬼子就惨无人道地屠杀了1490人!日军单独地或三五成群地在全城巡查,随意杀人、强奸、抢劫、放火,把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幼当成射击的靶子,见人就打,大街小巷,尸横遍地……
这一夜,全城一团漆黑,一片死寂,极度的恐怖笼罩着县城,死的恐惧笼罩着每一个家庭,被蹂躏的天镇城发出痛苦的悲泣。
“我真傻呀,全家的七条性命,让我给断送了一半……一想起这事,我,我真格儿地不想活了,我悔呀,恨呀……可,可上哪儿买这后悔药呀……”
说这句话的是一位头发雪白的老人,叫段发仁,曾是小学的老师,在搜集县志资料的座谈会上,这位76岁高龄的老人,双手大把地扯着自己的头发,他声泪俱下的控诉,至今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1937年9月12日的前4天,盘山打仗,城里的火药味儿呛鼻得浓,我老丈人赶着两头毛驴要接我全家到崔家山避一避。我犟嘴说,有晋绥军三九九团把守,县城丢不了!老丈人劝我说,管它丢了丢不了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去住上一阵子再说。最后我和老丈人各往后退了一步,先把我老婆和两个女儿打发走,留下我爹和我的两个儿子。谁知过了两天,李服膺一下令,晋绥军稀哩哗啦撤出西城门,比兔子跑得还快,一下子全乱套了。
“9月12日白天,我听得飞机‘嗡嗡地擦着房顶上的烟筒飞,坦克‘隆隆地开进城里来,我寻思着势头不对,就搀着我爹、领着两个儿子急慌慌地躲到南房的山药窖里,大气不敢出一口,一直藏到天擦黑。一整天粒米未粘牙,滴水没进肚,两个孩子嘴唇干裂得出了血,我心疼得比针扎都难受……一发狠,我就想出去弄点吃的、喝的,谁知刚上来走出南房,扑面就碰上六七个鬼子兵闯进院来,白晃晃的刺刀一家伙抵住了我的胸脯,我一时没了主意,颤抖着嗓音喊了句:‘有强……强盗……我喊的本意是想让窖里的人听见不要出来,不曾想事与愿违,我这一喊,我的两个儿子怕我出事,一前一后争着跳上来;我爹担心孙子出事,也颤巍巍地爬上来,我们全被鬼子押走了……我,我……我咋就这么浑?这么傻呀……”
段发仁老人悔恨得双手直拍大腿,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他一家三代四个男人被关到北城门瓮城里,那里早已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天已经黑了,看不清周围的情景,也看不清他们身边有没有熟人,只闻到尸体发出的血腥味,薰得人直恶心,许多人呕吐不止。人群渐渐地骚动起来,接着就向城门那边凑拢……鬼子们慌了,手电筒的光柱像蜘蛛网一样从四面八方照来,大概是怕人们闹事儿或是逃跑,就开始捆人,把每个人的裤带解下,用裤带先把每个人两手反缚起来,再把两个人的手臂捆在一起,然后又排成一行一行,互相不准挨靠。一阵拥挤,把段发仁一家挤散了。
段发仁老人的情绪稍微平静了些,接着说:“第二天(9月13日)早上,鬼子从我们这一行里拨
出40多人,这里边有我、袁美、邓三子、刘全义等。鬼子让我们每人在胳膊上戴上写有‘苦力二字的白布袖章,然后分成两队,一队分配到城外拉水,供鬼子们吃用,因为城里40多眼井里都有死尸;另一队清理大街小巷的尸体。我被分到收尸队里,我们20多个收尸人就近先到东北角上清尸,那里地势高,从老远就能望见鬼子们押解着北门瓮城那500多人,排成一列长队,弯弯曲曲,裤子全都耷拉在半腿,走得很慢。一些人被绊倒站不起来,鬼子们就拳脚相加,枪托乱戳,有的被打得不省人事,昏厥过去;鬼子还用燃烧的烟头烫一些人裸露在外面的阳具,惨叫声四起,鬼子却哈哈大笑……
“500多人被押到了东北街的大操场。操场东边有一座院子,院内有晋绥军挖的3条大壕沟,每条长11米、深3米、宽2米。鬼子们把大操场上的难民10人为一批,押进院内的壕沟沿上,用机枪射死,跌入壕内,再押一批,再射杀……我们20多个收尸的哪有心思收尸,心早被大操场那边揪去了,那儿有自己的亲骨肉呀!我泪眼汪汪地呆望着,监工的鬼子用枪托在我的头上砸,血流不止,我竟全然不觉……机枪疯狂地吼叫了大半晌,只打死一半人,后来刽子手们大概嫌麻烦,干脆把重机枪、轻机枪、步枪围成半圆形,一齐对着难民猛烈开火。顷刻间,枪声哭声喊声响成一片,还有个鬼子跑前跑后地照像……我完全像疯了一样,不顾一切,呼天抢地奔到大操场上,猛然看见我的一个儿子满身鲜血,‘林儿——我大叫一声,连滚带爬扑到儿子身边,一下抱住儿子,拼命地摇着、号哭着,之后我便昏过去……
“当我醒过来时,发现我躺在壕沟里,两具尸体压在我身上,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恍然大悟,我身上染着儿子的血,人家把我当作了死人……我爬上壕沟,没敢放声号哭,趁着天黑逃出城外,这才边放声号哭,边往崔家山踉跄……”
日军在9月12、13日两天的大屠杀,城内家家遭劫,院院遇难;大街小巷,行人绝迹,尸横遍地。
烧杀抢掠
事实,不容抵赖也无法抵赖。日军在天镇城里不仅杀人如麻,而且放火、抢劫、奸淫,极为残暴。
1937年农历八月初八、初九两天,日军兵分三股一边进行惨无人道的集体大屠杀,一边肆无忌惮地放火抢劫。县城沦陷后的两小时,南街一处唐代建筑——宏伟壮丽的慈广楼,被日军洒上汽油,一把火烧光;北街天镇最大的一家银行——实业银行被日军砸开门窗,一窝蜂似地抢劫一空,尔后点火把房子全焚烧了。
大屠杀中幸免于难的高日融说:“我家就住在实业银行附近,银行门面的大火,照得我家的院子通红。我忙溜到大门的门板后,朝外一看:鬼子们两手紧捂着鼓囊囊的衣裳在前头跑,后面衣兜瘪沓沓的鬼子连追带嚷。我怕大火引着我家的房子,就拿了把铁锹悄悄地爬上房顶,又望见那伙啥也没抢到的小鬼子追到十字街,忽地停住脚步,猛又拐到西街,像恶魔一般,噼哩叭啦直砸铺面门。‘积厚成、‘庆福元、‘义和成、‘天德公、‘德庆隆等挨着的几家大商号,厚墩墩的门板都被砸断了,值钱的货物被抢掠一空,不值钱的商品被扔得满街都是。劫后,他们又把这20多间店铺浇上汽油点燃,一眨眼的工夫,大火烧红了天,浓烟罩满了城,又赶上刮南风,呛得我连连咳嗽,差点儿从房顶上滚下来……”
东南街姓冯的老翁,使劲拽着一件羊皮袄不松手,小鬼子见争夺不过来,挥刀把冯老汉的脑袋砍掉,头滚到门外,身子还在门里。小鬼子这才把皮袄往肩膀上一搭,狞笑着扬长而去;鬼子们闯进王直和的家,用刺刀把他的衣兜挑破,裤带挑断,仍没搜出一块银元,气得掉过枪托对着他的脑袋不住地猛戳,可怜他当场毙命。
天镇城在痛苦中呻吟。妇女们的惨叫声、呼救声和鬼子的淫笑声,不时地传来。
9月12日中午,东南街三个年轻媳妇和两个姑娘,作伴儿躲藏在一间暗屋里。在日军挨门逐户搜查时被发现,她们遭到反复蹂躏。两个姑娘被十五六个小鬼子轮奸,因无法忍受痛苦和折磨,尖声叫喊,招致阴部被残忍地插进擀面杖。
同日同街,一位姓阎的姑娘出嫁的吉日临近,却被多个鬼子在她的闺房里轮奸,事后又将她活活扔进大水坑淹死。
同日午后,年仅15岁的张姓少女,光天化日之下在大北街被7个小鬼子轮奸,后又被鬼子揪住她的双腿,活活地撇成两半。
9月13日上午,西街的刘银兰、刘玉兰两少女,被鬼子们拖到慈云寺前轮奸。两个少女颤抖着赤裸的身子,紧紧抱在一起,上吊自尽……
仅两天的时间,确切落实姓名和地点的被害妇女多达上百人。含冤忍辱,带着肉体和心灵的创伤、沉默终生的妇女又有多少?恐怕永远也难以算清了。但西北街、东北街妇女受害最深,受害后上吊跳井者最多。据一些老人回忆,这两道街的20多眼井内,每眼至少有两三具女尸。
9月14日,一伙日军从四道街的住宅里搜寻出来六七十名妇女,就像赶去屠场的羊群一样将她们赶到大操场。日军就用刺刀逼着她们把裤子褪到膝盖下,挪蹭着小步,绕七横八竖的尸体转圈子,供他们消遣取乐。他们还用燃烧的烟头,一边去烫妇女的阴部,一边大声淫笑……
绝大多数的妇女,不论年龄大小,为了躲灾避难,有的剃发扮男,有的毁容换装,也有的成天躲藏在山药窖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妇女中也不乏奋勇抗拒者。西北街年仅19岁的贺月娥,面对日军毫不惧怕,连骂带踢与其拼打,终被枪击腹部而死。后被埋在北城门外,人们将其坟墓称之为“贞女坟”。
不完全的数字
天镇县城人口统计,1936、1937年无资料可考。
1938年 户1948 人口 8568
1937年9月12日 日军集体大屠杀 6案 死1490人
1937年9月13日 日军集体大屠杀 2案 死630人
1937年9月12、13日 日军零散屠杀400人
两天在天镇县城屠杀总计2520人
被杀害者中铭刻姓名于1946年纪念塔上的同胞计:西南街332人;东南街368人;东北街258人;西北街290人。共计1248人。
全家都被杀害的绝户者约420人。
受害的外籍客商及本地不知姓名者约820人。
“一个懂得铭记和反思的民族才是成熟的民族,一个成熟的民族才能对世界对人民担当更多的责任。”
“可以宽恕,但绝不可以忘记!”
记住吧,这惨绝人寰的灾难!
(责编 卫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