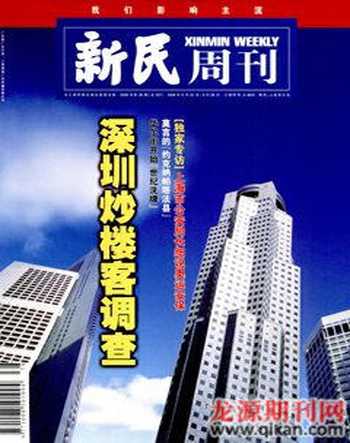藏在科学背后的强子对撞机
任蕙兰 吴 荻

LHC的成功启动真的标志着欧洲科学力量的复苏吗?
大型强子对撞机(Large Hadron Collider,简称“LHC”),一个长达27公里的实验仪器,于9月10日在瑞士、法国接壤的小镇正式启动,开启了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物理实验。正当全球粒子物理学家都为实验结果紧张地守候在电脑前,普通人似乎更加关注一些与科研无关的事。
LHC为何花落欧盟?
明眼人会发现,这个巨无霸试验仪器并不是“一如既往”地建立在美国,而是在欧洲。二战时大量欧洲科学家投奔美国,战后长达几十年的冷战和军备竞赛,美国在国际科技研究占据着绝对领导位置。
二戰期间,瑞士长大的爱因斯坦出走美国并在普林斯顿大学领导高等研究院,开创了世界一流大学研究院的典范;上世纪60年代,英国著名科学家波尔赴美进行科学研究并最终获得诺贝尔奖;直至近几年,欧裔美籍的诺贝尔获奖者并不鲜见。美国在科学世界中以其一流的科研环境,丰厚的财政资助,优越的福利制度不断吸引大量欧洲科学天才,并在美欧科学角力中始终处于上风。因此,这个人类历史上投入最大的科学实验由欧洲人牵头确实耐人寻味。
不过,LHC的成功启动真的标志着欧洲科学力量的复苏吗?欧盟能否借着这个历史性的科研事件重新夺回它们失落百年的科学皇冠?
从科技投入和成果来看,欧洲的实力依然大大落后于美国。2003年,经合组织(OECD)的一份统计报告指出,美国在科研(R&D)方面的总投入达到了2700亿美元,而欧盟仅为1870亿美元。在另一个极具说服力的指标——诺贝尔奖获奖人数的统计中,欧洲也是处于绝对劣势:欧洲在物理、化学和医学生理三个大项的总获奖人数仅占美国的一半,必须指出的是,欧洲有很大比例的获奖者是在二战前获得诺贝尔奖的。
正如上述指标显示,欧盟的科技投入大大落后于美国,是欧盟在科研中落后的根本原因。另外,欧盟毕竟是一个国家间的联盟而不是统一的国家,语言、文化的差异,教育制度不协调等因素决定了它在科技交流方面的先天不足。同时,不同利益驱动之下,各国科研的重点不同,很难做到人力物力的大规模集合。这种政治上的差异无疑是欧盟国家进行科研活动的又一短板。
然而LHC为何花落欧盟?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提一下LHC的主要制造者——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该中心汇集了3000多名科研人员,预算高达11亿瑞士法郎,每年接待1000多名世界各地的学者进行访问研究。这个诞生于二战后的大型科学机构已成为世界上所有粒子物理学家的精神圣地。开放性是其最大特色。以LHC的建造为例,参与该项目的科学家高达8970名,来自数十个国家,其中包括了欧洲以外的美国、以色列、日本等地。
一贯保守封闭的欧洲科学界在LHC计划上显示了极大的宽容性和开放性,项目不仅容纳了全球的科学家,并吸引了各国的经济投入,其中仅美国一个国家的投入就达到了5.9亿美元。也正因如此,欧盟的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获得全球粒子物理界的极大关注,在科研的推进和经济投入上也是罕见的顺利。
反观美国,其进行大规模物理实验的决心和机制却远不如欧洲先进和有效。美国物理学家们曾于80年代着手组织他们的大规模实验——超导超级对撞机(SSN)实验。但这个始于1982年的计划却最终胎死腹中。1993年初,美国国家审计署发表了一份对SSN极为不利的审计报告,该报告指出SSN的资金投入过大,挤占美国科研经费。这份报告随后被提交到国会,多个国会议员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停止对SSN项目的资助,平衡在各领域科研经费的投入,最终,停止SSN项目的议案获得通过。SSN的终止标志着美国大规模物理实验时代的结束,可以说是对美国粒子物理界的沉重打击,并决定了美国在大规模实验中必将落后于欧洲。有科学家指出,SSN项目中,美国一方面希望得到其他国家的投入,但另一方面却限制各国科研人员参与项目,防止其他国家分享这一重要的科学成果,最终结果是,其他国家对项目缺乏兴趣。在投入巨资的科研项目上缺乏他国支持,显然是行不通的。
可以说,SSN的失败和LCH的成功,与其说是欧美科技能力的体现,还不如说是其科研制度的反映。
虽然从各方面说,欧盟的科研能力仍较大地落后于美国。但欧盟在科学研究上却不甘心就此被美国抛开,其决心在LCH的推动上可见一斑。2007年7月1日,第七期欧洲研究与发展框架计划(EU R&D Framework Programme 7,简称FP7)正式启动,该计划致力于“建立共同的、成员国协调的欧洲研究与发展基地;统筹欧洲内部统一研究市场以使知识、研究者和技术在欧盟内自由流动;重组欧洲研究机构以欧盟层面和国家间研究活动的协调;制定欧盟共同研究政策”。由此可见,欧盟已经意识到其在科研合作方面的缺陷并矢志改革。
媒体角色在哪里?
有人担心撞击实验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或制造出小型黑洞吞噬地球,或产生出理论中的奇异微子,令地球异变,由此世界末日论的传言四起。在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前核安全专家沃尔特·瓦格纳和西班牙科学作家路易·桑奇联合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中止具有潜在威胁的强子对撞机试验。同时,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庭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法院同意审议主要由德国和奥地利教授和学生提出的强子对撞机可能导致世界末日来临一案。不过,法庭拒绝了他们提出的立即中止大型强子对撞机实验的请求。
在实验的安全性问题上,CERN得到了包括英国的斯蒂芬·霍金在内的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支持。这些科学家帮助消除了人们的担心,并宣称有关实验是绝对安全的。霍金说:“如果LHC中的粒子对撞制造出了一个微型黑洞——当然这是不太可能出现的,这个黑洞也会消散殆尽,产生独特的粒子模式。在地球大气层中,像这样的或更大能量级别的对撞每天要发生数百万次,也没有造成任何恶果。”
对LHC的安全评估自有相关专家来操心,但公众对此保留知情权。对于与自身安全相关的科学实验,公众知情权的行使尤为重要。
当媒体着重关注一些怀疑论者有关地球爆炸的预言、以科幻小说手法编织出一个个黑色梦魇时,对“世界末日”的恐惧便在民众中迅速蔓延。
在宗教传统根深蒂固的印度,对LHC试验以及相关威胁的恐惧通过媒体迅速传播,成千上万的人涌进寺庙祈祷。人们迫不及待地去享用最喜欢的食物,等待世界末日的到来。一位寺庙住持表示:“这几天日均比平常多了1000名香客。”而一名印度少女的自杀将恐惧情绪推向极端。女孩的父亲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称,女儿查雅观看关于世界末日的新闻节目后自杀。过去两天,印度不少新闻频道一直播放讨论欧洲强子对撞机实验以及世界末日预言的节目。
“舆论会对社会事物的关注表现出积极主动的态势,从而影响乃至左右大众的心理判断。”与其说查雅是死在对LHC的盲目恐惧中,不如说她是死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上。
当我们习惯将“媒体”与“告知”画等号时,不自觉地忽略了其对话功能。无论理性与否,公众以死亡的极致方式拒绝接受科学实验,难道没有其他途径吗?对于造价高昂、又具有潜在威胁(即使只是在假设上)的科学实验,公众难道不具有话语权吗?如果有,话语权向谁行使?
媒体是一个平台,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各阶层都能利用该平台进行理性对话。科学话题也不具有特殊性,由纳税人供养的科学不只是为了满足部分科学家的好奇心,它早已不是少数人手中的垄断资源。有识之士认为,以媒体为沟通桥梁,具备基本科学知识以及信息识别能力的公众,应理性行使质疑科学的权力。
中国究竟走了多远?
在大型强子对撞机(LHC)上的4个大实验中,共有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多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参与。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研人员参加了部分实验。
LHC计算网格分三层:第零层、第一层、第二层。第零层代表了CERN的中心设备,这里将把实验产生的原始数据进行存储和初步处理。第一层代表了国家级实验室,美国的费米实验室、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位列其中。在这里将进行大规模的计算和数据处理。第二层主要由大学和研究所的小型计算中心构成。这些中心的计算机将为整个网格上的数据分析提供分布式处理功能。高层组织有使用第零层和第一层工具的优先权。每个国家依据投入建设LHC项目的资金比重,获得一定级别的分享数据待遇。目前,中国各大实验室只能作为第二层计算中心,而日本则获得了第一层计算中心的资格。
LHC项目是我国政府首次投资参与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有无数个“第一”、“之最”值得鼓舞。尽管单凭一台超级粒子对撞机就断言中国在科研实力上跻身一流似乎有失偏颇。但是,中国的LCH参与,也至少说明我们在这条科研道路上的起步还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