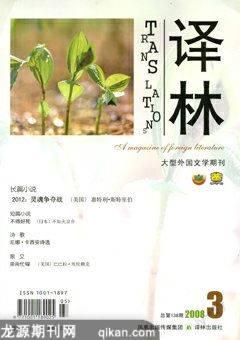一绺头发
[俄罗斯]米哈依尔·波波夫 著 马伯健/译
我们学会了烤肉串。在五块立方形的大而鲜美的猪肉上浇上番茄沙司,撒上青葱盐渍番茄,外加一块面包,这就全齐了?当然,还应该再来瓶啤酒!于是我拿了一瓶“克林斯基”。
春天。地铁边的集市。太阳。天很蓝,云彩甘心情愿地反映在脏水洼里。在商场里“营长”正声音嘶哑地在说话。
太好了!
一只脏兮兮的狗小心翼翼地嗅着我的膝盖。它瞅了我一眼。不,亲爱的,这一切都是主人的,无论是肉啊,还是啤酒啊,都没你的份。
我拿起一把易碎的塑料叉子,对得到的第一块肉感到满足,并用鼻子深吸了一口它的气味。突然一个影子落到我的桌子上。我瞥了一眼——是两个警察,带着自动步枪,脸色很阴沉。
“我们一起喝吧?”
“行,我想吃一点……”
“证件。”
我用手掌拍拍口袋,尽管明知道我随身什么证件也没有带。要知道我是出来买土豆的,不是出国旅行。
“走吧!”
争论是无济于事的。如果你在法律面前没有过错,那你在警察面前就一定有过错。何况那是两个荷枪实弹的小伙子。可我仍然试图寻找有利于我留下来喝自己啤酒的理由。一支破旧的自动枪的枪管迅速地顶在我的肋骨上,很痛。
“别耽搁了!”
可我并没有耽搁。我的目光中一定对自己的肉串流露出深深的遗憾,所以,为了不让那肉串继续折磨我,其中一个警察,比较和气的那位,没有用枪顶着我,他把肉推到了桌子底下。刚才的那只狗,它一点也不惊奇这命运带来的礼物,开始舔起猪肉上的番茄沙司来。
我被关在颠簸的“乌列斯”车上带走了。当我们经过十分熟悉的朝着警察局的那个转弯处时,在我那愤愤不平的深深困惑里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我明白,事情变得比我原先能够推测的还要糟糕。我靠在有格栅的小窗上,“乌列斯”朝市中心方向颠簸着前进。就是这么回事。我神经质地朝那位可怕的警察转过身来,就在我打算张口的那一瞬间,我的嘴被一个职业性的动作用胶带封住了,此外,双手“喀嚓”一声被铐上了手铐。
当然,我颤抖起来,使劲地用鼻音说话,气愤地瞪大了眼睛。我想说,这是个错误,这是个可怕的错误!我的脑袋被不知什么很重的东西撞了一下:车臣!亲爱的妈妈!事情竟然是这样!他们化装成警察,竟然在莫斯科直接抓捕!可我毕竟不是银行家,不是将军。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勤快人而已。除了住所,从我那儿还能得到什么呢?再说那也是以我岳母的名义登记的。当然,还有0.06公顷的萨拉尤什卡别墅,再也没有什么了。他们也许会强迫瓦莉娅卖掉住宅,可她还带着两个小孩子……我狂怒地一拉,但我觉得这么做是白费劲,我被捕鼠夹子一般的手揪住了。
“乌列斯”出了环城花园向库尔斯克火车站驶去。我心情沮丧,在冰冷的地上哆嗦起来。火车站?那就是说,确实是——车臣!现在我被塞进箱子里,撂在一边,在格罗兹尼过了一夜,接着是山,大羊群……也许,就这样付出一生。要知道瓦尔卡一定会拒绝出卖住宅的。她甚至也许会为摆脱我——一个傻瓜——而感到高兴。
我们没有到库尔斯克火车站广场,我们拐弯到了一条巷子。
一切准确无误。他们可没有拉着那个被封住嘴的人直接走过火车站大楼,他们把他带到后面的某个入口处……天哪!可为什么?!我们这儿各种各样的人都带着很多钱。他们该弄明白,我可不是这种车臣人的敌人,当这些谢马什卡的人在轰炸的时候,我甚至还在心里轻轻地谴责呢。
我们停下来了,正当我在半明半暗的门口推测时,门刹那间被打开了,在那些面色阴沉的警察的目光之下,我好像轻飘飘地跑向了那里。接着我们继续乘电梯往上,这使我产生了对车臣最初的猜疑。之后,我们来到一个稍稍被照亮的楼梯间,两扇没有号码的铁门像是不经意地开着。这不,我已经到了豪华的前厅。这样的居住条件我只有在电视节目《没戴领带的今日英雄》里看到过。
我还来不及好好看一下,一个穿着运动服的秃头大胖子从左面不知什么地方朝我走来。年岁大一点的那个警察向他报告说人已被带到。胖子打开了前厅里的附加灯,他用很长时间撕开我嘴上的胶带,顺带还扯掉了我上唇上的细毛。眼泪不由自主地从我的眼睛里流了下来。胖子低声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并用两个手指稍稍抬起了我的下巴,接着后退一步,低下头眯缝起眼睛。他的每个一个动作都伴随着轻轻的赞叹声“很好,很好!”他吩咐警察把我转到侧面,在最后一次发出的赞叹声后他大声命令道:
“洗澡去!”
我被沿着走廊扭送到这所住宅的深处。我来到四周全是黑色大理石的浴室。浴缸很大,是三角形的,有镀金的龙头。浴缸里水浪正翻动着,一个个浪峰在颤动。我来不及看清楚任何东西,就被很快地脱下了衣服。这时我完全放心了。在出发到车臣前我没有洗过澡。我觉得内衣穿得有点不舒服。说真的,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换过了。我依然不明白,他们究竟要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我来不及说话,我的头就已被泡在水里了。他们洗得很用心,但洗得也很快。他们没有从我手上解下手铐。
他们用一块长绒毛大毛巾擦干我的身子,给我穿上了一件香喷喷的长袍。
“去理发!”胖子接着发出新的命令。
过了几秒钟我已经坐在皮椅上了,面前有一面宽大的镜子和一张桌子,桌子上摆放着色彩鲜艳的瓶瓶罐罐。镜子里出现了一个穿着工作衣,神情阴沉的男人,他把浆硬的布巾系在我颈前,拿起了危险的剃刀。我试图站起来解释一番,但这是徒劳。我依旧被他们牢牢地按住。
胖子向拿着剃刀的人出示了一张照片。
“这些络腮胡子,让它们见鬼去吧。”
刀刃欢快地在阴沉男人的指间闪了一下。
“听我说,”我被夹住吱了一声,又不做声了。我想说,我专门蓄了这长鬓发,我觉得这漂亮。即便是我有错,这也不是用磨快的剃刀对待我的理由。可关于这一点我什么也没有说。我怀疑,谁也不会在意我的话。
事情并不局限于剃胡子的事。我被“抬起”了后脑勺,他们扩大了我的秃顶,弄了一绺鬈发。特别是这一绺卷发有好多麻烦事。胖子好几次认为这位理发师的活不行。最后的收场是在右脸颊上的一颗痣。胖子专心致志地打量了我一番。他显得如此满意,以致吩咐解下我的手铐。这时我甚至没想去按摩一下我的腕骨,只惦念着我的新发型。
“别碰!”胖子尖叫了一声,由于愤怒,他的脸色变得苍白。接着他变得温和些说,“我请您别动这个。”“一绺鬈发——这是最重要的。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除了明白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想在我聪明的回答中得到有关我命运的哪怕一点点信息。可我什么也来不及问,就传来了下面的命令。
“走吧!”
理发室后面是厨房。这厨房像这住宅里的一切那么豪华。其中一个警察从桌子上拿起一瓶刚刚打开的外国白兰地,往方形的水晶玻璃杯里倒了一百五十克左右。
“喝吧。”
我心里想说,这种器皿里的白兰地人们是不喝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掩盖自己的想法要比披露出来要好。我把这沉甸甸的杯子拿在手里,我突然怀疑——这是毒药!不知是哪一个行为反常的人,订做了一个被洗得干净,做过发型的人的尸体。而这尸体正好还处于轻微的酒醉状态。
“喝吧,这是‘库尔武阿兹耶,当你还有品尝机会的时候。”
无论怎么觉得奇怪,我还是相信了对方的话。我两口喝下了这些白兰地,胖子又抬起我的脸来,打量着。
“还有一百克。”检查之后,他吩咐带酒的警察。
我又喝了一百克。不过这以后我的外貌变成了他们规定的模样。随后我们就出发了。我很想知道去哪儿。原来我们是来到了一个有着宽大床的房间。窗子上挂着窗帘,软软的地毯,墙上挂着两幅画,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不,这不是所有的东西。天花板上还有非常明亮的枝形吊灯。在卧室里为什么装吊灯呢?整个五只两百瓦的灯泡都在发着光。
“请脱下衣服。”
“为什么?”
“请脱下衣服。躺到床上去,什么都不要感到惊奇。”
“你们要对我做什么?”
“您会喜欢的。”
然而,我继续用手捂着自己身上的那件别人长袍的前襟。
“这一切将会很好,甚至比您想像的还好……”胖子唠叨着。在他们说话时,一支自动步枪的枪管伸了过来,顶在我的脊梁骨上。我一切明白了。
我扔下长袍,顺着丝绸罩单爬到了床的那一头。
“不要睡在被子下,不要。就睡在上面,不要碰那绺头发。不要碰,我求您。”
他们走了。我仍然侧身躺着,按照电影里宫女的某种样式半弯着左腿。我老是在想不知把自己那双有裂缝的肮脏袜后跟藏到哪儿。尽管拼命地擦洗,它们还保留着一部分原有的污垢。
不过,最使我不满的并不是羞愧,一连串的问题压倒了这种不满:我在哪里?为什么是我?我将发生什么事?怎么办?等等。可不久我就向它们屈服了。通向卧室的门被打开了。两个姑娘轻盈地走进了房间。她们很漂亮。穿得怪怪的,她们梳着复杂的发型,穿着半透明的衣衫。我用手指稍稍遮住了我那可怜的害羞处,开始慢慢地拉动前面提到的那双袜后跟放到自己身体下。
姑娘们笑了起来。她们像天使一般,静悄悄地迈着步向床靠近。一个靠近床的右侧,另一个靠近左侧。我辗转不安地看着她们。左边的那个以习惯性的动作脱掉了衣衫,说:
“我叫娜斯佳。”
另一个同样作了介绍,她宣称自己叫“达莎”。
“瓦莉娅,亲爱的,我亲爱的妻子。瓦莉娅。”瞬间我不由地想起,“仿佛我现在要背叛你。没有任何反抗的可能性。我一个人,可他们有三个。娜斯佳、达莎和白兰地。”
我不是处在车臣人的山上,而是突然落到天堂般无限幸福的顶峰。一切都忘了——家、妻子、女儿、袜后跟。只有这一绺头发,只有这一绺令人惊奇的头发我得珍惜。我两手交叉着,两脚交叉着。娜斯佳和达莎创造了女性的带有很多躯体知识的小小奇迹。回忆这持续了多久是无益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如何结束的。
很突然!
像是按照命令!
姑娘起身,穿上衣服,没有告别,就消失了!
我似乎觉得,我失明了。不过稍稍冷静下来之后,我明白这不是失明。这不过是枝形吊灯五个灯泡中的四个熄灭了。
门又被打开了。可这次不是娜斯佳跟达莎,而是一个秃头带着一团我的衣服。
“全在这儿,亲爱的。全在这儿,可以穿衣服了。”
我费了好大劲走到床边,把自己那双不幸的袜后跟放在地毯上。
“快点,快点,朋友,明白吗,时间不等人。”
我穿上了裤衩、裤子,把脚伸进皮鞋之后,依然拽着由于惊吓被汗水湿透的衬衫的扣子,走出了卧室。
在厨房里一杯白兰地和一只信封在等着我。
“这儿是三百元。”胖子说。
“美元?”
“是卢布,亲爱的,卢布。这些姑娘将得到美元。”
我拿了卢布。
“现在关于不泄漏的字据就在这儿。但愿您不要泄漏这儿发生的事。人们反正不会相信您,可我们会知道。您签字了?好极了,喝一杯白兰地吧。比如,您要考虑,您的夫人了解这一切后会说什么。”
“你们给我照了相?”
“我们照了相,照了相。”这个浑蛋说得很亲热。
“可这是为什么?恫吓我,还是怎么着,要知道我……”
“无论是谁。我们非常了解这一点,我们觉得这合适。”
“那你们是谁?”
胖子皱了皱眉头,警察旋即抓住了我的手,强扭着向门口走去。我已经站在铁门边,叫了一声。
“那一绺头发?”
“什么一绺头发?啊——一绺头发,天哪!”胖子很快跑到我跟前,从后面口袋里抽出剪刀。咔嚓,于是我便没有一绺头发了。
这不,我重新出现在大街上。太阳依然明亮地照耀着。由于白兰地我体内暖洋洋的,可脑袋很清醒。
见鬼去吧!竟有这样的事情。我很想知道的是,我将对瓦莉娅说什么?但愿不要忘记顺路去买土豆就好。希望她认为,我只是喝醉了。
过了差不多六个月。
我在厨房里剥土豆皮。自然不是我那次买的。瓦莉娅在电视机旁编织,突然我听到一声喊叫。
“瓦西里,过来,快,你这个傻瓜!”
我跑了进去。
“你看,你看,多像你这个傻瓜!”
“谁?”
“就是这个新上任的副总理。刚刚被任命的。”
她用织针指着荧屏。
“一模一样,你跟他一模一样。不过,他有一绺卷起来的头发,而你没有。”
“这个人不会撑很久的。”我阴郁地说。
“你有什么根据说这一点,你,我的聪明人?”夫人挖苦地问。
“我怎么会知道。”
“也许,你要给我讲讲?”
“啊,不,不值得,反正你不信。”
———“人民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