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故事:一个传统藏族家庭的60年变迁
杨时旸


发生在这个春天的拉萨暴力事件让西藏在短时间内又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在西藏近百年的历史上,这样的境遇着实不少。
我们一直关注西藏,是因为那个地方的疼就是我们的疼,那个地方的怒就是我们的怒。西藏与我们,不可分离。
藏民族是离太阳最近的民族,诡秘绮丽,但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她又显得遥远。
“我们对于西藏的理解,就像外国人对于中国的理解。”学者廉湘民对西藏长期以来所遭受的误解有如此感慨。这样的误解,在藏学者看来,主要源于视角上的偏差。如何消解这种偏差,注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这一次,我们又努力使自己离西藏更近,直至让自己像显微镜一样深入她最深层的肌体——我们尝试通过记录一个传统藏族家庭半个多世纪的变化,力图给读者提供一个观察西藏社会的视角。
一个开放的民族,不会拒斥现代化;西藏百年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尝试现代化的故事。
这个生动的故事里,有艰辛,有奋斗,更不缺欢愉。
阿里,被誉为“西藏的西藏”“离太阳最近的地方”。
这个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严重高寒缺氧的地方与中国其他地域一样正在进行着自己的蜕变。
狮泉河,阿里地区首府所在地,常住人口一万多,有着这样规模的城市应该有的所有设施。人们上班上学,节奏缓慢,扎着鲜艳红色头巾的进城务工牧民,不时在街头走过,一切大致与内地城市无异。

而在两个多小时车程以外的阿里牧区,牧民们仍需直面严酷的自然环境,居住在祖辈留下的黑帐篷中,以放牧为生。
在这里,有九个兄弟姐妹成了牧区的传奇——因为命运和自身际遇,兄弟姐妹中有的已经成为知名学者、成功商人,或者政府高级干部,有的仍然留在牧区,继承家业,与牛羊为伴。
这个传统藏族家庭半个多世纪的演变,可以作为我们观察西藏社会直面现代化具体而微小的切片。
“红汉人来了”
1959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在阿里穷人的心里只是留下了两个简单的印记——“无法继续祖辈的生意”和“来了一群讲道理的红汉人。”
次仁加布,西藏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所长。
2008年4月15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北京见到他时,他正要飞往奥地利参加一个关于藏学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1961年,次仁加布出生在阿里地区噶尔县左左乡朗久村,从记事起便跟着姐姐牧羊,曾经的生活与现在相比,恍若隔世。
父亲强巴,母亲拉姆次仁。西藏和平解放之前,这对年轻的牧民夫妻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1994年,父亲因肝病去世;母亲在2006年也撒手人寰,享89岁高寿。
西藏民主改革之前,次仁的父亲一直给别人家里干活,放羊、搬家、找牛,“养活一家人”。有时,父亲强巴会对次仁的弟兄们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生活经历,儿子们瞪大双眼。“家里的帐篷谁都可以随便出入,父亲回家发现有人来过,如果是朝圣的人,他会非常高兴。”次仁加布说。
1959年,发生西藏叛乱,达赖喇嘛出逃,部队进驻西藏。
因为路途遥远消息闭塞,远在西北疆的阿里地区反应并不像拉萨那样剧烈。当部队快来到阿里时,一个传言开始在草原上散播:“红汉人要来了!”
所谓“红汉人”是当地牧民对于红军和汉人的混合想象。想象在传播中变形,“牧民竟然听说‘红汉人是要吃富人的肉”。后来人们又都知晓共产党是要“共富人的产”,于是拉萨叛乱后不久,阿里地区的富人几乎全部外逃印度。
“当时边境意识不强。”次仁加布说。原本有着50多户的乡村这时只剩下30多户。
富人走后,留在当地的穷人也有些害怕。祖辈很多都曾与印度有原始形态的盐粮和畜产品生意往来,因为有着几辈人的传承和固定的生意对象,有时一笔生意的钱款可以等到来年对方宽余的时候再付账。而1959年始,因为严格的边境概念,对父亲强巴来说,世世代代做生意的朋友永久失去了联系,曾经欠下的账再也无法返还。
在次仁加布的记忆里,父亲经常念叨的是,“哎哟,我那边(指印度)的朋友怎么样。我还不了别人啦,我吃了别人东西的啊。”
部队的帐篷就驻扎在牧区附近,因为传说中“红汉人坏得很”,没有女人敢靠近。有一次,父亲因为接活,到部队驻地附近去了一次。回到家就说,“那些人好得很,讲道理。”
1959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在阿里藏族穷人的心里只是留下了两个简单的印记——“无法继续祖辈的生意”和“来了一群讲道理的红汉人。”
阿里的“文革”岁月
“文革”彻底改变了这一切。据次仁加布回忆,到目前为止,整个郎久只出过一个僧人,且已还俗。
“西藏叛乱”之后,1951年签署的“十七条协议”实际被终止。后来,大量庙宇被关闭,传说西藏政权被废除,上层贵族的财产也被没收,西藏的政权重新建立。

发生在拉萨的这一切传导到遥远的阿里,又慢了几拍:
1966年之前,次仁加布家里的牛羊仍然归己所有,只是成立了互助组,“工作在一起干”。这是人民公社的前奏。在这之后,一些被称为“工作组”的干部出现在这片曾经人烟稀少的牧区。
“工作组”多是乡里或者县里来的汉族干部,也有从拉萨来的藏族干部,主要是陪同翻译。“工作组”组织牧民“提高思想觉悟”,干部们还出钱从富裕一些的牧民家里买来羊和牛分给那些没有牛羊的人家。
那时,次仁加布开始帮助家人放羊。他的大姐,18岁但没有上过学的多吉卓玛,其中一个身份是乡里7个共青团员之一,这时也因“各方面要求进步”,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这位年轻的会计不会算术,“记账只能用小石头”。
而大哥,在1965年,通过招工来到城里——这是这个藏族家庭第一个走出牧区的人。
1959年到文革发生前的那段日子,次仁加布每天早出晚归,放羊,或者向二姐学习藏语,“夏天在沙地上划,冬天在雪地上写,指头都是红红的”。
日子就在写字的指间偷偷流逝。直到有一天,一直供奉在帐篷最前面的一卷经书被父亲偷偷拿走,那是次仁的“自学材料”。祖传的“自学材料”被父亲藏到了嘛呢石堆,后来下落不明。
“那是一卷类似于佛教全集的经书,还包括地方历史和家族历史。”次仁加布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后来次仁加布才知道,“文革”来临了。
在当时的次仁看来,“文革”只意味着他的一个稍微富有的舅舅被批斗。“我就知道连小孩都可以踢他,可以骂他,心里很不舒服。”次仁加布说。
因为牧民居住大多分散,所以很少能组织起像内地一样的批斗大会。政治学习会议上时而会有批斗场面出现,次仁的姐姐回家时告诉家人,“舅舅的牙齿和头发都被打掉了。”
这个时候,大姐多吉卓玛带领牧民学习文件,告诉牧民“这么多年吃不饱穿不暖,是由于寺庙里的僧人和牧主的压迫造成的”。

“穷人们都懂这个道理。”2008年4月25日,已经六十岁的多吉卓玛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我自己也斗过牧主。年轻人和穷人都支持斗牧主。”
1969年,次仁加布世代居住的牧区更名为“红旗公社”,曾经属于自己的牛羊都化归集体所有。如果羊丢了,年底要扣工分。
次仁家分到了600多只羊,但是“没有肉吃,也不能杀”。这600只羊“放得好”,每人一天可以记10个工分,年底按照工分分配下一年的肉食、奶渣和酥油,生活上“凑凑合合能吃饱”。
不满十岁的次仁加布搞不清楚这一切的真实含义。他照旧过着自己的生活,放羊的时候仍旧偷偷拿着家里传下的经书坐在草场上看。其时,这些书已被视为批判革除的对象。
次仁加布忍受不了亲情割离。
研究生毕业,应导师的要求在北京工作四年之后,他回到拉萨。
旺扎“下海”
旺扎如今已经是成功的商人,他说如果不是前年做了个大手术,元气大伤,他“还想有点变化”。
1992年,内地经商大潮风起云涌。
虽然家人都安于现状,但旺扎“还是想改变一些什么”。
邮电局投资30万办了一个小企业,这个“通讯发展公司”5年赔掉了25万。旺扎提出要承包。利用剩余的5万元,一个七八十平米的门面房和一辆半旧的东风卡车作为启动资金,和邮电局签定协议,“承包三年,返还25万现金,每年上缴邮电局10万”。
“日用百货,什么挣钱我就做什么。”旺扎说。承包六年,他挣了300万元。
邮电局决定收回公司再投资300万扩大规模,并邀请旺扎做总经理。旺扎却谢绝了,“算我傻,我不干了”。
旺扎的逻辑是,“我从安多买一车酥油,有的十块一桶有的六七块,我一路卖,到阿里可能就已经卖完了,从收购到卖的程序谁也说不清楚。但是给公家干,一车酥油必须得拉到阿里,入库,再拉出去卖,这样成本大大增加,根本赚不了钱。”旺扎说,“到时候审计来一下就够你吃一壶。我得考虑后果。”
领导赏识他的能力,又把他调回单位继续从前的工作。
一段时间后,邻县一家邮电局局长挪用汇兑款,稽查组想抽调一名年轻人接任,看中了旺扎。口头承诺,到邻县锻炼一段时间,回阿里地区后可直接升任地区副局长。旺扎却要求领导给出书面保证,却不想因此开罪了上司。
升迁道路已断,旺扎又提出辞职。他决定开家公司,但母亲不同意,觉得他“翅膀硬了,不管公家了”。
狮泉河粮食公司很不景气,总经理找到旺扎,给他一个副经理的位置,“一起把粮食公司搞起来”。1997年,旺扎从邮电局辞职的时候,月薪4600元,而粮食公司的薪水只有800块。
两年之后,当地烟草公司濒临破产,行署领导觉得旺扎是个经营人才,调他到烟草公司做主管烟草的经理。2003年,旺扎又得到了阿里烟草专卖局局长和烟草公司总经理这“两个名分”,一直到现在。如今烟草公司年收入已经达到一个亿。
旺扎已是成功的商人,他说如果不是前年做了个大手术,元气大伤,他“还想有些变化”。
那次手术之后,旺扎觉得自己应该多关注一下家庭。
“特别是帮助一下还留在牧区的弟弟。”
东旦的2008
“他常跟我说,要是没有他,我就是最小的,我就得留在家里照顾牛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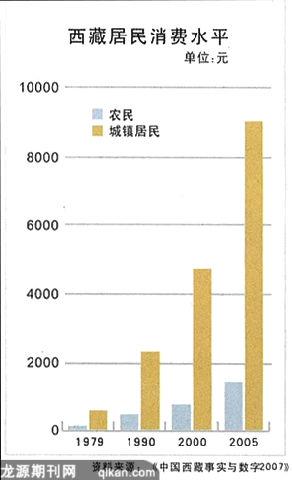
和狮泉河的繁华相比,阿里牧区显得遥远而荒凉。
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只有越野车才能通过,到达一座海拔五千多米的山后,车辆就不能进入,只能步行。爬过一座几百米的荒山,就能看到一顶黑色的帐篷扎在山窝间。
这个用牦牛毛织成的黑帐篷是旺扎一家小时候用过的,从帐篷里可以透过网眼看到天空。弟弟东旦今年40岁,但是看起来比旺扎还要老上很多。他的妻子和大女儿都在家里放羊,小女儿曲卓玛今年19岁。
曲卓玛从5岁起就被旺扎接到狮泉河上学,一直读到中专,住在伯伯家里,现在伯伯旺扎的烟草公司做业务员。
“我小时候上不了学,我姐姐哥哥都上了,小时候要是都上了就没人放羊了,但我愿意上学。”东旦不停地倒着酥油茶,他只能用藏语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交流。
“我家里有30头牛,山羊绵羊加起来280头,算中等吧。生活来源就是靠羊和牛,这些肉可以到卖到狮泉河去。这儿长不了青稞,生活上哥哥姐姐会帮帮忙,否则会有点困难。”如今的牧区,草场都已划分给各家所有,东旦家分到大约两三平方公里。
从今年3月起,这个牧区的大多数年轻男人都到狮泉河和牧区中间的一个乡去打工,当地政府在那里投资600万种植青稞,这些男人负责搬运石头和平整土地,每天可以挣40~50元,“可以干到6月份”。
“他有时候常跟我说,要是没有他,我就是最小的,我就得留在家里照顾牛羊了。”旺扎说。

在阿里牧区,一头牦牛可以卖到1000元,一只羊可以卖到250元,但即使这样,也要赶上好的年景,当地雪灾风灾连年不断,一场大灾可以导致牛羊死掉一半。最好的年景里,一个家庭可以挣到几万元,但这样的时候很少,最差的时候,一年收入不足一万。
东旦的帐篷里仍然放着父母留下的酥油茶壶和一些小小的银器,门外的羊圈里,十只刚出生的小羊羔不停地叫唤。东旦点了根烟,说,“我明年准备再去要点钱,把门口的路修一修,这路太难走。”
去年,东旦到狮泉河各部门要了大约5万块,平整了一段路,他计划明年“再要8万”。旺扎说,这些钱都是东旦自己要到的,他没有帮忙,今年如果可以要到6万,他的烟草公司准备赞助2万。
旺扎的二姐次仁卓玛,也仍然生活在牧区,离小弟弟东旦的帐篷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二姐的生活更加艰难,帐篷是用布匹制成,坐垫边上立着两只风干的羊,颜色血红。
帐篷顶端有一台录音机,可以用太阳能电池开启,有一个包裹得很严密的经卷,是老人婆家祖传的信物。次仁卓玛今年58岁,从14岁起就嫁到这儿,据说自学过藏文。
长期封闭的放牧生活,老人已经很难与外界人接触,终日与一只已经20多岁的老藏獒为伴,“只知道倒茶微笑”。次仁卓玛的大儿子仍然在牧区放牧,已经分家另过,小儿子在狮泉河的一家银行工作。
她家有1200多只羊,很少出售,“够吃就不卖”。
在城里长大的第三代
到了牧区,小女儿不愿意下车,旺扎问为什么。女儿说,“脏得很。”旺扎被噎住了,“心里发酸”。
大哥洛桑已经去世,小时候因不慎掉进火堆,落下一点残疾,所以父亲一直教他读经,希望他以后能到寺院有个着落。
洛桑最终没能成为僧人,却因为自己的努力进城做了电工,终生未娶。1991年,弟弟次仁加布结婚那年,洛桑落寞过世。
大姐多吉卓玛如今已经60岁,曾经的“积极分子”如今已在噶尔县妇联副主任任上退休,退休金4000多元。
因为儿时家穷,三姐才旺卓玛被送到亲戚家寄养三年,后来因为“不喜欢他家”,又跑回自家的黑帐篷。她“学过一点算术”,曾经做到了当地一家农业银行的副行长,“想照顾家庭”于是辞去职务做普通柜员。得益于工龄长,才旺卓玛保持了以前的待遇,现在每月8000多元工资。
二哥索南平措已经调任拉萨成为西藏自治区工商联合会主席,从12岁离开家乡就一直在外,从政后一路顺风顺水,如今的职位属于正厅级。两个子女都已送到内地读书。他不愿作更多采访。
这一家9个兄弟姐妹,6人走出牧区成为“公家人”,在当地备受尊敬。

如今,阿里牧区的年轻人,更愿意上学或者外出打工。但是,往往初中毕业后,却无法考上高中,回到牧区又可能“难以适应放牧的生活方式”,这成为很多牧区父母头疼的事情。
去年,旺扎带着自己4岁的女儿回了一次牧区老家。到了牧区,小女儿不愿意下车,旺扎问为什么。女儿说,“脏得很。”旺扎被噎住了,“心里发酸”。
东旦的小女儿,在狮泉河生活了十几年的曲卓玛也很少回到牧区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她,“你喜欢牧区还是城里?”
她犹豫了一下,用磕磕绊绊的汉话说,“城里,城里。”
西藏记事
1949年十世班禅确吉坚赞在青海塔尔寺坐床,从青海致电毛泽东、朱德希望早日解放西藏。
1950年10月,昌都战役,一举歼灭阻挡西藏解放的藏军主力。西藏摄政达扎下台,十四世达赖亲政。
1955年3月,国务院决定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拉萨制造武装叛乱。十四世达赖随员出逃。6月,自治区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在全区实行民主改革。
1962年西藏各地工办和民办小学已达1500多所。中央批复西藏工委《关于农村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
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1966年“文革”开始。贡嘎机场建成通航。
1978年区党委发出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的指示。
1979年宽大处理1959年参叛人员。中央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西藏新时期的工作方针。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提出当前和今后要解决六件事。国家拨款50万修复甘丹寺。
1983年西藏农牧区普通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
1984年中央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有9省市帮助西藏建设43项中小型工程项目。
1985年内地19个省市为西藏办中学和初中班培养藏族人才。43项工程陆续建成交付使用。
1989年1月28日第十世班禅大师在扎什伦布寺圆寂。3月,西藏拉萨发生反革命骚乱,中央在拉萨实行戒严。这一年,西藏粮食总产达5.325亿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拉萨大规模改造、新建民居住宅。
1991年西藏和平解放40年,藏族干部迅速成长。全区共有藏族干部3.7万,占全区干部总数的66.6%。国家计委决定投资10亿元,在十年内分期对川藏公路进行整治改造。内地26个省市开办西藏中学和西藏班。
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上落实了西藏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的62项援建工程。国家投资5300万元维修布达拉宫工程,经过先后十年努力终于圆满竣工。
1995年5月,达赖喇嘛非法认定班禅转世灵童,遭到佛教界坚决抵制;11月29日,认定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金瓶掣签仪式在大昭寺举行,同日中央政府批准经金瓶掣签认定的坚赞诺布为第十一世班禅。
1996年国家拨款20亿元全面正式川藏公路;可可西里建立高原野生动物保护区。
2006年7月,青藏铁路建成通车,结束西藏没有铁路的历史。
2008年西藏拉萨发生“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