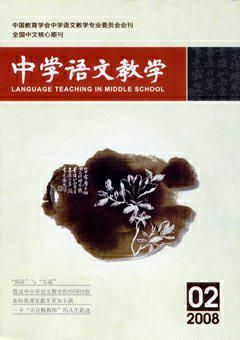课例沙龙
主持人:史老师,这辑课例我们确定了一个比较形象的话题——“如何使课堂教学更加丰满”,想听听您对此的看法。
史绍典:说一堂课“丰满”,指的是教学的充实与鲜活,这显然是个正面的比喻。
当然,强调“丰满”,并非意味着“丰满”就是教学的唯一追求。事实上,如果每堂课都丰满,一堂课的每个环节都丰满,则过于肥腴,反倒少了点意思。最好是有那么点空白(留有空间,引发玄想),“红肥绿瘦”,该瘦处则瘦,才是上上境界。
主持人:课堂教学的“丰满”有标准么?
史绍典:有的。标准大致有三:首先,有情境;其次,有过程;第三,能增值。
先说有情境。宗礼先生的实录在创设学习情境方面堪称典范。
情境一:巧用半截松木
学生没有见过“本体”(张迎善的手),洪宗礼老师就拿来“喻体”(半截老松木),由直观的“喻体”搭桥,学生在观察、描摹、感悟、对话的过程中,一双真真切切的张迎善的手呈现在他们的眼前了。
这样才有了对“半截老松木”的精彩解读,渐次抓住了以老松木喻手的主要特征:粗→老→硬→干→色深→厚。这样的教学是何等丰满!
我们该向洪老师学习,他没有刻意追求“丰满”,也不只是为了得出几个高度概括抽象的“手”的特征。他是反对那种“形而上”的不得要领的贴标签式的概括,他只是引领学生做“形而下”的体认,让学生用自己的眼去看,用自己的感官去感受那手是如何的“粗”,如何的“干”……这样的感受一定要比单纯的抽象概括丰富得多,细腻得多。
课例二也讲“一双手”。但做法却是让学生填空:“张迎善有一双________的手”,于是就有了“粗糙的手”“神奇的手”“创造绿色宝库的手”“绿化世界的手”“做出巨大贡献的手”……我以为这些关于“手”的概念,似乎使张迎善的手一下子“高、大、全”起来、“丰满”起来。但给人的感觉却太冷涩、太生硬、太干燥,又太崇高、太虚饰、太矫情。
张迎善到底有一双怎样的手?学生在“第一时间”里做了许多概括,但是,这些概括不但没有加深大家对这双手的印象,反倒使之更加玄虚、不真实起来。我们看到的是被概念化了的张迎善的手,而不是实实在在的张迎善的手。作者眼中的张迎善的手原本是那样具体、真实,但是在教师引导下,学生一下子就跳到概括层次上去,具体的“手”化为“概念”的手,失去了丰富的细节,如同生命失去了血肉,于是便毫无丰满可言。
当下流行的语文教学的“新套路”也大致如此:迅速浏览课文,再用一句话、一个词把意思概括出来。这一套路未必无益处,但如果将这种概括在一堂课中进行到底,则相当可怕。
与洪老师的课例相比,我们不难发现谁更能体现语文的特点,谁的课堂更加丰满厚实。
情境二:妙用一把尺子
讲张迎善的手“大”,作者用了长、宽、厚的一组数字,洪老师在引导学生体会运用数字的作用之后,设计了这样一个教学环节:用尺子量自己手的长、宽、厚,以与张迎善的“大”手作比较。这确实是神来之笔。
这个体味“大”的过程实在是巧妙,它把学生从惯常的概括之中拉回来,并让他们认识到简单的概括不是丰满,而是“太空洞”“太笼统”!只有具体、具象,才是丰满。为了体味一个“大”字的妙处,洪老师采取了方法,使得一个看来非常空泛的“大”字顿时鲜活生动起来。
情境三:咀嚼一个“裹”字
洪宗礼老师还让学生从“裹”字里体会张迎善的手大,那个片段实在太出色了。一个很俗气的“裹”,一个很平常的“紧紧”,竟可以让学生感受出这么丰富的内容。洪宗礼老师用的是从直观读出具象的方法;在读书的过程中,通过还原“裹”“紧紧”这些平凡词语的真实情境,使学生真切感受到了张迎善的手是如何的“大”!
这便是使课堂教学丰满起来的关键:从课文中拎出能够给学生留下印象的语句,然后想方设法引导学生体会这些词语所蕴涵的丰富的意义与情味,而不是那种泯灭印象的概括(这里隐含着通常所说的由过程走向结果的理念)。
主持人:其实,洪老师的这个实录片段的内容很少,只讲了两点:一是“半截老松木”,一是“大”;但我们却觉得非常充实,非常丰富。而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些课,老师洋洋洒洒涉及了许多内容,大家却觉得很空泛。
史绍典:确实如此。阅读教学在相当程度上需要体验,只有丰富充实的细节,才能够形成丰满充实的教学,而过度概括就损耗了体验所需要的丰富的情境因素。
再说有过程。
课堂教学要追求丰满充实,但不是说一上来就要丰满,“丰满”应该是一个渐次的过程。语文教学需要体验,与体验密不可分的就是过程,过程能够使作者所感受到的一切也为读者所体验到。过程,是使语文课丰满的要素。
语文课是要教学生读书方法的,要让学生学读书、会读书,最后形成读书的基本能力。那么,能力的形成,就离不开一个感受、体验、积累的过程。
一个能使感情、认识渐次生发的教学过程就是一个教学逐渐丰满的过程。
宜昌的李祖贵老师指导的《吆喝》课例与洪老师的方式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师:让我们来看看,哪一句吆喝,让你一听,就口水直流?
从一句吆喝,要听出“口水直流”,这一方面是说“吆喝”得好,另一方面是说对“吆喝”隐含的信息体味得好,更重要的,是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怎样从一句不经意的“吆喝”中,把这两方面的好都体会出来,而积淀为一种读书(认知)的方法和能力,即从直观中读出具象。
师生关于“吆喝”味道的对话,与其说是“听”得地道,不如说是“读”得地道、“品”得地道。跟洪宗礼老师相通的地方是,他让学生在“听”的过程中,“还原”着吆喝的原生态。“还原”后的吆喝,就是生活中活生生的灵动的“吆喝”了。
主持人:有了这样一个过程,教学就显得丰富、鲜活得多了。
史绍典:过程还有一个含义,就是教学环节。教学环节是外在的过程。《吆喝》实录教学环节也不少,但不嫌臃肿,因为这些环节都源自文章的内在肌理,而不是外加的硬贴的。如果因为作者写了北京的吆喝,教师也要求学生仿写一下湖北的呢?因此,教学的丰满不看环节多少,只看是否适宜。
最后,在注重过程之外,还要看结果,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有增值。
所谓增值,是指教学中思想碰撞后,“对话”的双方或多方都产生了新的收获,思想获得增值。教学的丰满,就是要使思想增值;但这种增值,绝不是外加与硬贴的。
比较两个“一双手”的教学案例,我们可以看到洪宗礼老师对学生的引导是从具体的美与丑导向对生活中美与丑的感悟的。洪老师没有局限在张迎善手的美与丑上,而是通过并结合张迎善手的具体的事例,指向对人生、对人生价值的严肃的思考,毫不拘泥、毫不牵强。如果只是平面地让学生“寻找”张迎善手丑的原因,继而概念化地夸饰张迎善手丑的崇高,就会使教学内容虚化,使得所谓的“美”成为一个标签、一顶帽子!
主持人:对,如果我们的教学只是让学生复述一遍在政治、历史教科书中学来的一些“高论”,而没有使学生依赖自己的体验、情感和思考真正地体会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们的教学便是干瘪的。最后,我们再看看《阿Q正传》这个片段吧。
史绍典:鲁迅笔下的阿Q,是个永远谈不尽的话题。
从解梦的角度读《阿Q正传》,吴老师确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三个问题的设计也有一些解读新意。不过,总的看还是一种大而化之的谈玄。
阿Q的悲剧是笃定的。师生谈阿Q,其实是站在“隔岸”的立场,“冷眼向洋”,做或是笑话或是严肃的评说,不过也都是些司空见惯的话语;而所谈论的对象,也就是一个完全与己无关的“物品”!
鲁迅先生对阿Q的情感不是这样的!
教师能引导学生设身处地地设想一下阿Q吗?他的境况、他的际遇、他的苦痛、他的希冀……教师应该让学生摆进去自己的父辈、祖辈、先祖辈,再摆进去他自己来谈谈阿Q!
这样,教学或许会增加许多新意。
主持人:可以结合上述几个课例谈谈您对当代及洪先生时代的语文教学的看法吗?
史绍典:这个话题太大,从几个课例无法比较两个时代教学的特点。但这种比较还是有意义的,举几个例子说说吧。
我有个总体感觉,当前的许多课总体上比洪先生的课漂亮多了,但是单薄了。或者说,当代许多课堂失之于花哨、肤浅。大致有如下几类现象。
第一,当前语文教学,尤其是所谓公开课、竞赛课,似乎有一个通用模式:以跟文本有某种粘连的文章来导题或作结题时的迁移拓展。
例如,教鲁迅先生的《雪》,教者以彭丽媛《我爱你,塞北的雪》VCD影音入题,以柳宗元《独钓寒江雪》、老舍《济南的冬天》、毛泽东《雪》结题。二者本毫无相同、相似、相近之处,只是在文题之中,都有“雪”而已。问题是,这样多的雪,与鲁迅的雪,到底有什么关联?鲁迅的《雪》,是对“孤独的雪”“死掉的雨”“雨的精灵”的礼赞!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雪,自有其独有的意蕴,岂能如此生拉硬扯!其实,并不是不能联系,不可比较,只是说,把这些关系不大的“雪”一股脑儿地抛给学生,鲁迅的《雪》处于何种位置?学生自己心目中的雪处于何种位置?学生自然而然地由鲁迅的雪到自我的雪到其他的雪处于何种位置?
这种所谓的联系、迁移、拓展,只是意在造成一种容量大、联系多、积累广的虚假“繁荣”,实则是教学的华而不实、哗众取宠,于文本自身的解读,是弊多利少。貌似丰满,实则干瘪。
第二,组织形式上的花哨。课堂上充满闹闹哄哄的分组讨论、填表……“读书”则被忽略了,文本解读被忽略了,“对话”被忽略了。
第三,学生也开始变得花哨。学生在这种氛围中也学会了一套方法:能够圆熟地运用一些早已根植于口头言表的时令语词,轻飘飘地置于任何“讨论”的场合。教师实际上努力“培养”学生的只是一种莫测高深的故作姿态和不切实际的媚俗话语。
相比之下,洪先生及其那个时代的许多老师的课就显得本色得多,古拙得多,却让人觉得丰满得多,厚实得多!
主持人:作为编者,我想强调一下,洪先生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之一,他的课例代表着他那个时代的高端水平;而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几个课例其执教者都是非常年轻的教师,其间确乎不太具备可比性。也许,这样的比较对这些老师而言过于苛刻了些。但我们确实希望,若干年后,这几位老师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王宗礼”“吴宗礼”呢!
史绍典:不错,语文教育的希望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