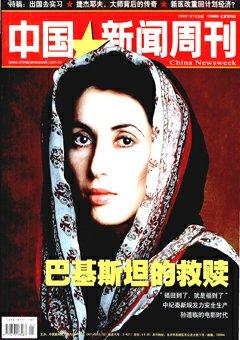三门峡移民的回归土地之路
韩 永
陕西三门峡库区移民的代表陈思忠、郗新继被华阴市公安局带走了。这天,正好是他们到北京上访,拿到国家信访局批复的第10天。
记者在华阴市华西镇孙庄村农民张纯芳那里,看到了这一批复,上写:“你们来访反映的事项,我们根据《信访条例》的有关规定,将转送陕西省政府办公厅处理。”时间为2007年11月24日。
12月16日,第三位农民代表张三民也被华阴市公安局带走了。
张纯芳,以及同时参与上访的渭南市的大荔县农民代表马连宝、李孝玉,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处理流程:批复从国家信访局批到省里,再从省里批到渭南市,然后由下属的华阴市和大荔县出面处理,处理的方式常常就是,出头的人像陈思忠、郗新继、张三民一样,被公安局带走。
而张三民被带走的那天,距离华阴市政府曾经承诺的与农民代表谈判的时间还有三天。
马连宝则在听到风声后迅速离家。李孝玉从暂时的“避风港”蒲城县赶来与其见面时,特意带了一瓶二锅头,为这位70岁的老人“压惊”。
国家信访局批复中所提“反映的事项”,是指国家明文规定划拨给农民、却被地方政府发包渔利的土地问题,背景则是一段陕西渭南农民随着三门峡水库的涨落而漂泊沉浮的历史。

艰辛返程
这段历史是以当时惯有的磅礴的气魄开场的。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初生的新中国处处洋溢着对快速发展的渴望,三门峡水库作为一个“大手笔”粉墨登场。1955年7月,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通过了《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将三门峡水库的库容面积设计为100万亩,其中80%的库区在陕西省渭南市所辖大荔、华阴、潼关三县(市)境内。
这是一次牵涉28万多人的大规模迁移,过程却顺利得出人意料。迁移在当时被当作一种资格受到追捧,第一批迁出人员无一例外都要经过严格的筛选,被选中的青壮年、党团员和贫下中农在“敲锣打鼓,披红戴花”的热烈气氛围中远赴宁夏陶乐等地。
但在50年代,陶乐等地自然条件的恶劣远超常人想象。很多移民后来向记者描述,他们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沙漠里几无生命的痕迹,“一觉醒来已是大漠封门”。在新开垦的荒地里撒下种子,永远也盼不来发芽的时刻,有放羊的孩子被狂风吹走后,就永远没有了消息。马连宝告诉记者,当时十八九岁的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四次搬家,“根本找不到一块立足之地”。
在生活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移民们的返乡潮此起彼伏。
国家被迫在1960年进行第二次迁移,将他们从宁夏迁往陕西渭北的蒲城、白水、澄城、合阳等地。虽离家乡近些,条件却好不了多少,旱塬沟壑,土壤缺肥,生活依然艰难,很多人靠卖血度日,特别是澄城县,“几家都看不到一个女人,”一位当年的移民张彦龙说。
此时,三门峡水库正在面临始料未及的巨大考验。由于前苏联专家领衔的设计团队对黄河的品性不甚了解,建成后的三门峡水库因泥沙的不断增多而使河床抬高,15亿吨泥沙铺在从三门峡大坝到陕西潼关270公里的河道中,在潼关的渭河、洛河入黄口形成5米高的拦门沙,造成洪灾频发,对关中的西安、咸阳、渭南等市形成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决定改变三门峡水库的利用模式,从“蓄水发电”转变为“径流发电”——来多少水发多少电,不再大规模蓄水。
蓄水的减少使库容大大压缩,原来被淹的大部分土地浮出水面。为了不使这些土地荒废,国家在1964年前后在库区设立两处军事基地及农场,并将西安市的大批知识青年招收为农工安排到库区建农场。
念念不忘返乡的移民们,在库区水位的节节下降中看到了回家的希望。他们开始偷偷地返回,在河滩上搭起庵棚,跟军队和农工争夺土地,并与政府部门展开拉锯——你追我跑,你退我返。
随着返库人数的不断增大,返库移民推举出自己的代表,日后闻名的四大代表苗福群、陈文山、王福义、刘怀容正出于此时。
返库在1984年的“祭祖活动”中达到了顶峰。当年清明节,返库移民以祭祖的名义强行进库,抢收部队和农工的小麦,砍伐部队和农工的树木,受到冲击的农工则开着汽车,打着“移民要返库,农工要返城”的牌子,浩浩荡荡来到西安,向陕西省政府要求返回城市。
“双返”行动惊动了中央。在听取了陕西省政府的有关汇报后,1985年5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中办发[1985]29号文件,即《关于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安置问题的会议纪要》,对移民返库的要求做出了积极回应:“三门峡库区移民现有40万人,其中15万人生产、生活很困难,需要返回库区安置。”
政策突变
所谓安置,其实就是解决土地问题。
当时的库区土地共有58万亩,其中归地方国营农场使用的有30万亩,归部队农场使用的有22万亩,根据陕政发[1986]44号文件和陕政发[1985]133号文件,地方国营农场向当时的渭南地区行署划交21万多亩土地,部队农场则向渭南地区行署划交土地10万亩。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份文件中,对于这总共31多万亩移交土地的用途,都做出了明确的表述;即“为安置返库移民”。
土地有了着落,搬迁工作随之展开。为了严格控制返库人数,政府对当时的搬迁户实行自搬、自迁、自建原则,尽管可能无力承担此间费用,但返乡心切的移民还是有些迫不及待。当时,在渭北至渭南上百公里的公路上,男女老少肩背手提,一时间,主要的交通工具架子车价格倍增。
据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介绍,移民返库工作于1986年开始试点,1987年集中进行,到1989年全面截止。
这里不能不提到一种情况,虽然国家计划的返库人数为15万,但由于大家对自搬、自迁、自建心存忌惮,以及很多人已经在外乡扎根等原因,实际返库的并没有那么多人。
据李万明介绍,1989年这项工作全面截止时,实际返库人数只有73900人左右,还不到计划返库人数的一半。这一数字在1992年渭南市移民局编写的《渭南地区移民志》中得以确认。
按照划交土地时的既定用途,上述31万多亩土地应该在扣除1万亩左右的公共用地后,平均分配给返库移民使用。这一原则在返库工作刚结束的1988年、1989年得以貫彻一当时,30万亩土地在7万多名移民中平摊之后,每人可以分到4亩左右土地。
这看起来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对该地区移民前的生活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它仅仅是以前土地的一半。
黄河的屡年泛滥留下了广袤的河滩,形成大片的可耕田,迁移之前,库区的人均土地达到8亩上下。据马连宝介绍,那时虽常遭黄河水患,却每每在水患的次年
因河水的冲积而获得大面积丰收。华阴市的北社、华西等地,一直是当地北粮南调的主要输出地。北社乡北社村农民张彦龙,将这块土地称为“白菜心”,是“休养生息的好地方”。
但是,土地政策在1990年风云突变。当地政府以返库移民未达到预定数量为由,强行将农民刚刚耕种两年的土地收回一半,只给每人留下不到2亩的可耕田,被收回的15万亩土地由各县、乡政府托管,被称为“预留地”,即以备将来可能返库的移民之用。
据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时任该局综合秘书并负责移民数字统计的李万明介绍,在长达四年的返库行动后,有返库意愿的移民,想回来的、能回来的早就回来了,留在外乡的,要么是在当地已经扎根,要么是在库区已无根可循。
承包梦魇
关于土地移民们还有一件事情“想不通”,这些土地刚从农民手中收回来不久,就以发包或者出租的方式,流落到了土地贩子、某些官员、企业主以及与掌握土地发包权者关系密切的其他人手中。
1992年前后,由于群众反映太多,渭南市政府不得专门组织一次有关土地使用状况调查。李万明在此次调查中担纲领队,与另外两位同事一道,耗费一个多月的时间,调阅各种合同文本,造访大量返库农民,得出的结论是:政府部门发包土地的现象普遍存在,并且,几乎所有土地,到达普通农民之手前都已经过转包手续。
此时,土地承包价格早已超过初始的承包价格,甚至已经翻倍。
在渭南民间大量流传着有关土地承包的交易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主角都与这条利益链顶端的某些政府官员有关。
李万明所做的此次调查验证了部分民间故事的真实性。大荔县移民局一位文书将大量的土地低价承包给自己的家人,这些土地又无一例外被加价转包给了其他人;
华阴市一位镇党委书记擅自将780多名移民退回原安置区后,将空出的1000多亩土地私自承包;
华阴市城建局一位领导在就任某乡乡长时,为自己低价预留了几百亩土地,谎称是从部队承包的土地,最近该领导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处分,非法承包土地的问题才逐渐浮出水面。
土地管理的混乱状况还引来了大批逐利的外乡人。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疏通关系,倒买倒卖土地。
据李万明介绍,截至移民返库全面结束的1989年,全库区共有假移民7000人左右,光华阴市华西镇西渭北村就有400人之多。他们中有的人能从乡村干部中买得户口,不仅分得土地,还尽享国家给予移民的各种福利。
然而,生活在本地的真移民却依然生活困顿。华阴市北社乡的很多田地位于毗邻渭河的坝北,几乎年年遭水灾,今年虽非涝年,仍有大片庄稼淹没在平流过来的渭河水里。该村村民张三民一家8口人,7亩半的口粮田全在坝北,如果遭遇水大的年份,那将颗粒無收。
另外,回库移民们人口的增长也使得很多家庭的土地捉襟见肘。北社乡北社村农民张彦龙对记者说,很多人丁兴旺的家庭,能有一半人分到土地就已经不错,有的八口之家只有两个人的地可供耕种,要想靠着土地吃饭,惟一的出路就是再去包地。
普通的农民要取得土地的初始承包权,几乎没有可能,只能从包括土地贩子的其他人手里拿到二手、三手甚至四五手的转包地,这时的承包价格已经严重高企。
大荔县平民乡平民村农民王春明、李德沾向记者透露,去年以每亩400元左右的价格从别人手里包到手的土地,非但没有赚到钱,还因为种地贷款欠下银行一屁股债。
“晚上睡觉我都想不通,”马连宝的语气里有种深深的伤感,“本来属于我们移民的地,现在却要高价向别人承包。”
争取依然未果
从政府部门将一半的土地从移民身边拿走的那一天起,移民争取要回这些土地的努力就没有停止过。
这方面,他们有一个启蒙者,就是上文提到的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
李从1985年渭南市移民局成立伊始(当时还叫渭南地区移民工作办公室)就在该局工作,当时的他并没有想到日后会走上一条与所属单位领导“对着干”的艰辛道路。
正是在他的不懈揭发下,移民们开始认识到土地分配中的巨大黑洞。在与地方政府交涉无果后,去北京上访成为移民们寄予厚望的选择。
2005年7月,移民代表曾经与陕西省、渭南市以及所辖库区各县(市)的相关领导进行对话,华阴市相关领导承诺在两个月内对移民反映的土地等问题予以解决,但承诺期限过了40多天后仍无答复。
大荔县的移民代表侯焕成,在北京上访时,被大荔县公安局带回,并遭检察院指控,可能面临三年的牢狱之灾,罪名是“诈骗罪”。事由为侯接受赵渡乡富民村的委托,为该村跑提前修路之事,并以要向有关人员进贡为由,从该村支取了26000元。检方控其编造进贡事由欺骗该村,为自己牟利。
接受采访的一位当地律师认为,且不说检方的指控能否站得住脚,单就这一案件被列为刑事案件,就让人大为生疑。侯与该村本为民事委托合同,代理费用的多少乃你情我愿,不管侯编造什么理由讨要这个代理费,都只是侯的一种“要约”,承不承诺的权利掌握在富民村的手里,怎么就成了一个刑事案了呢?
在对话不成的情况下,2005年秋收后,忍受不了高价承租土地的移民,在他们认为应该属于自己却被县政府发包的7000亩黄河滩地上,强行种下自己的小麦。然而,一个月之后的一个晚上,县政府动用大型机械,将已有半尺高的小麦全部铲掉。
“当初要知道这么难,我也不会干,”说起争取土地过程的艰辛,马连宝颇为感慨,为了此事,他前后已经投入了四五万元。
“但我既然做了,就要做到底。”这听起来不像是誓言,倒更像对自己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