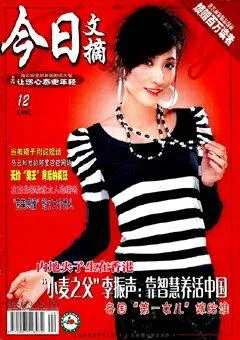在柏林散步
早晨醒得早,起身出门散步。沿着宾馆对面的花园无目的地行走。花园尽头,是一个十字路口,见一片被围起来的废墟,荒草丛生,似乎有点煞风景。回宾馆后听人介绍,才知这片废墟当年就是纳粹党卫军冲锋队总部,纳粹的头领常常带着他们的随从在这里进出。
对生活在柏林的犹太人来说,这就是地狱之门。盟军和苏联红军攻打柏林时,这里当然是主要的轰炸目标,炸弹将这一片楼房夷为平地。二战结束后,被摧毁的柏林很快开始重建,德国人在废墟上重新建造起一座新的柏林,但纳粹冲锋队遗址却一直废弃着。我想,这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警示。这样疯狂地镇压人民的武装机构,不应该再恢复。这废墟触目惊心地横陈在闹市中,也可以提醒人们这里曾发生过什么,提醒人们德国在二战中曾犯下的深重罪孽,提醒人们再不要重蹈覆辙。我很自然地想起二战后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的一幕,在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纪念碑前,他含着眼泪下跪。全世界都记住了德国总理的这个情不自禁的动作。一个敢于直面历史,勇于反思,记取教训的民族,是可以获得谅解并赢得尊敬的。
上午继续在城中漫步。离我们的宾馆不远,就是当年的柏林墙。隔离东西方的高墙早已倒塌,但遗迹还在。当年围墙的唯一通道,是一个森严壁垒的检查站,两面都有全副武装的军人把守。检查站的岗楼还在,楼边竖立着一块高大的广告牌。我们从东柏林一侧看,广告牌上是一个苏联军人的大照片;如从西柏林一侧看,则是一个美国军人的大照片,照片上的军人表情肃穆目光中含着几分忧郁。那目光给人的联想是复杂的,它们折射出一段漫长的不堪回首的历史,它们和人为的分隔和敌对连在一起,和无谓的流血和牺牲连在一起。柏林墙被推倒已经十多年了,在柏林城里,那道围墙的痕迹依然清晰留在地上,每个自由经过这里的人都可以看到地上那道用石头铺出的墙基我们的汽车在当年的检查站旁边停下来,我发现,那里有一家商店,店门外的墙壁上,镶嵌着一块块柏林墙的残片,残片上是彩色的绘画局部,依稀可辨流泪的眼睛,扭曲的肢体,让人产生沉重的联想。
看到了著名的勃兰登堡门。当年,它属于东柏林,由于它紧贴柏林墙,一般人难以走近它,在很多人心目中,它已经和柏林墙连成一体,也是咫尺天涯的隔绝象征。柏林墙的墙基,很触目地横过勃兰登堡门前面的大街,每一个穿过街道的人都会看到它踩到它bogK81QMSaQMiTOaPtazHg==越过它,此刻,它只是地上的一道痕迹了。勃兰登堡门前的广场上,有不少游览拍照的人,阳光下,门顶上那组青铜雕塑闪闪发亮。柏林墙被推倒的那一天,欢庆的德国年轻人爬到了门顶上,雕塑的马腿和人像的手足都被扭歪了,事后费了很大的工夫才将它们修复。穿过勃兰登堡门往东,就是当年的东柏林,正对勃兰登堡门的是著名的菩提树大街。我们眼帘中那些方正高大的建筑,基本上都是二战后建造的,1945年前的老柏林,已经旧迹难寻了。
不过,在柏林还是到处能看到旧时建筑,少数是残存的,大部分是重修的,如那幢堪称巍峨的国会大厦。当年希特勒利用那宗不知所终的国会大厦纵火案,清洗了德国共产党,国会大厦也因此名扬天下。这幢大厦当年也被战火严重损伤,那个巨大的绿色圆顶,几乎整个被炮火掀去。战后,大厦被修复,但那个圆顶,却只留下镂空的骨架。这是战争的纪念,也可以让德国人睹物思史,反思那段耻辱的历史。
洪堡大学也在菩提树大街边。车经过时我走进校门看了一下。洪堡大学是世界著名的大学,许多了不起的文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曾任教或就读于此,其中有诗人海涅,哲学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科学家爱因斯坦,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在这里读书。曾先后有三十多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这里上学或任教。
因为是星期天,静悄悄的校园里看不见人影。两棵高大的银杏树金黄的落叶撒了一地,落叶缤纷的草地上,有一尊大理石胸像,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特奥多尔·蒙姆森(Theodor Mommsen),这位德国历史学家,曾在洪堡大学讲授卉代史,也曾任该校校长。他的《罗马史》写得文采斐然,获得了190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此刻,这位老人独自在他曾经工作过的校园里沉思,凝视着遍地黄叶……
(孙佳宁荐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