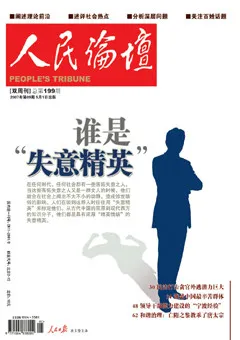和谐社会呼唤“良性精英循环”
实现阶层群体之间精英的良性互换和替代,恰恰是循环系统中“失意精英”迈向“适意精英”的社会逻辑起点所在
大浪淘沙,所有的精英都处于时空的客观环境中。时空变动不居,因而精英的起伏涨落也就成为必然。彼时不等于此时,彼地不等于此地。社会本身就是“筛选器”,名垂青史、流芳百世的精英者有之,而昙花一现或遗臭万年的所谓精英者亦有之。
精英的失落,与社会结构变迁、体制转型、文化传统、社会习俗的关系十分密切
张某原为政府要员,但在政府机构改革精简过程中被“剥离”而能迅速地适应市场转型的需要,将政治资源转换为经济资源,摇身一变而成为腰缠万贯的企业家明星,这种精英往往被一些社会学家称为机会面前“不落空”的精英,其所运用的精英转换策略是资源的替代。精英理论学者常常把精英的变迁与转型界分为精英替代(再生产)模式和精英循环模式。能从一种精英转换为另一类精英,这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中屡见不鲜,比如精英循环模式则是通常所理解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所指的是新的精英分子替代了旧的精英分子,恒定的位置上已经换了新面孔,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产生所谓的“失意精英”了。
失意精英,准确地说,是指与其精英身份和地位相应的权力、财富或声望,应该得到维续或提升,但却没有得到维续或提升,因而产生一种失落感(即失意)。
我认为,失意精英的“失意”主要不是自身的原因,而是因为外在的原因所导致的失落感。也就是说,精英的失落,与社会结构变迁、体制转型、文化传统、社会习俗的关系十分密切。
前途看好的政治要员或因机构改革精简,或因岗位重设标准变化如学历文凭(文化资源)不够而旁落乡野,或因传统文化中的“圈子运动”、“派性斗争”、“山头主义”(社会关系资源缺乏)而沦为“替罪羊”;财富巨大的百万富翁也可能因经济体制的转轨而一夜之间沦为街头乞丐;专业技术职称评聘中有的人可能会因为权力干扰、评委不公等而不能正常晋升;众星捧月的文化精英如歌星影星或专家学者也可能因婚恋破灭、道德瑕疵或权力争斗而甩离出主流舞台;平时成绩出众的高考生也可能考试“犯刹”而名落孙山等等。
在体制和机制运行不公正的情况下,过高的期望一旦没有实现,往往造成巨大的“心理落差”
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这么一类目前年龄50多岁的群体:在20岁左右的时候,他们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学校成为“革命阵地”,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几乎没法读书学习;而到改革开放提出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的时候,他们很多年富力强却因学历不够、知识不足而被拒绝进入主流社会的机会;进入1990年代,企业掀起下岗分流的时候,他们因知识陈旧首当其冲被彻底淘汰出局。这是整体精英的失落,这是历史的遗恨。而在这么一个年龄段的群体中,只有少数人能够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或家庭的“红色”背景而成为今天的精英分子,如有的成了省部长,有的成为亿万富翁。
单位组织的变迁同样导致整体性的精英失落。过去的国有企业、产业工人阶级是“老大哥”,但市场转型条件下国有企业的整体衰退和部分破产,导致了工人阶级精英地位的整体失落和无数工人的下岗分流。这是体制转型的“阵痛”和代价。
失意精英的出现总是与社会结构转型、文化传统、心理预期密切相关。从根本上是制度公正问题,而制度公正的运行又依赖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体制。所谓制度公正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制度的设置必须公正科学;二是制度的执行必须公正合理。也就是说,制度公正是社会公正的首要价值。制度公正就是要使符合条件的社会成员应得所得(或奖或惩、或升或降),不能有偏差。我们不能做到绝对公正,但必须确保相对公正。日常生活工作中,一些当权者借口做不到绝对公正就连相对公平都不去做而且有意损害相对公平,如在提拔用人或免职、利益分配等方面有意采取“双重标准”或“多重标准”,让自己“圈内”不应得者而得益,而让“圈外”应得所得之精英失利。
按理说,农业社会主要是“关系本位”,工业社会应该是“能力本位”主导,但在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里,在某些领域、某些地方、某些单位中传统文化中的“关系本位”反而得到了强化,这实际违背了市场社会发展的逻辑,也可能本身具有中国特色。体制改革问题的核心是要制约权力。从集权到分权转型后,地方或单位“一把手”的权力很少再受垂直制约,而在法治较弱和地方或单位内部权力制约机制缺失的情况下,“一把手”成为地方“诸侯”或单位“猴王”,在人事安排、资源和利益分配方面难免为所欲为,或者通过权力“寻租”给予相关利益者,这些都有可能使精英旁落、失意。
精英的失意,同样会在攀比中逐步形成。同样的起跑线,却会有不同的结果。人们在比较中心理失衡,在比较中产生了社会愤懑。精英的失意,也恰恰会与精英者本身的心理期望有关。在体制和机制运行不公正的情况下,过高的期望一旦没有实现,往往造成巨大的“心理落差”。
实现阶层群体之间精英的良性互换和替代,恰恰是循环系统中“失意精英”迈向“适意精英”的社会逻辑起点所在
失意精英失落后的心态和言行也各有千秋,总体上呈现出几个趋势:一是顺其自然,得过且过,或超然物外,或意志颓毁,或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倾注于儿孙;二是消极对抗,处处发泄不满,与上司作对,与同事不和;三是积极抗争,越是逆境越进取,乃至去讨还公道,维护基本权利;四是转移兴趣爱好,潜心钻研,并有所成就。
失意精英伤害的是个体,一定程度浪费了社会才智,揭示出社会体制的流弊。改革社会体制,促进阶层内部升迁流转机制的合理科学化,实现阶层群体之间精英的良性互换和替代,恰恰是循环系统中“失意精英”迈向“适意精英”(人生适意)的社会逻辑起点所在。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在各大阶层之间进行上下左右流转和互换,恰恰是现代社会趋高级发展的需要和体现。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同样可以转化为政治精英;昔日旁落的政治精英无不可自由转换为“小本买卖”起家的新的经济精英,或者成为“术业专攻”的学术巨匠;丧失巨大财富的经济精英或者沉入社会底层的文化精英亦可回归校园成为“人类灵魂工程师”或从事其他创业。
良性的精英循环、良性的精英替代始终是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的要求和体现。但恶性的精英循环和替代则需要我们有勇气、有智慧去改革体制,净化风气;需要我们调整收入分配机制,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和传统户籍制度,改革僵硬的干部人事制度,营造良好的教育、就业环境;需要我们去倡导“能力本位”,破除“关系本位”,创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氛围。
失意精英丧失的是地位和身份,不灭的是精神和人格。重振雄风、东山再起,或者转移领域、另起炉灶,调整心态,都应该成为失意精英走出人生阴影的追求,而这也恰恰需要社会体制的创新、社会环境的改造、舆论氛围的酝酿,需要形成时代新的风尚。这样的风尚,不是精英的失落和淘汰,而是精英的再生和重替。同样,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各阶层的共同努力,需要社会合力去化解分配不均带来的危机,需要形成心态更为健康、行为更加理性的阶层关系,形成宽厚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社会群体心理。这才能带来马克思所期盼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生、华北科技学院副教授)
精英“恶性循环”典型案例
4月12日,原上海建委党委书记、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会长陈士杰因涉嫌在房地产项目开发中谋取非法利益而被相关部门调查。这是继3月底上海市房地局原副局长、上海土地学会会长殷国元因涉嫌违法违纪被上海市纪检部门调查后,又一名与房地产管理有关的更高级别的上海主管部门高层人士接受调查。这两人都曾经是上海市政府主管房地产部门的高官,退休后又担任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协会或学会的负责人。他们的被调查,使得前房地产主管部门官员—房地产相关协会—开发商之间盘根错节的土地“食物链”开始露出冰山一角。
上海一位房地产研究专家指出,“开发商通过聘请这些退休官员到公司任职,或者通过结交与房地产相关的各类协会的负责人,打通土地审批的各个环节,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香港大公报就此发表评论指出,要破解公权出轨、权商勾结的权力迷局,需要警惕权场“旋转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