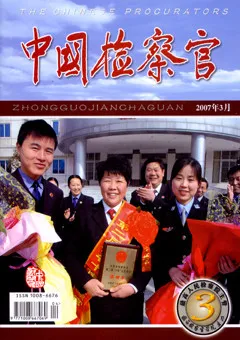投毒(危险物质)行为中一罪与数罪的认定
[基本案情]
案例1:
被告人黄某为了牟利,勾结被告人李某于1997年10月22日至11月3日,趁人不备,先后9次将毒鼠药磷化锌投入9户村民的猪槽内,每次毒死毛猪1至2头,总共毒死村民毛猪16头,价值人民币四千余元。在作案过程中,被告人黄某直接投毒,被告人李某望风。事后,二人分别单独或一起向受害村民购买死猪肉,然后卖给某食品加工厂,获利280元。该食品加工厂及时发现猪肉有毒,即采取了必要措施,才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黄某和李某事前通谋,共同实施了故意投毒的行为,给公共安全造成了危险,依法判处二人犯投放危险物质罪。
一审判决后,二被告不服,依法提起上诉。二被告辩称,二人主观上并不想危害公共安全,客观上投毒行为只是造成了猪的死亡,并且每次只毒死一、两只猪,谈不上危害公共安全;出售毒猪肉给食品加工厂,是出于牟利的目的,自己认为只要将猪的内脏洗净,就不会引起中毒,所以不存在放任危害公共安全结果发生的情况。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黄某和李某采取投毒的危险方法破坏他人财物、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案例2:
被告人叶某1997年12月某日晚,窜至本村农民孙某家,将事先准备好的带有剧毒鼠药的玉米棒放在孙家的牛槽里,毒死1头耕牛,价值3000元。次日,叶某以1000元价格将死牛收购,后到市场贩卖。1997年12月至1998年2月间,叶某采取投毒的手段,以收购被毒死的耕牛贩卖谋利为目的,先后在各地作案17起,毒死耕牛20头,价值5.8万元。其中,叶某收购13头到市场贩卖,牟取非法利益八千多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叶某,为图私利,使用投毒方法毒死耕牛,又收购贩卖被其毒死的耕牛,致使公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危害,且足以危害群众身体健康,其行为已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其犯罪手段恶劣,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依法严惩。一审法院作如下判决:叶某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判决后,叶某不服,依法提起上诉。其辩称,原审判决认定投放危险物质罪部分事实不清,量刑过重。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叶某以收购被毒死的耕牛贩卖牟利为目的,向他人家牛棚及野外散放的耕牛附近投放毒饵,造成20头耕牛中毒死亡,致使村民个人财产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同时,也给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危害,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销售有毒的牛肉,危害不特定多人的身体健康,情节恶劣,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二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中对叶某犯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定罪和量刑部分;叶某犯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
[分歧意见]
案例1与案例2的案情相似,但判决却迥异,而案例2中一审和二审的判决差异之大,更是让人震惊。定罪上,不仅罪名完全不同,而且由一罪变成两罪;量刑上,由死刑到有期徒刑11年,真是生死之别。司法实践中,对同一投毒行为,不同地区的同级法院,同一地区的不同级别法院就会有不同判决,往往差异很大。这种情况的存在不仅使被告人的自由难以保障,甚至被告人的生命权也难以保障,且极损法律的尊严和统一性,从而导致法律适用之目的不可得,甚至适得其反。所以,无论是理论上抑或实践中都应该重视投毒行为的定罪问题(事实上就是投毒行为的一罪与数罪问题),尤其理论上,更应结合实践来研究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极具有实践和理论意义。
[评析意见]
一罪与数罪问题在刑法理论中也是争议比较大的。有学者将这个问题简化到不值得研究的地步,也有学者认为该问题是刑法理论中的哥德巴赫猜想。事实上,该问题从立法的角度看,是一个极其复杂、难度极大的问题,说其是刑法理论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并不过分。但从司法的角度看,却应该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可由于立法的不科学、不完善,加之司法实践现象的繁杂,该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又是有一定难度的。在理论界,关于区分一罪与数罪的标准众说纷云,如行为标准说、法益标准说、因果关系标准说、犯意标准说、法规标准说、构成要件标准说及广义法律要件说。在我国刑法学界普遍公认,犯罪构成是区分一罪与数罪的标准。[1] 某行为事实符合一个犯罪构成的为一罪,符合两个以上犯罪构成的为数罪。具体地说,行为人以一个或概括的犯罪故意或过失,实施一个或数个行为,符合一个犯罪构成的为一罪;以数个犯罪故意或过失实施数个行为,符合数个犯罪构成的为数罪。下面我们就以此为标准对投毒行为中的一罪与数罪的几种情况进行分析论述。
(一)投放危险物质罪与他罪发生想象竞合的情况
想象竞合犯,亦称想象数罪,是指行为人基于一个罪过,实施一个危害行为,而触犯两个以上异种罪名的犯罪形态。其具有两个特征:(1)行为人实施一个犯罪行为,即行为的单数性;(2)行为人所实施的一个犯罪行为必须触犯两个以上的罪名,即行为触犯罪名的复数性。那么,据此,投放危险物质罪与他罪想象竞合是指行为人实施一个投放危险物质行为,而触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和他罪的情况。其主要特征有:(1)行为人实施一个投放危险物质行为;(2)行为人的投放危险物质行为不仅触犯投放危险物质罪,而且还触犯他罪。所谓触犯投放危险物质罪是指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即行为人的投放危险物质行为危及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或财产安全。若仅是单纯的投放危险物质行为而不危及公共安全则不构成这种情况,如甲某毒杀乙某两头猪。
在实践中,投放危险物质罪与他罪的想象竞合有以下几种情况:
1. 投放危险物质罪与杀人罪的竞合。这种情况是指行为人采取投毒方法杀人而触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和杀人罪的情形。这种情况的构成条件有:第一,行为人实施一个投毒行为。第二,行为人的投毒行为危及了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安全。第三,行为人主观上目的是杀特定的个人或少数人,但对其他多数人的生命持放任态度。例如,某甲为杀某乙,向某乙所在食堂投毒,导致10人死亡。甲的行为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与杀人罪的想象竞合。
2. 投放危险物质罪与盗窃罪的竞合。这种情形指行为人为盗窃而投毒,但盗窃行为没有实施而触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和盗窃罪。事实上是投放危险物质罪与盗窃罪(预备犯)的竞合。构成这种情形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行为人只实施投毒行为,没有实施盗窃行为,实际上,这个投毒行为是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实行行为,是盗窃罪的预备行为。第二,投毒行为危及了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财产安全。例如,某甲为偷集体鱼塘的鱼而投毒后被抓获。某甲的行为就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与盗窃罪的竞合。
3. 投放危险物质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竞合。这种情况指行为人采取投毒方式破坏公私财物而触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其主要特征有:第一,行为人实施了投毒行为,没有实施其他犯罪行为。第二,行为人出于破坏公私财物之目的。第三,行为人的投毒行为危及了公共安全,即危及了不特定多数人的财产安全。例如,甲出于泄私愤,向集体鱼塘投毒,结果造成十余万元的损失。甲的行为便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竞合。
4. 投放危险物质罪与破坏生产经营罪的竞合。这种情况是指行为人出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采取投毒方式残害耕畜而触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和破坏生产经营罪。其特征表现为:第一,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第二,行为人实施了投毒行为。第三,行为人的行为对象是耕畜,如耕牛等。第四,行为人的投毒行为不仅危及生产活动,还危及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财产安全。例如,甲为泄私愤,向全村牛槽中投毒,结果导致23户人家的30头牛中毒死亡。甲的行为就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与破坏生产经营罪的竞合。
5. 投放危险物质罪与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或者非法狩猎罪的想象竞合。这主要是指采取投放危险物质的方法去非法捕捞水产品,或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或非法狩猎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实际上实施了一个行为,即投放危险物质的行为,但这个行为同时也是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或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或者非法狩猎行为,如果该行为既触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又触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或者非法狩猎罪,就构成想象竞合。
想象竞合犯属于想象的数罪,由于其行为的单数性,实质上是一罪。但由于其毕竟触犯两个以上罪名,作为一罪处理,就存在着运用哪个罪名的问题。我国现行刑法未对想象竞合犯及其处断原则作出任何规定。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和司法机构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一般认为,对于想象竞合犯应采用“从一重处断”的原则予以论处,即对于想象竞合犯不必实行数罪并罚,应按照其犯罪行为所触犯的数罪中法定刑最重的犯罪论处。[2]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也规定,使用爆炸、投毒、设置电网等危险方法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或者非法狩猎罪,同时构成刑法第114条或者第115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二)投放危险物质罪与他罪发生牵连的情况
牵连犯是指行为人为犯某罪,其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的情形。其主要特征有:(1)行为人实施了两个以上行为,即行为的复数性。(2)两个以上的行为之间存在着牵连关系。所谓牵连关系,就目前刑法理论来讲,是原因与结果或方法与目的的关系。(3)两个以上的行为各能独立成为犯罪行为,各触犯不同的罪名。由上述观之,投放危险物质罪与他罪发生牵连的情况是指行为人为实施他罪,其所采取的方法行为——投放危险物质行为又触犯投放危险物质罪,目的行为触犯他罪的情况,或者行为人为实施投放危险物质罪,其采取的方法行为又触犯他罪的情况。从我国目前的立法规定来看,投放危险物质罪与他罪的牵连关系不存在原因与结果关系,即投放危险物质行为不能成为原因行为或结果行为,而只存在方法与目的关系,即投放危险物质行为可以成为方法行为或目的行为。但在司法实践中,投放危险物质罪与他罪发生牵连的情况往往是投放行为与他罪行为是方法行为与目的行为的牵连关系,投放危险物质行为是目的行为的很少。这也与立法规定及投放危险物质行为的本身特殊性有关。下面分几种情况来分析投放危险物质罪与他罪牵连的情况。
1. 投放危险物质罪与盗窃罪的牵连情况。这种情况是指行为人为了盗窃而实施投放危险物质行为,先将盗窃对象杀死再实施盗窃行为。其构成条件有:第一,行为人实施了两个行为,即投放危险物质行为和盗窃行为。第二,投放危险物质行为和盗窃行为之间存在牵连关系,即存在方法行为和目的行为的牵连关系。第三,投放危险物质行为和盗窃行为分别触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和盗窃罪,即投放危险物质行为危及了公共安全,盗窃行为侵害了公私财产权。如果投放危险物质行为并未危及公共安全,则不属于这种情况。例如,甲某采取投毒方法将邻居的猪毒死后偷走的行为就不危及公共安全,其投毒的行为不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而甲某的行为仅构成盗窃罪,不存在投放危险物质罪与盗窃罪的牵连。但如果甲某为盗窃而大面积向本村各户猪槽中投毒,结果毒死毛猪30头,并将其中20头猪偷走。那么,甲某的投毒行为就危及了公共安全,触犯了投放危险物质罪罪名,甲某的行为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与盗窃罪的竞合。在实践中,投放危险物质罪与盗窃罪的牵连还存在这种情况,即行为人为实施投毒犯罪而盗窃毒药。在这种情况下,投毒行为是目的行为,盗窃行为是方法行为,二者构成方法与目的的牵连。例如,甲某为了投毒而先行盗窃某药店大量砒霜,后将砒霜投入某食堂面粉中,致使40人中毒。甲某盗窃砒霜行为是方法行为,触犯盗窃罪罪名;投毒行为是目的行为,触犯投放危险物质罪。甲某的行为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与盗窃罪的牵连。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很少见。
2. 投放危险物质罪与销售有毒食品罪的牵连情况。这种情况是指行为人出于牟利之目的,采用投毒方法将畜禽毒死,而后收购出卖。这种情况表现为几个特征:第一,行为人出于牟利的目的。第二,行为人实施了三个行为,即投毒行为、收买行为和出售行为。投毒行为与收买行为、收买行为与出售行为及投毒行为与出售行为之间均存在方法和目的关系。第三,投毒行为危及公共安全,触犯投放危险物质罪;收买行为由于刑法无明文规定不触犯任何罪名;出售行为触犯销售有毒食品罪。由于收买行为不触犯任何罪名,这种情况只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和销售有毒食品罪的牵连。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情况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伴随着投放危险物质罪与破坏生产经营罪或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想象竞合。例如,甲某为牟取不法利益,向本村村民猪槽中投毒,毒死10户村民毛猪21头,而后低价收购再高价售出。甲某的行为便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想象竞合,又一起与销售有毒食品罪构成牵连。
3. 投放危险物质罪与盗窃罪和销售有毒食品罪的牵连情况。这种情况指行为人为牟取非法利益,采取投毒手段将畜禽毒死后盗走,而后出售的情况。其构成条件有:第一,行为人出于牟取非法利益之目的。第二,行为人实施三个行为,即投毒行为、盗窃行为和出售行为。投毒行为和盗窃行为、出售行为之间依次存在方法和目的的关系。第三,投毒行为危及了公共安全,触犯投放危险物质罪;盗窃行为侵犯公私财物权,触犯盗窃罪;出售行为侵犯了国家对食品卫生质量管理秩序,触犯销售有毒食品罪。例如,甲某为牟取非法利益向集体鱼塘投毒而后将鱼偷走出售的行为便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与盗窃罪和销售有毒食品罪的牵连。
牵连犯无论是从形式上或实质上都是数罪,这一点是共识。但我国刑法学界对牵连犯的处断原则,由以往普遍坚持通说即“从一重处断”原则,发展到三种观点,即从一重处断说、并罚说和从一重处断和数罪并罚择一说。我们认为,牵连犯虽然是数罪,但其并不同于一般的数罪,毕竟其内部存在牵连关系,若将其按数罪并罚处断,则有悖牵连犯理论,抹杀牵连犯本身的特殊性;牵连犯也不是单纯的一罪,按一罪处断也没有道理。所以,一般情况下,牵连犯按“从一重处断”是合理的,即按数罪中最重的一个罪定罪,在量刑时考虑其他罪情况再酌情从重处罚。当然,对于法律有明文规定对牵连犯的处断原则时,应按法律规定。对于以上投放危险物质罪与他罪牵连的情况,现行刑法均未明文规定对其处断原则,所以应按“从一重处断”的原则。投放危险物质罪与上述其他罪相比,其法定刑重于其他罪,所以,对于投放危险物质罪与上述其他罪牵连的情况,应定投放危险物质罪,在量刑时考虑其他罪的情况。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投放危险物质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及破坏生产经营罪竞合后又与销集有毒食品罪发生牵连的情况。对这种情况,首先按想象竞合的处断原则处理,再按牵连犯的处断原则处理。按想象竞合的处断原则“从一重处断”,投放危险物质罪与破坏生产经营罪或故意毁坏财物罪发生想象竞合时应定投放危险物质罪;按牵连犯处断原则,投放危险物质罪与销售有毒食品罪发生牵连时应定投放危险物质罪。所以,对这种情况应定投放危险物质罪,量刑时应考虑破坏生产经营罪或故意毁坏财物罪和销售有毒食品罪的情节。
(三)上述两案的解决
现在,基于以上论述,让我们来看看案例1和案例2的情况。
对于案例1,被告人黄某和李某辩称每次只毒死一、两只猪,谈不上危害公共安全。也有学者认为,黄、李二人的投毒行为仅从每次单独看,并不危害公共安全,只是将投毒行为与出售有毒食品行为联系起来才危及公共安全。对于案例2,二审法院也认为被告人叶某的投毒行为仅致使村民个人财产遭受重大经济损失,不危及公共安全。这样,我们首先就必须弄清案例1和案例2中的投毒行为是否危及公共安全,即如何认定刑法分则所规定的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
行为理论是刑法理论中的核心理论,也是难度很大的理论。从因果行为理论、目的行为理论到社会行为理论、人格行为理论,都没能将纷繁复杂的行为事实高度抽象概括出一个能得到共识的关于行为的概念,更谈不上给出一个具体的认定行为的模式。但是,尽管如此,对于司法实践来说,认定行为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我们认为,认定某一行为事实是否刑法分则所规定的行为,必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也就是说,客观外在的行为表现必须是在主观意思支配之下的,在同一主观意思支配之下的数个自然行为在法律上表现为一个法律行为。客观外在的数个自然行为由于属于同一主观意识支配而使其间具有内在联系,就表现为一个整体。所以说,认定行为时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要从整体把握,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不能机械地割裂属于一个法律行为的几个自然行为的内在联系。例如案例1和案例2的投毒行为,如果单独孤立地看每一个投毒行为都不危及公共安全,即不是刑法分则所规定的作为投放危险物质罪构成要件的投毒行为,但是这一系列的投毒行为之间并不是相互孤立、毫无联系的,由于这一系列的投毒行为在同一的意思支配之下,即案例1和案例2中的被告人在行为之始,就准备实施这一系列的投毒行为,而不是一次,其主观意识中存在着要分次向各家各户投毒,即被告人明知其一系列投毒行为会危害公共安全,而事实上,作为一个整体的这一系列的投毒行为也危害了公共安全,所以,案例1和案例2的投毒行为能够作为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构成要件的投毒行为。如果能够割裂来理解的话,犯罪分子很容易规避法律,比如将能够一次实施的行为分次实施,而每一次都不构成犯罪或不构成重罪,如若这样,不仅投放危险物质罪可以规避,侵财犯罪、伤害杀人犯罪都可以规避。显然,对行为性质的考察并非单纯地从客观考察,还要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也不能分割地来考察,而应从整体上把握。
解决了行为认定的问题,那么,对于案例1来说,被告人黄某和李某实施了三个行为,即投毒行为,收买行为和出售行为。投毒行为触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构成想象竞合;收买行为不触犯任何罪名;出售行为触犯销售有毒食品罪,由于出售行为和投毒行为之间存在目的和方法的牵连,则销售有毒食品罪构成与投放危险物质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牵连。在这种情况下,应定投放危险物质罪。一审和二审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但应该在判决中说明竞合和牵连的情况。对于案例2,叶某的行为依上面的论述,应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和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想象竞合,而后与销售有毒食品罪发生牵连。在这种情况下,定投放危险物质罪,在量刑时应考虑破坏生产经营罪和销售有毒食品罪的情节。所以,一审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二审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即使数罪并罚,也应是投放危险物质罪和销售有毒食品罪的并罚,因为投放危险物质罪与破坏生产经营罪的竞合应定投放危险物质罪。
注释
[1]参见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85~590页。
[2]高铭暄:《刑法学原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
作者:国家检察官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102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