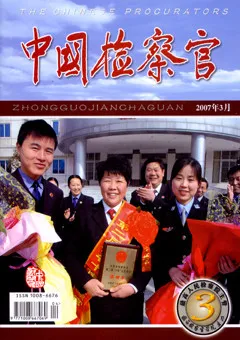期待可能性理论的产生及适用
[案 例]
被告人系一马车夫,受雇驾驭一双辔马车,其中一马有以马尾绕缰并用力下压缰绳之癖。被告人向雇主提出并要求另换一匹马,但未获允许。1896年7 月19日,该马癖性突然发作,用尾绕缰下压,致使马车失控,将一行人撞倒致伤。检察官以过失伤害罪对被告人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宣告被告人无罪。检察官提出上诉,此案移送帝国法院审理。帝国法院驳回了检察官上诉,理由是:要认定被告具有过失责任,仅凭其认识到该马有以尾绕缰的习惯并可能导致伤人还不够,还必须以被告基于此认识向雇主提出拒绝驾驭此马为必要,而德国当时正处于经济萧条时期,无法期待被告人不顾丢失来之不易之工作的危险拒绝驾驭此马,故被告人不应负过失责任。[1]
[案中法理]
一、期待可能性理论的产生及发展
期待可能性是指在行为当时,能够期待行为人避免该犯罪行为而实施合法行为的可能性。如果不能期待避免犯罪行为实施合法行为,即没有这种期待可能性时,即使能够认识犯罪事实或能够意识该事实的违法性,对行为人也不能给以规定的非难,行为人就没有故意责任或过失责任。如果期待可能性相对较低,就应当相应减轻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期待可能性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典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霍布斯。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是由于眼前丧生的恐惧而被迫作出违法的事情,他便可以完全获得宽宥,因为任何法律都不能约束一个人放弃自我保全” ,“如果一个人缺乏食物或其他生活必需品,除非犯法没有任何其他方法保全自己,就像在大饥荒中无法用钱买或靠施舍得到食物时行劫或偷盗一样,或是像夺取他人之剑以保卫自己的生命一样,那么他就可以获得完全的宽宥。”[2]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形成,也就是心理责任论向规范责任论转变的历史过程。在德国法院作出该判决之后,德国学者弗兰克、高尔德·施密特、爱贝尔哈尔·施密特等人以此为契机,使期待可能性理论得以确立和发展。弗兰克在1907年提出,要使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及其结果承担责任,除了要求有责任能力、故意或过失之外,还要求有“随附情况的正常性”。高尔德·施密特则指出,责任的更本质的要素是义务违反性。他提出了二元的规范论,一是要求人们采取一定外部态度的法律规范;二是命令人们作出或采取外部态度所必要的内心态度的义务规范。违反前一种规范的,具有违法性;违反后一种规范的具有有责性。爱贝尔哈尔·施密特则认为,法规范可以从不同侧面分为评价规范与意识决定规范,评价规范是针对一般人的,意识决定规范只是针对可以依法作出意识决定的人;追究责任除了要求行为人具有故意、过失的心理要素外,还要求可能期待行为人实施其他合法行为而不实施违法行为的规范要素(期待可能性的要素)。至此,期待可能性的理论便得以确立。[3]
在日本,被学界广为引用的运用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先例是有名的第五柏岛丸案件[昭和8年(1933年)10月21日大审院判决]。案件梗概是:被告为领有乙种二等驾驶执照的海员,自昭和7年(1932年)6月起开始受雇于广岛县音户町的某航运业者,任该人所有的发动机船第五柏岛丸号(九吨)的船长。9月13日上午6时,被告人驾驶第五柏岛丸号满载乘客128人(限乘24人)由音户町发航前往吴市。途中,另一船自右后方急驰而来,右舷乘客为免受追越时海水激起的浪沫溅湿,纷纷向该船左舷移动,船身因载重过多而左倾,海水随即由船尾浸入,终至该船沉没,结果乘客溺死28人,致伤7人。初审的广岛法院吴市分院及广岛高院都以被告人触犯业务过失致人死伤罪及业务过失倾覆交通工具罪,按想象竞合犯以业务过失致人死伤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6个月。但最后大审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过不当,改判被告人300日元的罚金。理由是:事故发生的当时,从音户町到吴市上班的人非常多,但作为交通工具的船舶却很少,上班的职工不愿迟到,因而不顾船员的制止而争先乘船;负责管理的警官也只考虑职工的准时上班,督促严格遵行出航时间,放松了对超过定员的监督;该船的航运经费,需以搭载超过定员的乘客的收入才能得到补偿,船主不顾身为船长的被告的再三提醒,命令搭载过多的乘客。总之,对此因超载而引致的惨剧,身为船长固无从推辞其应负之责,但如将责任完全归诸于被告一人,又显过度残酷。大审院斟酌这些基本情事,又鉴于被告人缺乏资产,收入菲薄,故作出上述判决。[4]
在日本通说认为,缺乏期待可能性是一般的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因此诸如违法拘束命令、基于强制的行为、义务冲突、安乐死等尽管在法律上没有规定为正当化事由,但法官都能以行为缺乏期待可能性为由,宣告行为人责任的阻却。同时一些更为细微的刑法根本无法精确规定的一些场合,法官也能根据自身对于社会生活的理解和认识,设身处地的站在行为人的角度分析是否存在责任阻却的可能,如: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实施了轻微的盗窃,或者在再就业极其困难的状况下,受职务上司的强索,如果拒绝,则害怕失业,而实施某种违法行为。判断期待可能性的有无及程度,通说采用“行为人标准说”,即应以行为人本身的能力为标准。因为既然个人责任是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故判断期待可能性标准只能求之于行为人的情况。因此,正如日本学者大家仁所评价的那样:“即使按照行为人标准说,对有责任能力的行为人不能期待适当行为的情况,绝不必过多担心,所谓招致刑事司法的弱化,不过是杞人忧天。”[5]
“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关系,任何科学不论离人性多远,它们总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 [6]由期待可能性在德日的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不难看到,较之心理责任论,规范责任论对刑事责任的追究作出了某种更为严格的限制,因而可以看成是一种通过限制国家刑罚权而保障被告人权利的刑法理论。对此,大家仁教授曾经对期待可能性理论作出过以下恰当的评价: “期待可能性正是想对在强有力的国家法规范面前喘急不已的国民的脆弱人性倾注刑法的同情之泪的理论。” [7]因此可知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精神实质在于对人性的关怀。
苏格拉底曾说:“各种学问,最根本目的,是要解决‘人怎样活着的问题’”,把这个“苏格拉底命题”换个说法,就是:各种学问,最根本的使命,是如何使人类生活幸福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增进人类福祉的问题[8]。因此,这种极富弹力和开放性的期待可能性就可以让法官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面前可以做到遵循法律偏爱人情照顾人生的基本精神,使得表面上生冷僵硬的刑法变得温润而通融并由此获得公众的亲和与认同,进而可以将自己宏大抱负得以顺利实现。
只有生活才是富有创造性的,审视期待可能性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我们当为法官不拘形式的睿智和机敏而赞叹,为其想象力与独创精神而折服。案例永远走在法律前面,故此,刑法的生命不仅在于逻辑,更在于对案例,对生活的真切把握,不能把案件事实与法条间的“眼光之间的往返流转”仅想象为只是判断者视角的转变,其更是刑法在思辨和哲理中自我成长的必然。“情理是法的生命”,期待可能性理论就是在对案例的把握和升华中的产生,并将情理人性置于刑法的显要地位,使刑法摆脱了僵硬呆滞的律文和教条束缚而得以更好地适应变化多姿的现实生活。离开案例的滋养,缺乏犯罪人的灵气和法官的睿智,制定法将很快枯萎僵死,就此而言期待可能性理论是这方面一个很好的范式。
二、期待可能性理论在中国刑法的现实存在
“法律不强人所难”,在中国刑法理论虽无期待可能性学说,但中国刑法典确实在很多方面已经体现了期待可能性理论。如刑法总则中第16条规定的意外事件;第17条至第19条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精神病人、醉酒的人及盲聋哑人犯罪的规定;第28条对胁从犯的规定。在刑法分则中,相关规定也明显体现出了期待可能性的精神。如刑法第134条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其犯罪主体并不包括被强迫违章作业的人员。显然这里也体现了期待可能性,因为被强迫违章作业的人员基于当时的具体条件和环境,法律上一般难以期待其违背直接主管人员的命令而不从事有关的违章行为,因而缺乏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不能对其进行刑事非难。[9]相关司法解释中也体现了这种精神,如根据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对于那些迫于生活困难、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而出卖亲生子女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在审判实践中,妇女因遭受自然灾害外流谋生而重婚的,因丈夫长期外出下落不明造成家庭生活严重困难而与他人结婚的,因强迫或包办婚姻或因婚后受虐待外逃而重婚的,因被拐卖后重婚的都不以重婚罪论处。
但现实中,立法者不可能将期待可能性理论整体性的直接而明确置入刑法典之中,在形式上对该理论完全法定化,所以说一些具备期待可能性的刑法事实在刑事立法中还不能为它找到合适的位置。其实,即便是期待可能性理论形成并完善的德日刑法典中也没有关于期待可能性的概念详尽论述。实际上,大多数的刑法理论不可能完整地体现在刑法典中,如刑法中的因果关系、错误论、犯罪目的与动机、罪数形态、过失责任中的信赖原则等都不可能在刑法典中找到一一对应的法条,甚至法典本身根本无意体现上述理论的精神。刑法典的主要阅读对象不仅仅是法官、检察官,更是亿万受其影响,为其瞩目的普通民众。对于这些普通民众,其关心的是在法典中有什么犯罪,对应着什么样的刑罚,如此而已。所以德国刑法学家鲁道夫·耶林曾讲:“立法者应该像哲学家一样思考,但像农夫一样说话。”[10]故此,抽象而晦涩的刑法理论根本就不可能是法典的主要内容。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很多具备期待可能性的刑法事实是超法规的,事实上,正因为期待可能性的超法规特征本身超出刑法典所能涵盖的范围,而行为人标准的判定几乎是一个人一个标准,适用主体极为宽泛,体现出极大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对此刑法典无法细致规定,期待可能性就因摆脱刑法典的束缚而使得该理论自身所具备的相当程度的开放性及灵活性,这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制定法的僵化与陈腐。在刑法条文中并无具体明晰的规定,需要法官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和对正义的把握,运用自己的智慧解释制定法,从而寻求在制定法条文之内,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之下,寻找处于事实最为对应的法律规范。因为,“法律人才的才能主要不在于认识制定法,而正是在于有能力能够在法律的——规范的观点之下分析生活事实。”[11] 任何审判活动都是法官在法律和生活事实之间进行眼光往返流转过程,在此,“未经加工的案件事实”逐渐转化为最终的案件事实,而未经加工的规范条文也转化为足够具体而适宜判断案件事实的规范形式,这个程序以提出法律问题开始,以对该问题做出终局答复而终结。”[12]
超法规的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具体适用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一方面,在刑法中缺乏明确而具体的规范指向,法官在错综复杂的法网中难以理出清晰的头绪;一方面法官又必须在对刑法的精神和宗旨作全面而详尽的把握上创造性地主动找法后做出自己的判断,不能因法律无明确的规定而推脱责任。对于刑事法官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具有相当的挑战性但却又必须面对的难题。但这也正是期待可能性理论自身的魅力所在,因为正是这种挑战性的困难面前,法官的才情和智慧才可得以激发,才会赋予刑法理论更为旺盛的进取的追求与渴望。
三、期待可能性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
以下仅以实践中的案例解读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具体适用。
某乡甲自然村和乙自然村之间因土地及灌溉用水问题存在长期历史纠纷。原乡长丙,德高望重,在其任职期间,对此妥善协调之下,两村人尚能和平相处。丙退离工作岗位返城居住后,两村关系急剧恶化。终于某天两村村民之间因争夺灌溉用水而导致小范围斗殴。甲村村民在斗殴中因在场人少吃亏,其村主任当夜召集村民开会,要通过与乙村的大规模械斗来解决纠纷,乙村也严阵以待。乡干部闻讯后干预无效,一场流血冲突即在眼前。丙闻讯后让其子连夜冒雨驾车赶往事发地点欲调解争端,途中反复责令其子加速行驶。在接近甲村时,因超速行驶,又因路面湿滑,其乘坐的轿车将路边行走的两位农民撞入沟中,两人经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丙及其子在车祸中也身负重伤。当地公安局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事故系因轿车车速过高引起,车方在该交通事故中应负全部责任。
本文认为,该交通事故不构成犯罪,该交通事故不是意外事件也非紧急避险,该交通事故行为应适用期待可能性理论而作无罪化处理。
(一)该交通事故不是意外事件
刑法中的意外事件规定在《刑法》第16条中, “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因此可见,刑法中的意外事件包括“不能抗拒”和“不能预见”两种情况。
就“不能抗拒”而言,通常是指行为人虽然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损害后果,但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排除或防止结果的发生。如在驾车行驶中,车辆遭他人枪击驾驶系统全部失灵而驾驶员无法操纵,之后车辆颠覆,造成重大伤亡的就属于“不能抗拒”。具体到本案中,丙及其子超速行驶完全出于意志上的自由,没有任何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因而不属于“不能抗拒”的情况。
就“不能预见”而言,通常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发生损害后果不但未预见,而且根据其实际能力和当时的具体条件,行为时也根本无法预见。如两个外地游客在雪地里玩耍,张某将李某推到在地,但李某却跌进一个被积雪覆盖的深井而死亡,由于风景区所设置的警示标志也被积雪覆盖,二人均未察觉危险,因此,张某对于李某的死亡就属“不能预见”。具体到本案中,丙及其子超速行驶完全能够预见到交通事故发生的极大可能,因此当然不属于“不能预见”的情况。
(二)该交通事故行为亦非紧急避险
根据《刑法》第21条规定,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害,不得已而采取的损害另一较小合法权益的行为。如在高速公路上,公交驾驶员为了避免和突然掉头逆向行驶的油罐车相撞,而驾车冲破护栏,造成乘客一定的伤亡,但却避免了两车相撞后发生爆炸的更为严重的后果,此种情况即属于紧急避险。
本案中的交通事故行为不属于紧急避险。紧急避险的本质在于,当两个合法权益相冲突时,又只能保全其中之一的紧急状态下,法律允许为了保全较大的权益而牺牲较小的权益。因此,紧急避险实质上是两种正当权益相互比较后的取舍,获得刑法中的正效益是其根本宗旨。但就本案而言,丙及其子在危害了他人的生命权益之后并未使村民大规模流血械斗得以避免,也就根本无正效益而言,因此也就不属于紧急避险。
(三)该交通事故行为应适用期待可能性理论而作无罪化处理
“面对具体的个案,永远也不可能放弃个人所感觉到的正义的活生生的声音;这种声音是永远不能被排除的。不管法是多么努力想把正义变为原则的制度,法也不可能缺少正义,相反,只有在正义里面,法才会变得生机勃勃。”[13]就本案而言,对于已经退休在家安享晚年的丙来说,没有任何法律甚至道德上的义务可以强迫其协调处理这场纠纷,对于丙子而言,其听从其父要求而深夜冒雨超速行驶,也不是在履行公民任何法定义务。二人甘心情愿在夜黑雨大的情况下冒着超速行驶,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这种危险的可能的受害者同时也包括父子二人在内),无非是出于一种正义感的驱使,即避免两村村民之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的发生。仅从正义的角度,正义的举措应当得到社会的尊重与承认,将父子二人锒铛入狱的结果是任何人都难以接受的。因此,就二人超速行驶行为动机而言,不可能期待其在可能导致重大人员伤亡的冲突发生在即的情况下,以正常速度赶到事发现场,因此就不具备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这一点和在执行抢救任务的救护车及执行灭火任务的消防车一样,超速行驶或是闯红灯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虽然表面上和交通管制法规相冲突,但实质上都是一种为求更大利益的适法行为,为此而产生的事故,不应受到法律的追究。
参考文献
[1] 洪福增:《期待可能性之理论与实践》,载《刑法总则论文集》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474页。
[2] [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第234、235页。
[3] 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21页。
[4] 黄丁全:《论刑事责任理论中的危机理论——期待可能性》,载《 刑事法评论(第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