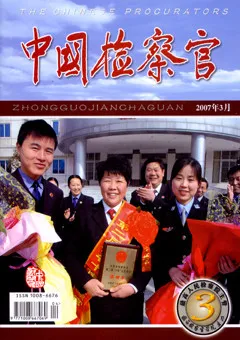邱兴华之死给我们留下哪些想象空间
随着陕西高院于去岁12月28日终审裁定维持邱兴华的死刑判决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对其执行枪决,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邱兴华案”,在程序上已经降下了帷幕。
但是,由于陕西高院没有充分考虑公众和媒体的强烈吁请,在没有给邱兴华进行精神病鉴定的情况下,就对其执行死刑,使得这起2006年中国最具“影响性”的案件所引发的争论、震荡乃至质疑,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以平息和消除。
尽管此时争论该不该对邱兴华进行精神病鉴定以及是否应对邱兴华执行死刑的问题,对于邱兴华本人而言,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对于这样一起具有“公共事件”性质的案件,学者们继续予以关注,并从各个角度分析和解读,还是非常必要的。或许,它们能为中国未来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提供一些基本思路。
事实上,学者们之所以关注该案,甚至吁请为邱兴华作精神病鉴定,并非仅仅是因为,学者比法官更悲天悯人,因而更在乎邱兴华的生死。在笔者看来,学者们所在乎的主要是,在邱兴华的二审辩护律师已经明确提出为其作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申请后,陕西高院到底应不应为邱兴华进行精神病鉴定。
然而,我们很遗憾地看到,陕西高院并没有认真对待并采纳辩护人的这一申请,反而,在最高院收回死刑核准权生效前四天,对邱兴华宣布判决并执行了死刑。给人的直觉是,陕西高院似乎在有意地防止该案进入即将由最高法院主导的死刑复核程序。
虽然,邱兴华是否被“错杀”,目前已经无法得到验证。而且,由于邱兴华已经被杀,这一案件或许将和历史上的很多案件一样,成为一桩永远的疑案。
虽然,邱兴华被“错杀”的可能性未必会很大,但是,由于陕西高院不同意辩护律师的这一申请,致使邱兴华获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并没有得到充分保障。
不仅如此,陕西高院不同意为邱兴华进行精神病鉴定还是违反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的。
因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6条的规定,辩护人申请调取新的证据,只要该证据涉及的证明内容可能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人民法院就应当同意该申请,并宣布延期审理。陕西高院可以不理会学者近年来呼吁的,并已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接受的程序公正理念,但其显然不可能不理会最高法院制作的具有“准立法”性质的司法解释。而我也绝不认为,陕西高院的法官们是由于没有注意到这一规定,才导致了“违法”。
合理的解释或许是,陕西高院“知道”有这么一个规定,但是考虑到其他诸多因素,只有不同意辩护律师提出的申请,才是惟一符合陕西高院“根本利益”的选择。至于陕西高院都考虑到了那些因素,作为局外人的我们显然无法知道。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能对本案有着巨大的想象或者推测的空间。
首先,笔者推测,陕西高院之所以不同意为邱兴华作精神病鉴定并在判决生效后立即对其执行死刑,不仅是因为,担心对邱兴华鉴定出精神病来,使得该案出现戏曲性的变化,从而承受巨大的压力,也不仅仅是因为,如果对邱兴华作司法精神病鉴定,将不得不为其支付一笔额外的费用,更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的存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简称《决定》)。《决定》将人民法院组织法的第13条修改为:“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而且,《决定》将于2007年1月1日起施行。也就是说,如果陕西高院同意为邱兴华作精神病鉴定,必然使本案拖延至2007年以后。如果邱兴华经鉴定确实患有精神病,自己将经受空前的考验;如果邱兴华经鉴定并非是精神病人或者并非是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那么,邱兴华恐怕仍然难逃一死。只不过,对邱兴华的死刑判决需要经过最高人民法院而已。而这对于陕西高院而言,同样是一个考验,甚至是一个比前者更大的考验。道理很明qjIwfbQmFI+KGF1TyzHRoc0v3ovIiMId3mxbwjLRVow=显,在中国的官场文化中,陕西高院宁愿自己面对风险和承受压力,也是不会和不敢“拖累”最高法院的。
其次,笔者推测,陕西高院在决定是否对邱兴华进行精神病鉴定的问题上,很有可能会请示最高法院。尽管,前不久,陕西高院根据最高法院的改革纲要,决定逐步取消个案请示。但是,面对着这样一起颇具“影响性”的案件,也面对这样一起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将舆论的焦点集中到最高法院的案件,陕西高院很可能会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并按照最高法院的意见办理。当然,这种个案请示的做法,绝非始于本案。事实上,它是我国法院内部一个长期盛行不衰的潜规则。笔者相信,只要中国司法的行政化得不到明显改变,只要中国司法实践中那种不正当的奖惩机制得不到根本的清理,这一潜规则就会通过各种方式发挥作用。
再次,退一步讲,即使陕西高院在该案的处理中并没有请求最高法院拿出意见,人们也可能会有如下的推测,那就是,陕西高院不同意为邱兴华作司法精神病鉴定,并在判决生效后立即对其执行死刑,是得到了最高法院“默认”的。甚至,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断,最高法院并不希望该案走到由自己核准的那一步。之所以如此推断,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其一,对于这样一起带有“公共事件”性质的血腥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不予以关注;其二,根据中国的司法现状,如果最高法院希望保障邱兴华获得做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权利,总是有途径的。而我想,最高法院之所以不希望由自己来复核此案,不仅是因为,最高法院碍于人手、司法资源,确实难以承受太多的死刑案件,更主要的是因为,面对这样一起备受关注的“影响性”案件,最高法院有理由担心,如果处理稍有不当,将使自己陷于非常被动的境地,也将使刚刚被最高法院收回并有待于观察其效果的死刑核准权,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而这恐怕是最高法院不愿面对的。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陕西高院之所以不同意对邱兴华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逆反心理”在作怪。我们知道,在邱兴华案进入二审程序,尤其是在二审开庭过程中辩护律师提出为邱兴华进行精神病鉴定的申请之后,该案从一起恶性刑事案件,迅速演变成为一个“公共事件”。不仅《南方周末》等颇具影响性的媒体刊载了精神病学鉴定权威关于邱兴华可能患有精神病的声音,而且还有不少法学专家也开始通过包括“上书”在内的各种方式,呼吁陕西高院同意为邱兴华做司法鉴定,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然而,这一切,在陕西高院看来,只不过是纯粹的“炒作”。陕西高院在处理邱兴华案时所表现出的专横,充分揭示出了,司法实务部门与理论界所存在的紧张关系即“相互瞧不起”。理论界基于社会责任时常批评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而司法实务部门却时常指责,理论界不懂中国国情,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甚至是对司法的干预!这是一个我们不愿看到,但却不得不在很长时间内面对的事实。
诸如此类的想象或者推测,笔者还可以提出一些。但是由于只是想象或者推测,既不一定确切,也没有必要求全责备。
逝者如斯!邱兴华案已经成为历史。
在新的一年,我们除了重温历史,更应该有新的期盼!
作为一个法治的信仰者,笔者真诚地期盼,在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之后,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判决能够降临祖国大地!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