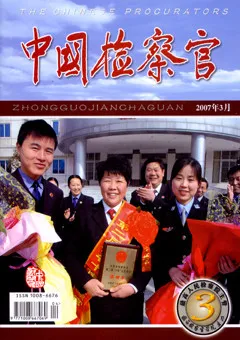商业贿赂罪与非罪实证分析
内容摘要:商业贿赂犯罪在司法适用上的疑难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商业贿赂罪与非罪的界定问题,二是商业贿赂此罪与彼罪的界定问题。检察实践中有关商业贿赂犯罪的典型案例,对罪与非罪的认定及犯罪的惩治等问题的研究是十分有价值的。
关键词:商业贿赂 罪与非罪 疑难问题 实证分析
商业贿赂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和利益的交易,一般情况下发生的各类商业贿赂犯罪容易把握。由于商业贿赂犯罪手段日益更新、犯罪方式千变万化,而现有《刑法》规定的稳定性和滞后性、司法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和不平衡性,势必会给具体法律适用的统一带来诸多障碍,尤其是对某些商业贿赂罪与非罪的界限难以厘清,其结果难免出现放纵犯罪分子或罪及无辜的现象。因此,立足本地检察机关近几年来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比较典型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例,对商业贿赂罪与非罪法律适用上的疑难问题展开探讨十分必要。
一、村干部在何种情况下构成受贿罪的主体
2000年4月,浙江义乌市稠城镇所辖的北苑管委会准备对原属石桥头村后于1998年被镇政府征用的D、E地块约47.6万立方米土地进行土石方平整。在确定施工单位过程中,石桥头村村民委员会主任吕某、村支书李某代表石头桥村多次向北苑管委会要求把该工程交由石桥头村施工。考虑到石桥头村本身不具备施工资质条件,为了减少施工过程中和石桥头村的矛盾,镇政府研究决定,同意北苑管委会将平整工程以议标形式承包给石桥头村指定的符合发包方要求的工程队施工,每立方单价为5.38元。吕某找到包工头王某,提出工程由王某做,但王某要上交石桥头村总工程款的3%作为“管理费”,并要付给吕某、李某每立方八角的“好处费”,王某同意。王某收到167.46万元工程款后,按约定给石桥头村“管理费”5万元,并送给吕某、李某“好处费”22.8万元(二人各分得11.3万元、11.5万元)。
2001年11月15日,义乌市检察院于对两犯罪嫌疑人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11月30日侦查终结并移送审查起诉。义乌市检察院鉴于检委会讨论意见有分歧,向金华市检察院请示。金华市检察院对吕某、李某的行为定性亦有分歧,遂向省检察院请示。省检察院检委会于2002年6月27日讨论决定,吕某、李某不构成犯罪。
本案的争议焦点: 吕某、李某是否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他们取得财物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一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吕某、李某利用了职务之便以及找工程队的便利,非法占有了村里与工程队共有的财物,构成职务侵占罪。另一种意见认为,两犯罪嫌疑人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下称“《解释》”)第(三)、(七)项之规定,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他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构成受贿罪。第三种意见认为,犯罪主体不符合《解释》之规定,不能认定为受贿罪,收受的款项不属于村里所有,也不能认定为职务侵占罪。
笔者赞成上述第三种意见。犯罪嫌疑人吕某、李某利用村长、村支书的职务之便,在选定工程队过程中索要财物22.8万元,社会危害性较大。但是,由于他们为北苑管委会选定工程队的行为不属于《解释》第(三)、(七)项规定的“国有土地的经营管理”和“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的情形,以议标的形式选定工程承包人员只是村自治事务。因此,吕某、李某不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不符合受贿罪的主体要件,不构成受贿罪。22.8万元也不是王某给村里的“管理费”,不是村里的财物。因此,二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也不构成职务侵占罪。一般而言,《解释》中的第一至第六项都比较好理解,也没有争议,关键是对第七项“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它行政管理工作”的理解。主要把握两点:一是“协助”表明是辅助性的工作,不是起主导作用;二是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并且是政府所委托的,不能把一切村委会的自治事务视为行政管理,如村委自己决定集资修路,村干部在工程承包中的贿赂行为就不能视为受贿罪主体。当然,如果是乡政府决定集资修路,委托村委管理,情况就不一样了。
二、“受委派人员”的身份认定
1999年至2004年,犯罪嫌疑人陈某在先后担任绍兴市电力局电气承装公司、绍兴电力设备成套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期间,利用管理有关电力设备成套产品采购方面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供销商所送的现金计105000元。本案已由绍兴市越城区检察院以受贿罪提起公诉,绍兴市越城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依法判处陈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成立,有期徒刑五年。检法两家对陈某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但对其罪名认定有分歧。检察院认为,电力局虽然未给陈某正式下过“委派”文件,但事实上陈某的组织人事关系一直在电力局,陈某也从未向电力局提出过辞职事宜,故陈属于电力局委派人员,应对陈应定受贿罪;法院认为,陈某任职公司纯粹是集体性质的“三产企业”,陈某并非电力局委派人员,电力局从未对陈某作出过委派决定,故不属于法定“受委派人员”。
这里涉及到我国《刑法》第93条第2款的正确理解,其关键要把握三点:一是何谓“委派”。委派就是委任和派遣,委派具有多种形式,可以是任命的方式,也可以是指派、提名、批准等方式。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经理必须由公司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委派就不能直接采用任命方式,只有向公司董事会提名,要求某人担任公司经理,受委派人员通常保留其原有的身分、级别或待遇。二是委派的去向单位。从实际案例看,受委派人员主要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为了行使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权而派驻到具有国有资产成分的中外合资企业、合作企业和国有控股或参股的股份制企业中的管理人员,但是,在特定情况下,也可以是委派到没有国有资产投入的非国有公司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因此,委派去向并非一定是有国有资产成分的单位。 [1]三是必须是从事公务,是代表委派单位在非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工作,如果只是去从事一般性业务技术或后勤服务性工作,则不是从事公务。可见,上述案例中的陈某是符合“受委派人员”身份的。因为其任职的绍兴电力设备公司是在特定情况下组建的“三产企业”,虽属于集体企业性质,但这些企业的主要负责人都是电力局党组首先提名的(每次都有局会议纪要记录),他们的组织人事关系都保留在电力局,这些人员也从未向电力局提出过辞职事宜,而且陈任职企业的主要业务还具有电力行业的垄断性,同电力局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对陈某以受贿罪名处理是适当的。
另外,涉及到公司、企业改制的经济案件也不少,办理难度较大,必须慎重处理。比较典型的情况是:国有公司改制为国有控股的股份制公司,原国有公司的全班人马都进了改制后的股份公司,那么,对这些人的身份如何确定呢?笔者认为,改制后只有符合国有公司委派特征的,或上级主管部门新任命的,并代表国有公司行使监督、管理国有资产的这部分人员,可以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其他包括中层部门经理或分公司经理等都不按国家工作人员对待。
三、普通医生能否成为受贿罪的主体
2006年6月至8月,绍兴市院侦查指挥中心在检察长的领导下,统一指挥,协调作战,运用谋略,案中找案,一举查获了绍兴市医疗卫生系统特大商业贿赂窝串案,先后共立案近20件,涉及犯罪嫌疑人20余人,涉案单位遍及绍兴市所辖5个县(市)的10余家医疗单位。对于国有医院的领导干部(包括医院正副院长、科室负责人等)利用职务之便收取医药或医疗器械供应商的回扣构成受贿罪在司法理论和实务界已达成共识,但对普通医生利用开处方或医疗器械使用选择权收取回扣是否构成受贿罪主体,却存在较大的争议。在刑法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1.否定说 [2]。其主要理由:一是根据我国《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才能构成受贿罪的主体,而刑法意义上的“公务”应当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人民团体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等等具有管理职能性质的活动,普通医生并不行使国家权力,只是提供技术或服务业务;二是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刑法》对此尚未有明确规定,普通医生收取回扣虽然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群众反映强烈,但是定罪量刑不能只看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群众的反映。2.肯定说 [3]。其主要理由:一是医药处方权或医疗器械使用权是医院管理权的必然延伸;二是处方行为和医疗手续行为虽然是技术性活动,但同时也是具有管理性,医生根据病人的实情有权选择不同类型的药品或医疗器械,医院行政部门都无法干涉;三是在法律后果上,处方行为或手续行为直接影响到各种不确定的医疗事故责任的承担,医生代表医院开处方或动手续,不仅是医生的职业要求,也是医生的职务行为;四是根据1998年的《执业医师法》第27条规定,医师不得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患者的财物或牟取不正当利益;第37条第10项又规定,实施上述行为又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见,从立法机关看,医生医疗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回扣行为构成受贿罪。
综上所述,普通医生利用处方权和医疗器械选择权收取回扣的行为定性在刑法理论界难以定论,说明对此类情况的犯罪认定还存在许多疑点,其根源是到目前为止没有明确的立法依据。因此,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碰到这种情况还是慎重为上。根据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在没有新的立法或立法解释的情况下,对普通医生收取回扣的行为以无罪处理为宜,但是可以提出检察建议,对这些人员以行政或纪律处分,这也符合当前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四、馈赠与行贿的法律界定
郭某任浙江洞头县农林水利局副局长期间主管水利资金和水利工程项目。1992年5月其女儿因重大交通事故被严重烧伤(全身烧伤面积达68%)。同年底,洞头县决定兴建风门水库,郭任该工程总指挥,省围海工程公司中标承建风门水库后,该公司总工程师闵某到洞头县检查工作,到郭家做客时见郭家女儿烧伤惨重,深表同情,回公司后向总经理和其他同事讲述该情况,经公司党委和工会集体研究决定,以工会名义送给郭10000元人民币,称帮助其女儿治病。1992年至1994年郭某女儿治病期间,该县东屏镇后寮村干部蔡某、大门镇仁前涂村林某、双朴乡大朴村苏某、二垄坑水库施工负责人朱某、小门镇盐场主郑某等,因水利工程有关事宜到郭家洽谈,见郭家女儿情状均表同情,先后以看望其女儿伤病的名义送给郭共计人民币11100元。
1997年1月10日,洞头县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郭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判决生效后,郭向温州中院申诉,1999年12月28日温州市中级法院指令洞头县法院再审。洞头县法院于2000年11月22日维持原判。郭不服提出上诉。温州中院认为,郭在其女儿遭受重大事故情况下,收受他人以看病为由所送钱物,具有人道主义捐助性质,属情节轻微,不宜以受贿罪论处,二审改判郭无罪。
本案的争议焦点: 郭本在其女儿遭受重大事故情况下,收受他人以看病为由所送钱物是受贿还是接受捐助? 一种意见认为,郭某身为县农林水利局副局长,利用其主管水利资金及水利工程项目的职务之便,多次收受他人以看望其女儿伤病为名所送的钱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另一种意见认为,郭在其女儿遭受重大交通事故的情况下收受省围海工程公司以该公司工会名义捐助的10000元,纯属基于人道主义的捐助,而不是贿赂。其余11100元虽然是有关当事人因曾受惠于或将有求于郭而送,但也难以排除人道主义的援助性质,考虑到本案具体情况,属情节轻微,不宜以受贿罪论处。
这里实质存在着馈赠与行贿行为的界定问题。商业贿赂方式往往有较大的隐蔽性,行贿人会打着“馈赠”的幌子,受贿人也往往辩解说收受贿赂是别人的赠送礼物,属于礼尚往来,因此,区别馈赠与行贿,是准确、有效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要求和保障。首先,馈赠和贿赂有本质上的区别:二者的主观目的不同。馈赠是行贿人自愿将自己的财物无偿地给予他人的行为,并且没有收买对方以使对方为自己谋利的目的,与受赠人的地位和职权无关。从实践看,馈赠的主要目的是基于人类自然怜悯和感情等因素,如亲朋好友为加深相互感情赠送礼物,赠送财物帮助危难之人渡过难关,赠送财物褒奖表彰某人的成功等等。行贿则不同,其目的是以财物贿赂对方,请求对方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双方存在着一种利益交易关系。其次,事务本质往往有其外在表现,在司法实践中还要综合考虑以下各种因素:(1)涉及财物的数量、价值大小;(2)交付财物的方式,是公开还是秘密;(3)行为人与相对人的身份、地位是否相称;(4)双方在平时的日常交往情况;(5)交付财物时或交付财物前后,有无提出相关利益要求;(6)交付财物前后,交付财物人有无从接受财物方那里得到利益好处,等等。
在本案中,被告人郭某身为县农林水利局副局长,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的条件,但是他同时也具有普通人的身份,有一个普通人所有的喜怒哀乐,同样会遇到意外的天灾人祸。所以,对本案中的郭某多次收受与水利资金、水利工程项目等事宜有关联的利害关系人所送钱物的行为,应该辩证地看待。郭是在女儿遭受重大交通事故的危难情境下所为,难以排除送钱人的行为具有人道主义的捐助性质,因为假如他是无职务身份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获得类似的捐助。因此,郭的上述行为与借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之机收受财物的行为明显有别,且涉案金额与郭家所受的危难基本适应,故不以受贿罪论处较为妥当。
五、名为“借”实为“受贿”的认定
2004年,绍兴县柯桥街道某村支部书记盛某,利用管理县政府下拨的土地拍卖款的职务之便,擅自将土地拍卖款1000多万元挪用给绍兴市某房地产公司使用。随后,盛某先后两次向该公司老板袁某借款共55万元,至案发日,盛某从未提起过还款之事。
在司法实践中,这种名为“借”实为“受贿”的现象出现的较多,每逢假日出游、购买房屋、出国考察、子女上学、结婚等机会,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便打着“借款”的名义,明目张胆地行索贿之实。一旦钱到手却再也不提“还款”之事。这种方式具有较大的迷惑性,有些还特地出示“借款凭证”以干扰侦查人员的视线。
如何区分这一虚假行为呢?当然,既不能仅凭当事人一面之辞来判定,也不能仅凭是否有书面凭证来判定,应该综合各种因素,把握商业贿赂的权钱交易的本质。具体可以考虑以下因素:(1)有无正当、合理的借款事由;(2)款项的去向;(3)双方平时关系如何、有无经济交往;(4)出借方是否要求国家工作人员为其谋取利益;(5)借款后是否有归还的意思表示及行为;(6)是否有归还的能力;(7)未归还的原因等。这样,可以避免那些狡猾的犯罪分子逃避法律的制裁。
因此,即使双方有书面凭证,也要综合考虑上述7种情形,作出综合的判断,如果能形成证据链,则可以认定为行贿受贿犯罪。
六、“事后受贿”的法律处理
吴某,原某国有公司总经理(副处级)。1995年5月3日,该国有公司能源化工处处长兼某实业有限公司承包人王某向吴某递交书面报告,提出新的承包经营方案,要求给予“倾斜政策”,对超额利润实行三七分成。吴某没有经过集体讨论,就私自同意王某的新的承包方案。王某在享受提高分成比例的“倾斜政策”后,当年多获取提成款18万元。1996年,王某又在“倾斜政策”关照下,多得提成款22万元。1997年春节前,王某为感谢吴某的关照,在其办公室送给吴某人民币12万元,吴某收下,没有退还。1998年3月,王某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查处。笔者认为,本案中吴某构成受贿罪,理由是受贿表现为权钱交易,收受财物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时间先后并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在刑法理论上,根据收受和索取财物的时间不同,可以把受贿分为事前受贿、事后受贿和离退休后受贿(即职后受贿)三种情况。对于事前受贿构成犯罪没有争议,而事后受贿和职后受贿的认定有不同的看法。
事后受贿又可分两种情况,即有约定的和无约定的。对事前有约定的受贿构成犯罪没有争议,在这里主要针对无约定的受贿行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是否具有受贿罪的故意,在事后受贿犯罪中,行为人明知对方给付财物的行为就是为了感谢自己先前为其谋取了利益而收受对方的财物,应作受贿罪处理。而且事后受贿是行为人已经为他人谋取了利益,相比事前受贿的性质更为严重。受贿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不管是先取财后用权还是先用权后取财都是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纯洁性的侵犯,都是权钱交易行为。依据我国《刑法》,受贿故意的内涵为权钱交易的故意,交易表明权与钱的联系,这种联系形成过程具有复杂性,以“约定”方式形成的联系,受贿故意通常是“即时”形成,而事先无约定的受贿并非不能形成联系过程,这种受贿故意往往呈“历时”形式。行为人明知利用职权为对方谋取了利益,事后接受对方所送的明显超过友情馈赠数量的财物时,根据一般的社会常识和生活经验推断,其内心不可能不与事先利用职权谋利行为建立联想,这种内心联系便形成了权钱交易的受贿故意。当然,这种内心联系需要通过司法推定来认定,司法人员要根据案情,遵循法理,并在司法良知的前提下慎重作出。
参考文献
[1] 参见原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长熊选国与审判员、法学博士苗有水《职务型经济犯罪疑难问题对话录如何认定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
[2] 参见《医生收受回扣不构成犯罪应完善受贿罪立法》,载《医药网》;《北大刑法教授认为医生收受回扣不构成受贿罪》,载《人民网-人民日报》2004年5月19日;等等。
[3] 参见高峰:《医生收受回扣能否构成受贿罪》,载《中辚法治网》2004年6月;曲新久:《开处方收受回扣就是受贿》,载《荆楚网》2004年6月3日;黎宏:《医生收受回扣应定受贿》,载《检察日报》2004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