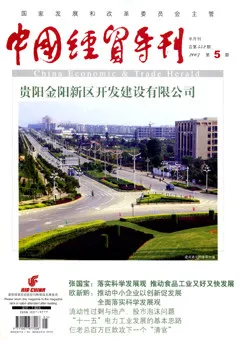怎样把握投资增幅的“合理”尺度?
2006年1—6月,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31.3%的高点。下半年,随着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的出台,投资增速开始下降,至11月底回落到26.6%。不少评论认为这标志着投资调控取得积极成效,也有评论认为增幅依然偏高。由此引出了一个老问题,究竟什么样的投资增幅是合理的、适度的呢?对此,我们很难看到正面的、直接的回答。
2007年投资宏观调控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依然是合理控制投资规模,实现投资的适度增长,同样的问题再一次摆在我们面前。
对此,人们往往从优化的角度考虑,希望能直接从理论推导上或从实践经验的总结中找到一个最优区间,然后以此作为调控的目标。然而,不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从历史经验总结的角度看,尽管经济学家们付出了不少努力,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但由于这个问题极其复杂,至今还是没有得到什么可真正付诸政策指导实践的成果。
怎么办?不妨两条腿走路。考虑到继续按传统思路直接探索最优区间的任务很难在短期内完成,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放弃以投资总量态势为调控出发点和归宿点的传统思路,将增长速度的“合理”或“适度”,定义为在一系列根据科学发展观设立的特定约束条件下(如物价水平、环境和生态保护、资源合理利用、劳动安全保护、产业政策等)形成的自然态势。其含义是,只要满足了这些约束条件,实现的投资增长态势就可以看作是通过“合理控制”实现的“适度增长”。这样,我们就从试图直接确定投资规模合理增长之“度”转到确定各相关约束条件之“度”。工作的重点就不再是争取实现某个(我们往往不知其所以然的)速度控制指标,而是力争实现那些可具体量化的约束目标或政策目标。显然,在新的思路中,本质性的要求是实现那些约束条件或政策目标,而我们所关注的投资总量调控,在某种程度上已还原为对整个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调控。于是,传统意义上的投资总量调控消失了,在新框架之下形成的投资增长态势,虽然只是一种作为自然结果的“副产品”,但它却是我们所定义的合理的、适度的增长态势。
按这样的方法去间接定义投资总量的“合理”与“适度”与否,人们可能还不大习惯。因为作为一种衡量标准,它毕竟与传统的数量型指标不同,不像我们所熟悉的通货膨胀水平约束目标或医学上的体温标准及血压标准那样直接和简明。特别是在这样的调控框架下,由于投资总量的形成是由一系列长短期因素共同决定的,其“合理”或“适度”的增长态势也必然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起伏不定,有较大的弹性,而且很有可能在某个时期出现“令人不安”的“高速”增长甚至“超高速”增长,那该怎么办?其实仔细想一想,如果我们真能免于通货膨胀的干扰,能享受大自然赋予我们的碧水蓝天,各项宝贵的自然资源能获得合理地利用,劳动者安全保护等约束条件均能得以实现,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投资总量,即使其规模比我们想象的合理值要大,增长速度比我们想象的适度值要快,又有什么不可以接受呢?在这样的一系列约束条件下,投资规模“失控”又能“失”到哪里去呢?
应特别强调的是,这些约束条件或政策目标的确定,应决定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而不是投资总量调控的要求,即独立于投资总量变动态势。不管投资总量的变化态势如何,这些约束条件或政策目标都不应轻易改变。虽然在近年来的投资宏观调控中,我们一直强调要严把信贷和土地两道闸门,但我们认为从本质上说那主要是针对通货膨胀和确保粮食安全的,而突出环境保护和资源合理利用则更是体现可持续发展原则的长期战略方针。如果把这些约束条件的设立与投资总量态势变化相联系,随投资总量态势变化而变化,投资增长快的时候就紧一点,投资增长慢的时候就搞一点通货膨胀,土地控制、环境保护和资源合理利用以至于劳动安全保护标准也放松一点,显然有违科学发展观的原则。更进一步分析,如果把这些约束条件的设立与投资总量态势变化相联系,随投资总量态势变化而变化,则人们还是会问,到底什么是“合理”和“适度”,到底应当在什么样的投资总量态势下采取调整措施呢?这样,我们又不得不面临寻找最优值和不知何为最优值、但又要使投资总量达到“合理”、“适度”水平的挑战,实际上再一次回到了本文的起点。
2006年,在“投资增长过快”的背景下,各地根据中央加强固定资产投资调控的决策对上半年新开工项目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背景是“投资增长过快”,但决策部门对这次清理却没有直接提出投资增长的数量控制指标,而只是从产业政策、项目审核、土地审批、环评审批、信贷政策、安全监管等六个方面提出了23项具体清理标准。这种只“重”约束条件的实现,“轻”实际增长速度的调控实践,应当可以看作是对“合理控制投资规模”之理、“适度增长”之度的一种新的把握,也体现了投资总量调控的一种新境界。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