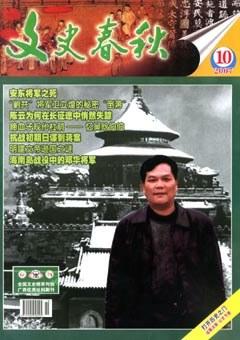啼血子规化杜鹃
万伯翱
以饰演马派《海瑞罢官》而著名的北京京剧院须生安云武,在电话里跟我说:“去年是批判吴晗先生《海瑞罢官》40周年,今年又是‘文革浩劫40年,吴先生遇害38周年;也是我的恩师马连良先生‘文革中因扮演海瑞,被江青多次点名而横遭加害致死40周年,您不写点什么?”
回忆起那血雨腥风的往事,至今仍是历历在目。那动乱悲惨的年代,是血与火的10年,刹时使我这花甲之年的心在滴血,握笔的手在发抖——
上世纪60年代初,由于父亲万里和北京市副市长、清华文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的明史专家吴晗同在北京市工作,因此我们两家常有来往,成了要好的友人。我知道吴晗伯伯是大作家,父亲与他关系非常融洽,因为父亲向来敬重有才干、有人品的知识分子。那个年代大家的日子都很清廉,吴晗伯伯一有了稿费收入,总是要请父亲等到全聚德、四川饭店和东来顺去吃饭。好像当时也只有吴晗这样的大教授和有工资以外收入的人才能请得起客(当时,他请一次客包括名贵的茅台酒在内大约是50元)。
他的《朱元璋传》、《投枪集》、《灯下集》等都曾签名赠送给父亲“指正”;他主编的“中华英雄人物历史丛书”,几十本一套,就送给我们万家的孩子们阅读。丛书文体流畅,又很有趣味,更兼历史唯物观,全书贯穿了中华民族历来崇尚的爱国爱民的英雄人物和廉政清官,所以我们5个孩子总是爱不释手,这使我们儿时的心灵受益匪浅。
在我的印象里,吴晗伯伯个子不高,当时也不过50多岁,身体已开始发福,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微微挺着肚子,很有一副大教授派头。他的夫人袁震阿姨是个长期病号,患有多种难治的病。30年代染上肺病,以后肝、胆、胰脏等都有疾病。她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董必武、陈潭秋、刘子通都是教过这位湖北才女的师范学校老师。她15岁时就写出了才华横溢、语言犀利、慷慨激昂的要求男女平等的《女子参政宣言》。25岁师范毕业,又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武大历史系,不久又考入了清华历史系,她当然久仰清华同届的高才生吴晗的大名。她27岁的时侯,吴晗到医院探望这位如林妹妹般柔弱的同学,他欣赏她的才气,又不讨厌她多愁多病的身心,就是不能生育,他也不在乎。不久,二人喜结秦晋之好,无论是和平的日子,还是暴风骤雨的日子,两人忠心不渝、相随为伴。
由于夫人袁震不能生育,他们在60年代初抱养了一对子女。认养时女儿吴晓彦才不过8岁,刚上小学;儿子吴彰仅仅4岁。吴晗夫妇对这一对认养的子女非常疼爱。我当年上中学时常看到,吴晗伯伯怀里抱着儿子,手拉着女儿在剧场和电影院,边看边耐心地为儿女们讲解,以增长他们的知识。他还经常苦口婆心地教育着他们,希望他们长大成人,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当然一对老人也是自娱自乐地享受着家庭的天伦之乐。
我还记得一次有幸执请柬去市委礼堂听他讲有关朱元璋的学术报告。当时我已考上高中,是怀着渴求知识的态度去听课。记得他用着明显带江浙口音的普通话,慷慨激昂,引经据典,历数朱元璋的残酷统治和暴行。在报告中他讲述了对蒋介石的痛恨,40年代他的那部名著《朱元璋传》是以朱元璋影射大独裁者“蒋总统”的,而且毫不留情地痛骂蒋是从“小流氓到暴君”。吴晗先生痛痛快快作完了报告,脸因激动略显微红,听者都已离席散去,我这个中学生却忙奔向主席台,向这位正扇着黑色折扇,身着米黄色整洁的纺绸短上衣、浅咖啡长裤的教授致少先队员的敬礼。他略愣了一下似乎是说,你这个娃娃怎么会来听这些?嘴里却说:“我教授不如你这个‘进士(近视)啊!”因为我戴着白色塑料框的近视眼镜。他还问我:“天这么热,游水了没有?我们小彦今天又带小彰去什刹海游水去了呢!等我有时间带他们去北戴河,像毛主席一样到大风大浪中去游水啊!”我看着激情未减的教授,觉得他真是一位好长者。要知道这位二十几岁就成为清华历史系著名学者的教授,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期间都积极参与过学生爱国、反帝、反蒋运动的热血青年,当年是多么帅气的一位英姿勃发、爱国爱民的青年啊!
谁也不知道毛泽东对这位正直的史学家所著《朱元璋传》的批示里埋伏的是赞扬还是批评,但最后两句的评价却是:“先生似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毛泽东当时是相当客气,最后一句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1954年修订此书后,吴又赠毛泽东“教正”,毛泽东又和他长谈过。当然千秋功罪,都由后人评说了。
实际上“文革”前,吴晗也常应父亲之邀到“养蜂夹道”和小平家中,同父亲和小平同志打桥牌。无论胜败多少总是很惬意,也常常令这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副市长(“文革”前还被选为全国青联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担任全国人大一、二、三届代表,同时还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激动和高兴。不过这正常的娱乐在“文革”中也成了追随“走资派”邓小平的罪行了。
1965年,父亲仍请他到北海旁边的“养蜂夹道”和小平同志一起打桥牌,那时报纸已开始批判“吴晗同志”了(刚开始文章还都加“同志”)。实际上打牌的人都处在暴风骤雨的前夕,只不过前奏风雨先打湿了吴晗而已。吴晗已无心思叫牌,心思不定,出牌也屡屡出错,他扶扶眼镜,扔下纸牌:“小平、万里同志,实在对不起,我哪里还有心思打牌啊——”小平同志仍不紧不忙地对他说:“教授同志,别这样长吁短叹,遇事不要太悲观,怕什么呢?老天还能塌下来吗?我今年也已过了花甲之年了,从参加革命到现在,也经历了不少风浪嘛,都熬过来了!经验不过是两条:第一不怕,第二乐观。教授呀,向远看,向前看,到头来历史总不会冤枉你这个好人呀——”父亲也不断开导这位实际上早已加入了党的老同志,只不过为了工作方便不大公开党员身份罢了。这无疑是一针强心剂,但邓小平和父亲都没料到后来有这么长时间的10年浩劫,又有如此大的杀伤力,他们都是自身不保,陷人重围,两人都是两次被打倒,根本没有一点能力顾及这位老牌友了。
显然吴晗伯伯的直接死因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应戏剧文化部门,尤其是四大须生之首的北京京剧团团长、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及市剧协等再三邀请,利用工作之余写了《海瑞罢官》京剧剧本。毛泽东在1959年4月5日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最后一天,特别提倡“海瑞精神”,要干部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吴先生在各方面支持鼓励催促的背景下,终于答应以史学家的思路,五易其稿完成了这部剧作。
在著名导演王雁先生认真执导下,马连良先生扮海瑞,裘盛戎先生扮反面人物、权倾一世的两朝首相徐阶,海瑞的贤母则由当时顶级老旦李多奎先生扮演。全戏剧情是:钦差大臣、握有尚方宝剑的八府巡案海瑞,发现了老相国徐阶包庇其子恶少徐瑛霸占农家良田、奸淫民女、勾结上下抗拒海瑞监察的事实。经过激烈较量,“海青天”动用尚方宝剑先斩后奏,斩了徐家恶少,后向嘉靖皇帝交印而被罢官。全场结束时马连良以一个如雕塑般捧印屹立不动的形象谢幕,给观众留下海瑞正气凛然而又两袖清风的难忘印象。
据有关资料表明,毛泽东在《海瑞罢官》公演以后,还亲自观看该剧,他老人家很高兴,接见了该剧主要演员,并请马连良等演员吃饭。席间,毛泽东余兴未减,还请他们演唱了片断,并说:“好戏呀,海瑞是好人啊!”至今海瑞的家乡海南岛海口市还有“海公祠堂”供游人凭吊,坟墓也修复完好。
“文革”前上海京剧院的名须生“麒麟童”——周信芳主演过的《海瑞上疏》(又名《海瑞骂皇帝》),比吴晗所写“罢官”剧本戏剧矛盾强烈而多一出戏:海瑞抬着棺材面君,在金銮殿上痛斥皇上的失误和罪过。大明朝过重的苛捐杂税使得农民“家净,家净(嘉靖嘉靖),家家户户都干干净净——无隔夜之粮了!”皇上面对阶下文武大臣,自然是大丢了面子,龙颜震怒。当时还是在这位徐阶重臣保全下,没有让海瑞进“棺材”,免他一死,而进了大狱。
实际上这样的戏剧效果比起“上疏”显然“瘟多”了,不是很抓人的戏。所以不是很好演,是需“名角来保戏的戏”。吴晗先生应该清楚海瑞指导思想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春秋孟子“以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从1965年10月以后,江青几次与姚文元、张春桥密谋,自此批判京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和声势从上海到北京愈演愈烈。
很显然,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为首的北京市委,一开始确实认为吴晗只不过是应北京剧协和马连良先生等再三之邀,写京剧剧本《海瑞罢官》,无论怎样上纲上线,充其量也不过是一部学术上有缺点错误或研究历史方法上有问题的剧本而已。本人和剧本不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而且和彭德怀元帅的罢官以及所谓的“彭、黄反党集团”根本联系不到一起。因为吴晗和彭帅一文一武,解放前一南一北,没有什么实际接触和联系,彼此仅是知道而已。但毛泽东在1966年春夏之交却又主观地强调指出:“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加上“四人帮”在上海居心叵测地推波助澜,在上海的《文汇报》上,通过笔杆子姚文元对一个剧本发动了大批判,吹响了“史无前例”的“文革”号角,终于通过批斗吴晗这只“替罪羔羊”又引出了邓拓、廖沫沙,进而直捣了所谓“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当然最后的战略大目标是打倒了一批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且是“斗倒斗臭,使之永世不得翻身”。
北京市委在“文革”中最早受到冲击,可怜吴晗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他万万没有想到一曲罢官戏,吴家却遭到了灭门之灾!
吴晗在北京市首当其冲被打成“黑帮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因而开始遭到造反派学生和“革命群众”的残酷批斗、无情摧残。他常常被戴上高帽、挂上牌、打上花脸,被强行摁头弯腰。可怜这位正直、认真并在解放后政治斗争中较为胆小怕事的大学者,却遭受到了晴天霹雳似地打击。全家被轰到丁家坑后,更是没有一天安宁,一家四口在风声鹤唳中惶惶不可终日。大中小学生纷至沓来,有的成群结伙,有的三五成群,被蒙蔽的“红卫兵”们个个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他们破门而入,折磨两位毫无抵抗能力的学者和两位年幼无知的孩子,实际上他们已经被打倒又被踏上一脚了,只有再束手就擒。
吴晗被拉到院校、街头,在振聋发聩的口号声:“坚决打倒三反分子吴晗!”“吴晗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批斗批臭”的喊叫声中度日如年。可怜他被殴打和摧残得遍体鳞伤、身心俱焚,他只能拖着伤残的身体回到家里,面对卧床的爱妻和年幼的儿女们说:“孩子们长大了会知道爸爸不是坏人,也没反党反毛主席,爸爸是冤枉的——”是的,心惊胆战的第二天,看到父亲同样又遭围攻,甚至遭受人们啐痰时,晓彦再也忍不住了,她冲出人群,抱住爸爸,声泪俱下:“要文斗不要武斗啊,这是毛主席的教导呀!你们不能再打我爸爸,你们回家打你们自己的爸爸去吧!”刹时,“红卫兵”惊呆了,武斗暂停了,晓彦拉起地下的“泥土老人”,一边拍打着爸爸身上的泥土,一边扶着爸爸一脚高一脚低地往家走,吴晗的血泪点点滴滴淌出:“好闺女、好女儿,爸爸今天能不被打死,全亏了你保护啦,我没白疼你们——”
同年的秋雨时分,父亲被改组后的以李雪峰为第一书记的北京新市委“留用”,其实“万书记”早已摇摇欲坠,难逃这场灾难。被江青在大会上点名后不久,这年12月4日晚上,两名造反派“红卫兵”头子越墙来到我们刚刚搬进的东单北鲜鱼巷胡同小小的四合院,打开院门,一群“红卫兵”蜂拥而入。惊弓之下的奶奶、妈妈和孩子们眼睁睁、哆嗦嗦地看着这群如狼似虎的学生们,一边抄家、一边抓人。父亲到底是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考验的职业革命家,临危不乱。他顶着紧催的“红卫兵”:“急慌什么?你们等着,得让我穿好衣服再走!”他估计要被不断拉到市里各处游斗、批判,因此在里面穿上了毛衣、毛裤和中山制服,外面又穿了件皮大衣。后来果然这件大衣“救了命”,在北京隆冬腊月天气中,工人体育场十几万人的批斗会上,如此这般的大批斗前后达50余场。久站的寒冷和拳打脚踢的“飞机式”都被这件皮大衣防护了三分!这些批斗场面(当然同台还有吴晗先生等被抓来陪斗),很快被制成“百丑图”在全国各地散发。我下放劳动的农场墙上也没有漏过,我立即被“勒令”不得再参加造反派“红卫兵”活动,整日让我揭发“黑帮老子”和“黑党委”。我从全国学习的下乡知青榜样和学习《毛选》先进青年职工,昼夜间变成了“黑党委黑藤上的小黑瓜,刘少奇下乡镀金的黑样板”。“百丑图”很快在莫斯科、巴黎等地出现,这引起了中央重视,因为都是武斗场面,世界哗然,最后被中央制止。其实,这在北京还可以,可怎能制止住全国多如牛毛的造反派各种小报的传抄张贴呢!
父亲被抓,一去就是三年。开始我们都不知道他被关在何处,也不知是死是活。北京的妈妈、弟妹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央和总理报告。后来我们被赶进了永外沙子口丁家坑。那时我还在河南农场下放劳动,当我收到弟弟用这一地址发来的信,心头“怦怦”乱跳,知道又搬家了,家里肯定又遭了殃。一年多后,北京卫戍区派吉普车到我们这个新家来要粮票、15块钱和父亲要读的《毛选》、马列著作和《鲁迅全集》等书籍,我们才知道他还在世,年过古稀的奶奶和我们心中就平静了许多。因为在当时,“红卫兵”打死人的事并不稀奇。
“反动学术权威”吴晗更有“火烧、油炸”之类大标语到处张贴。文革中造反派发明了这类灭绝人性的专用语言,不但用这些语言和满天飞的语录“文斗”,更有拳脚和棍棒加真枪实弹式的“武斗”。对待这位毫无抵抗力的教授学者,“喷气式”弯腰、烈日下暴晒、北风中受冻、脸上涂墨,更有学生为了表达自己对领袖的“无限忠心”和鲜明的爱憎,也就是说对“吴晗的无产阶级的深仇大恨”,对他进行各种残酷的、毫无人性的肉体折磨。学生们对吴晗自己不承认“自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自己的剧本是“大毒草”和“为彭德怀元帅翻案”的态度大怒,为了惩罚这位“死不悔改的三反分子”、“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黑帮”,就对站在板凳上的老人拳脚相加,从椅子上踹下来再打,真是“打倒了再踏上一只脚”,使之“永世不得翻身”了。结果,吴晗伯伯的眼镜被打落在地,身体多处被打伤。
我妈妈到楼下去看望他,他拇指和食指夹着恒大牌纸烟,边吸边老泪纵横地说:“我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呢!我做梦也不会呀,您想想,过去我是个穷教授,解放后党和政府才给了我洋房、汽车,还配备了司机、秘书、勤务员呀!我感谢都感谢不及,何谈反对呢——”妈妈很赞同他的心里话,两位老人再加上卧病在床的袁震,三人相拥而泣。放眼望望吴家四壁,除了书籍以外已没有任何多余之物了。据说,有一点节俭省下救命的稿费无处存放,就只能缝在被子里,除此家里已见不到什么值钱的东西了。而且,被抄了多次的家还常常有“红卫兵”冲入,借口批判吴晗,不断用架子车、自行车、小卡车随意拉走不计其数的各种珍贵图书,甚至包括毛泽东签名赠送“指正”的四卷“雄文”。
我们家也一再被“勒令搬家”,最后被轰进永外丁家坑一座五层楼的简易楼房。这是一座1958年“大跃进”时代“昨天订的计划今天翻一番,我们的一天要等于二十年”时代的产物,可以想像那是一座什么质量的楼房,恐怕现在早已不复存在了。我们家被分到五层,吴晗家被分在四层,没有电梯,每天上下楼,两家经常可以碰面。我们家除我在河南下乡劳动外,其余孩子都在北京读中学或大学,是二室为一个单元的结构。那时的房子几乎家家户户都没有什么“厅”,爸爸被抓走,4个弟弟妹妹加上妈妈和奶奶,6口人,怎么住呢?三四米长而狭小的厨房就不用了,让奶奶独住,妈妈和妹妹住一间,其余3个弟弟合住一房。做饭时,冬天在弟弟们那间卧室,夏天就搬到只有两三米的凉台上了。当然早没有了炊事员、勤务员,他们早就“造反”走了,做饭的事就由70多岁的奶奶和大家轮流帮厨。我们家人丁兴旺,大小伙子多,造反派来抄家,一看弟妹们个个怒目圆睁冷眼相待,也多少不敢像在吴晗家那样横行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