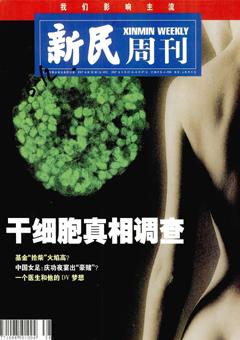火星文入侵
赵倩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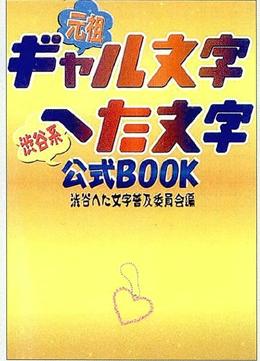
流行文化从来就具有对现有文化规范的颠覆性,火星文就标举着“特异”入侵到我们的语言文字规范里来。然而,一个新生事物的诞生、流传、确立,并不是看它的出现含有多少“创新”和“叛逆”,而是它本身具有多少合理性,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ㄗs:┽ぺ`過迲啲シㄝ孓ㄝ孓→恛鐿ぺぜ★鋧茬啲ギㄝ孓ㄝ孓╄→鉁鎴ジ~╲/~”这是天书,还是秘语?好端端一句“过去的回忆现在珍惜”在被转换成“火星文”后却成了这般模样。
8月上旬,火星文官方网站粉墨登场,目前注册会员超过2500名,同时在线人数最高达600多人,热闹非凡。然而对于其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大肆流行,有专家表示担忧,也有专家却称之为“对大人威权的无声抗议”。
火星文的起源
“ ﹊藍鳕餻〃”,这是北京某初二女生所使用的QQ昵称。粗粗看去,很容易把它当作是“蓝雪糕”的繁体字版,但偏偏“鳕”又不是“雪”的繁体。符号、繁体字、日文汉字加上错别字,是火星文的一大特色。
“我的名字好听吧?”“ ﹊藍鳕餻〃”对于自己的昵称似乎相当满意。但当记者问起什么是火星文,她先是回敬了三个问号,随即又说“不知道”。
台湾《火星文传奇》系列读物的责任编辑林佳慧解释道,火星文这种说法来自周星驰电影《功夫足球》中的一句台词:“地球是很危险的!你还是赶快返回火星吧!”从此,“火星人”一词便被台湾青年专门用来嘲讽不懂流行的人,而后来的“火星文”则是指普通人看不懂的语言文字。
根据维基百科的描述,火星文究竟是指何种语言,目前尚未有严谨的定义。但通常只要给人造成阅读和理解上的困难,就可算是火星文。如果从狭义来看,火星文就是所谓的“脑残体”。
“莓兲想埝祢巳宬儰⒈種漝惯”(每天想念你已成为一种习惯),将正常的汉字变形,大量使用与原字形似的别字,这就是典型的“脑残体”。
据火星文官方网站(www.huoxingwen.com)站长介绍,火星文起源于我国港澳台地区,起初随着仓颉、注音等繁体输入法出现,网友在打字时会频繁出现一些错别字,或为了图方便而故意打错字,但大家通常都能“心知肚明”,便渐渐默认使用。
随着网络的发展,大陆的一些论坛上开始出现台湾网民的留言,他们使用的繁体字、包括错字被当作时髦,引来了大陆网民的效仿。于是,一些追时髦的大陆网民也开始使用繁体字,并根据方言或自创的词语,进一步丰富了火星文的内容,这一现象在“85后”(1985年后出生)的年轻人中表现尤甚。
然而,火星文的怪异在使用和推广方面有天然劣势。普通的简体中文输入法往往按照字符使用频率排序,而火星文中所出现的冷僻字和繁体字通常都排在字符库的最后面。因此,在电脑上直接打出火星文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过这一难题阻挡不了年轻人对火星文的热情。从编写火星文对照表开始,使用者们逐渐开始自行设计软件,建立QQ群和论坛,打造着自己的精神家园。
“51QQshow”是目前最热门的火星文转换软件之一。比如在原文区中输入正常汉字“非主流个性魔法秀”,按下转换键,显示区就立马出现了“],◣◤°婔炷蓅嗰悻嚤琺莠.!'∞”,十分便捷好用。其编程者“ お本が郎/;d”告诉记者,其实设计这类软件非常容易,写起来没什么难度。
此外,一些颇有影响的网络游戏和即时通讯软件也成为了火星文使用者的聚集区。曾有人这样描述网络游戏“劲舞团”——脑残儿的模范集会场所,只因玩家的ID大部分都已被“火星化”。另有一些使用者则自发组建了QQ群和论坛,从头像到签名、从表情到资料,一概使用火星文书写。
字里行间的青年亚文化
火星文在两岸三地的流行并不偶然孤立,几年前日本流行的“Gal-moji”就与火星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三四年前,手机短信因其快速、隐秘和简单的特性被日本青少年推崇为一种普遍的交友方式,短信消费量大增。因此,日本手机往往都建有相当充实的字符库,包括拉丁字母、平假名、片假名、汉字和特殊符号。在此条件下,喜爱搞怪的日本女生间便产生了一种特殊语言,被称为“Gal-moji”,其中Gal即是“年轻女性”的意思。“Gal-moji”大量运用字符外形的隐喻,比如水瓶座的符号“﹖”,因形似波浪常会被当作“大海”的简写;又或者将原词拆开,如日语“愛してる”,在Gal文字中就可能变成“愛歹ヒ天流”。“死”在日语中和“し”同音,“天”和“て”同音,“る”和“流”同音,然后再把“死”字拆开成“歹”和“ヒ”,就成了上文的这种表现。
不愿规规矩矩地写字,新新人类们便竞相发挥想象力,扭曲正常文字,使其生动好玩起来,长此以往终于形成了“Gal-moji”文字体系。自编写翻译表开始,出版专书、组建小圈子,“Gal-moji”走过的路与火星文如出一辙。并且,这股风潮渐渐成为了日本年轻人的身份标志。从女高中生到男学生、大学生,以及20多岁的其他年轻人,看不懂Gal文字的人经常被耻笑为“欧巴桑”或“欧吉桑”,电视媒体也常以此为节目内容来测试你是否年轻。
同样,不懂“圈内语言”就被排斥在外的现象在火星文的传播中也有所体现。
2006年起,台湾华思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名为《火星文传奇》、《只i火星文》等一系列共5本图书,风靡一时。其作者火星喵喵自称“火星与地球人的混血儿”,“脑子里塞满稀奇古怪的创意”,“一天没挂网全身亿万细胞都会不爽”。
在面对媒体采访时,火星喵喵将出书目的归结为“研究文字创意”,但该书的简介中的一段文字却让人心生怀疑:“对于火星文,LKK(=老扣扣,闽南语老人家之意)带着毁国灭族的威胁口吻,呐喊着火星文的危害,却忽略这种创意思考,七、八年级可是爱不释手。”“ㄌㄎㄎ担心自己被世界遗忘,所以拼命阻挡火星文的流行,但是,你不听年轻人说什么,永远就不会听懂年轻人要讲什么!”
怀抱着这种心态的火星文使用者不在少数,其中大部分为90年代生人。一些小学生甚至坦言,他们用火星文就是为了“不让家长和老师看懂”。这样一来,即使小纸条落到了老师手里,只要不主动坦白,老师就抓不住任何把柄,私密空间便能得以保全。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严锋认为,火星文是年轻人不愿用前辈腔调说话的一种表现,而且“这种努力并非今天才有”。他解释道,“几年前电影《大话西游》红遍大江南北,遍地滥用‘大话句式,成为当时年轻人的标志,可以算是火星文初露端倪。再往前推,王朔掀起痞子文化,其小说《顽主》,骂人已用到反切的造词手法,正是‘前火星文。”“从老愤青王朔、中愤青周星驰,到现在的小愤青,属于青年的亚文化不断形成,一代代层出不穷。如果90后全无动静,不亮出自己的标签,那才奇怪。”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火星文所体现出的,是青年人对图像表达的回归。”长期从事符号学和青年文化研究的卢德平教授认为,进入分众传播时代,青年群体为了区别于成年群体的特征,在张扬个性方面做足了文章。火星文有其独特的符号系统,它流行于青年群体之间,进而成为青年亚文化的标志之一。
尽管作为整体从未被主流所接受,但卢德平教授相信,火星文中的有些要素还是有可能被主流吸纳。然而,“火星文不会改变我们的文化系统,区域性的语言只能在区域范围内传播,不可能为全部社会阶层所接受”。并且,“只要没有官方支持,流行文化很快就会逝去,对此我们应持开放态度”。
“围剿派”和“理解派”之争
火星文既已成为年轻人的“圈内语言”,自然再不会老老实实地呆在网络世界中。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在一个“7年级生”(即大陆所称的“80后”一代)300字的求职信中,出现了类似“Q”、“orz跪拜”、“3Q”等多达8处注音和表情符号,这样的“火星文求职信”让招聘方哭笑不得。
对此,台当局“劳委会职训局”向媒体抱怨现在的台湾地区年轻人求职不只“火星文”一箩筐,而且还错字连篇,明显是使用电脑打字太频繁所造成。
2006年,火星文猛地跳出网络,入侵到了台湾高中会考(台湾称为“大学学测”)的考卷上,摇身一变成了中文考试的改错题。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事件标志着火星文正式进入了公众视野。
因乱造生字、乱用同音替代等不规范用语现象,火星文引起了部分语言学家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火星文破坏了汉语的纯洁性和规范性,应予以否定。一些网友更是喊出了“围剿火星文”的口号,欲将之彻底封杀。
不同于“一杆子打死”的“围剿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勇更倾向于站到“理解派”一边。他将火星文看作是孩子们“对大人威权的无声抗议”,他认为“把小孩子逼成了地下工作者,大人们应该好好反省”,所以“十分理解和同情他们”。持相同看法的还有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严锋,“与其教训他们,不如从我们自己开始,作点实实在在的改变”。
在这场争论中,专家们各执一词,可似乎都无法摆脱“局外人”的尴尬身份。作为“圈内人士”,火星文官方网站站长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反对在正规场所使用‘火星文,但支持网络上使用。”
他解释道,火星文的存在迎合了当前部分网民的需要,供有“共同语言,能共同接受”的朋友交流,其实质是“追求好玩的错别字”。由于一个汉字往往可用多个火星字表达,因此火星文不可能成为一种独立语言。经过时间变迁和网络语言的“优胜劣汰”,它的命运很可能是“自生自灭”。这样的娱乐属于某种即兴幽默,没有必要对其进行恶毒的攻击。
年过七旬的《汉语大词典》编审金文明,在分析了火星文造字规律和使用情况后,同样表示不看好火星文的前途:“单从造字角度看,火星文没有固定的造字规则,而是大量采用同音代替。尽管这种方法在古代也有所运用,如‘女书,但现在已被淘汰。另一方面,由于辨识不易,即使是在有共同语言的好友之间使用火星文,都可能导致交流障碍。”而且火星文包含大量错别字,任意添加偏旁,故意拐弯抹角地表达意思,简不简、繁不繁、真不真、假不假,这些都是其流传的障碍,慢慢它就将被新的潮流所取代。
尚未踏入社会的“90后”们,长大后是否还能在自己的地盘里玩转火星文?赵勇认为,“大凡青年亚文化者,常常只会在某个阶段惹是生非。一旦亚文化的主人进入社会,亚文化本身就会自然而然地低眉顺眼、世故圆滑起来。”所以我们大可不必视火星文如“洪水猛兽”,如果将来,火星文中的一两个应用最终进入了我们的汉语规范里面,那也不过是这个“游戏”的幸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