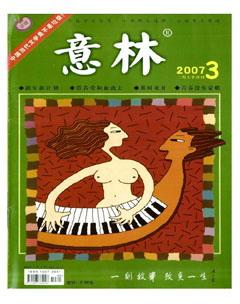只为那一瞬
那 海
当她身披薄如蝉翼的红舞衣,脚穿红舞鞋,在绚烂的舞台上尽情演绎着她的生命与自然的语言,她就如一朵美艳的红玫瑰,激情四溢,光彩照人。那一瞬,她是谁,她的年龄,她的国籍,以及关于她的所有跟凡俗尘世有关的东西,对诗人叶赛宁来说,已经毫无意义。
爱情就这样来了。甚至还没有准备好。
叶赛宁忧郁的蓝眼睛亮出了火花。那一道火花,自然不会划破长空,但至少顷刻间,也已将邓肯俘获。
那年,叶赛宁26岁,邓肯43岁。他们相差了整整17岁。
那个晚上,当俄罗斯的抒情诗人含情脉脉地看着被誉为“美国现代舞之母”的邓肯时,很快,翻译尴尬地发现,自己站在边上是多余的。叶赛宁与邓肯似乎根本不需要相同的语言。他朗诵自己的抒情诗给她听,邓肯看着这位年轻英俊忧郁的诗人,已经完全被迷住。她说,真好听,像音乐一样。
其实,他们根本听不懂对方说了什么。
但是,对于相爱的人来说,这重要吗?
你用你的语言,我用我的方式,我们始终会因灵魂的契合而交会。爱情通常如此,瞬间发生,刹那燃烧,毫无理由。
1922年,叶赛宁与邓肯结婚。
但是,这桩来自“红色王国”的诗人与西方舞后之间的婚姻,在旅行结婚途中就已闹得不可开交。他们生活习性居然有如此多的差异,他们的性格竟然也完全不同。
邓肯是一个率性的女子,她说,“我宁可全裸而舞,也不愿像当今的美国女人那样,半裸着还又假装矜持地在街上漫步。”她热情而快乐地活着,似乎全世界都会为她舞蹈。而叶赛宁总是忧郁地表达自己对生命的叹息,抑或生之惘然,他的性格中有着与生俱来的悲剧气质,就如他的诗歌,“生活,如今我已倦于希冀了。莫非你只是我的一场春梦?”
他们都不习惯彼此的行事方式。而想当初一个亲吻可以化解的疑虑或者困惑,如今仅凭肢体语言是无法让对方释然的。于是,激情过后,留下的就是爱情的碎片。无法捡拾,也难以拼凑。他们吵架打架,他们同样听不懂对方说了什么,但是很可惜,他们都读懂了对方眼中的不满与厌倦。
婚姻就是如此。它把一切华美的面纱撕下,所有的人都赤裸着面对这个烟火尘灰的生活。
而爱情或许是那样。所爱的都在彼岸。而当彼岸之物走向此岸,所有的距离都已消失,你看到的是真实,那么,最终无数人选择的是不愿面对。
“我见过世面,到处漂泊/我恋爱多次,受尽折磨/我之所以酗酒和耍无赖/只因比你好的人没见过。”叶赛宁对邓肯的表白是如此深情。但是,一切终究过去。1925年,叶赛宁在列宁格勒的一家旅馆自杀。这一年,他刚刚与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索菲娅·安德列夫娜结婚。他与她也是一见倾情。只是,婚后他才明白,这样的家庭生活他根本无法继续下去。
叶赛宁去世一年后,邓肯的长长的红围巾卷入开动的汽车轮子里,她曾经用它来跳《马赛曲》的围巾,如今却送她永远离开人世。
而叶赛宁曾经深爱过的另一个女子别尼斯拉夫斯卡娅,在叶赛宁死后不到一年,在他的坟前自杀。
叶赛宁的一生,爱情飘忽不定。他总是在瞬间轻而易举地爱上另一个人,那桩爱情或许能燃烧他瞬间的生命激情,但是,无法给他永久的安慰。他期待在爱情中找到精神与肉体的永久的栖息之地。
亦或许,这就是他的悲剧。
(玉冰心摘自《台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