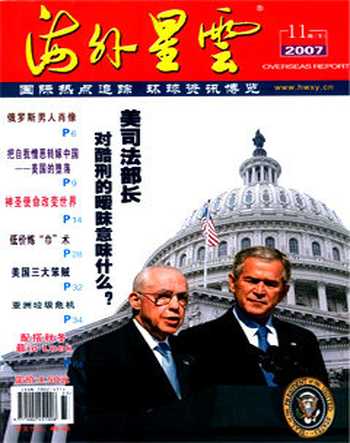作家张大春:义无反顾的文字工匠
卢智芳
不管喜欢他还是讨厌他,没有人能忽视张大春在台湾文坛上的光芒。《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的玩世不恭,《将军碑》的魔幻写实,《城邦暴力团》的武侠奇情,《大说谎家》的讥刺批判,《小说稗类》甚至展开创作者论述的文本新天地。张大春似乎永远有用不完的笔,难以预期他会抽出那一枝。然而当张大春谈起张大春,他的答案却是:“我就是一个工匠。”
张大春的黄金10年,有一种“不怕世界跟我不一样”的笃定。在这个文坛“鬼才”与“异数”的身上,看见一种简单的道理:人生的路,未必非得精细计算、多所探寻,“专注就能找到方向”。
也许25~35岁是一个决定未来职业的关键期,但那不是我的黄金10年。对我来讲,还没有到,还早得很。到现在我都还没有真正成熟,可能有些地方打磨得稍微好一点,但我觉得还没有真正发挥。
不过,这10年牵涉到我的几个阶段:一直到26岁拿到硕士学位,我都过着简单的学生生活。因为父母年纪比较大,我立定志愿不会出去念书,学校又没有博士班,所以我想我就是留在学校当教员。事实上也的确是,1986年,我30岁左右,就开始了前后两个学校、三个系、长达8~10年的教书生涯。
当兵回来后,我一方面在报社工作,一方面做电视节目,这是我社会参与最多的时候,但也最没有机会沉潜。做电视节目时,我每周读非常多的书,因为必须在节目里有很快的反应、讨论,可是这是一种过于快速的消化。我觉得我已经很了不起了,跟我同时期在节目里介绍书的人,都是读个大概、简介,但即使是那样,对于当时自己阅读的量和速度,我觉得还是自信太过。可以读得再慢一点、再少一点。
担任报社副刊主任半年多,我就辞掉了,因为我不能管人,给人家打考绩,我不会这个。但报社不让我走,我变成撰述委员,中间又做了四五个节目。
我一直没有大志向,到现在都没有,都是事情来了找上我。我们一家只有三口人,父亲有很稳定的收入,他曾对我讲过:“你将来考不上大学,找不到工作,在家,我养你也把你养到老。”维持一个简单甚至是简陋的普通生活,对我来说一点都没有后顾之忧。所以我一直到将近40岁,还是向父母拿零用钱过日子。
一直到我父亲76岁那年摔了一跤,家里很多事,我才必须自己去处理,在那之前,我连税都不报的。你可以说我运气好,也可以说我有点智障,生活上浑浑噩噩,要赚什么钱,达到什么地位,统统不知道。但是在所学、所事这件事情上,我却是义无反顾。
值得写的我才写,不消费自己
大学8个学期中,我5个学期第一名,考研究所也是第一名进去。我有本长篇小说叫《城邦暴力团》,序里面讲的读书的那个人就是我。我就是那样读书的,拿到一本书,有个问题不能解,到另外一本书里去找,找啊找就看下去,甚至忘记。原来要找什么,非常“接驳式”的阅读。你也不能讲是苦读,我读得挺乐的。
没有单一的作家是我的role model(典范),每个人都在影响我。就像从小学开始拿笔写字,一直到大学、当完兵,我只要看到谁的笔迹好看,就跟着他学。现在回头去想,大家的字都差本多,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着迷于其他同学的笔迹,但当时的我就像海绵一样,看到什么都不断吸收。
生活上没有压力,使我不必去设定人生在几岁时要赚到多少钱,我可以更纯粹去面对我的作品。当年我写《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一下卖了20多万本,到第2年,好朋友初安民(现任《印刻文学生活志》总编辑)约我出来,跟我说再写一本,我说不写。他说要找别人写大头妹,我说那不是糟蹋吗?才当场拿点菜的单子,抄写了12个回目,他一份,我一份,回家贴在台灯上,前后26天,12个工作天写完那本书。
这本书后来卖了16万本,过了一年,他又来找我,我就在书里把主角写死了(笑)。我只是不想让自己做一件有明确收益目标的事,我可以再写,但是不可以为了写而写。
对于创作,你认为完整了,就没有理由再出一样的东西。《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我妹妹》、《野孩子》,都是个别想好了,就这样干,《野孩子》实际写9天,《我妹妹》实际写12天,很短的时间完成后,不应该再被消费、复制。你现在看市场上很红的作家,没有一个不消费自己,不重复自己。那是他们的选择,我不是。
当我没有其它功利目的,生活就很准确地驱动我到必须从事的行业里去。我必须对故事情节、人物、使用的字、语言负责。选择我自己觉得最值得写的内容,而且东西要耐写,这是我从20多岁就知道的事。
专注当工匠,总有奇遇
我从不去想自己是个有风格的艺术大师或小说作家,我就是个工人。我一直认为工匠的技艺是一切事业的基础,只要眼睛里看到在工作中的人,专注工作的人,他们都会吸引我。尤其是操作工艺的时候,这些人的神情特别可爱。
在我人生里有非常多的例子,当我非常专心而努力地从事一件看起来没有用的事时,日后都会有用。
像我很喜欢李商隐的诗,一直觉得里面有玄机。研究生一年级时,有一天我遇见小说家高阳,他本来不理我的,但是我说,我认为李商隐有个小女朋友,而且可能跟他非常亲近。他一听完,我们就约吃饭,从那以后起我们几乎每周见面,变成忘年之交。
在我那个时代,高阳不见人的,他只跟张大干、台静农来往。后来他教我很多东西,考证、学问、史料的运用,我对李商隐的兴趣纯粹只是因为我觉得那诗里面有鬼,却因为一句话,结了一个缘。他带给我内在的充实、驱动,难以估计,开启我写历史小说的大门。
这些年重新写旧诗,写了大概2000多首,对我来说也是工艺品。有人问我要不要出诗集?没有这个打算。也许我会写到5万首,会印一堆给我的朋友看,但不会做成诗集。因为它就像日记一样,是我的手艺,我不知道目的是什么,反正就是要做。
结果突然今年7月来了一个活儿,吴兴国要我写京剧,当然我从小看京剧,但从来没想过我会去编剧本。正好写旧诗写很久了,写他的戏辞,就跟吃花生一样,很快,而且还比现在看到的京戏词更吻合于古典的格律。这是不期而然的收获。
天才要顶得住锻炼
我没有真正融入过这个社会,但是适应社会,或是社会对我的期待非我所愿,对我也从不构成情绪困扰。有一次我到《中国时报》去,遇见老朋友,他说你在博客那样写,心脏要很强。我没有心脏很强,因为我根本不在乎。个人遇到挫折,我到所受的训练里面去找解决之道。比方说写得不好,看法不够深入,那就不停地锻炼。
写作这东西,如果问我什么叫“大才”或“天才”,就是“不费力”。但是,天才另一个准确的解释,是经得起超乎常人的辛苦锻炼的这种人。我的工作里,也有这个部分。
(责任编辑/王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