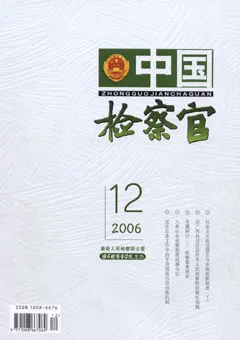人民监督员制度深化之设想
内容摘要:人民监督员试点工作是检察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对保障检察权特点是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正确行使,提高执法水平和案件质量,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作为新生制度尚有诸多缺陷,分析这些缺陷,探索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新路。
关键词:人民监督员 缺陷 深化
一、试行中的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缺陷——带有“体内”监督的痕迹
我们知道,人民监督员制度设计者的初衷是对检察权特别是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运行设定一个外部监督制度,以解决法律监督机关由“谁来监督”问题。为此,最高检察院印发了《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但是,从《规定》的内容和试点工作的实践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试行中的人民监督员制度确实带有“体内”监督的痕迹。
首先,从制定制度的主体看。人民监督员制度渊源于最高检察院的《规定》,也就是说,最高检察院是这一制度的制定者。尽管人民监督员制度作为一种规范性文件,它的制定有相应的宪法和法律根据;尽管根据立法机关的授权,高检院有制定检察工作内部规范性文件的权力;尽管高检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全国检察机关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但是,由于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最高检察机关制定的,因此,从它颁布实施那一刻起,就不能改变其检察机关内部制度的本质属性。
其次,从人民监督员的产生(任免)看。按照权力禀赋原理,任何权力的产生都有其产生的渊源,在法治国家,某种权力的产生或者源于宪法和法律的赋予,或者源自某些权力主体的授权或者委托。反之,某种权力一经产生,就要对其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法律及其制定者或者授权主体负责。根据《规定》的要求,人民监督员是各级人民检察院按照一定的程序聘任的,并由受聘检察院的检察长颁发证书。这一产生过程说明人民监督员的权力来源于检察院,来源于检察长,留给人的印象是被监督者自己请人来监督自己,被监督者授权别人来监督自己。这种制度无论是监督效果如何,都无法使人相信其彻底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最后,从人民监督员的日常联系管理和具体监督活动的组织上看。《规定》规定:“人民检察院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应当设立人民监督员办公室,作为人民监督员的办事机构。”作为人民监督员办事机构的人民监督员办公室由检察机关设立,并由检察机关管理,是当然的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规定》还规定,一旦“三类案件”和“五种情形”中需要人民监督员进行监督的事项出现时,由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在人民监督员名单中依照排序或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三名以上,总人数为单数的人民监督员参加案件监督”。很显然,这一规定是从防止参与监督活动的人民监督员“确定”上的随意性,进而保证监督活动的公正性而专门规定的程序。但是,由于人民监督员均为社会兼职,往往因工作繁忙出现不能按排序或抽取参加监督活动的情形,因此,监督员办公室必须邀请其他人民监督员参加监督活动。这样,很难避免随意性。同时,由于这一“确定”是由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实施的,因此,监督意见的公正性很难令人信服。
此外,《规定》中关于人民监督员的数额、免职、回避的规定等,也都不具备外部监督的特征。
综上,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基于检察制度现实而进行的制度设计,无论从制定制度的主体,还是从制度本身的内容,无一不体现着较强的内部性特征。另外,我国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活动是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一领导和各级人民检察院的组织下实施的,从根本上还是一个检察体系内的监督,谈不上真正意义的外部监督,因此,很难实现设计者预期的效果。
二、深化人民监督员试点工作的出路——由“体内”转向“体外”
众所周知,当代权力运行理论奉行监督和制约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监督体系往往是双重或者多重的。一般可分为内部监督也称制约和外部监督(在“三权分立”国家,权力外部监督也称权力制衡)。对权力的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互为补充、互为作用,二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严密的监督体系。考查我国现行检察制度,内部监督制约体系可谓完整严密,也不乏一般意义上的外部监督,这一点勿庸置言。所缺陷的是对自侦权有效的具体的监督程序,正是基于此,才有了人民监督员制度。但试点工作说明,定位于外部监督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却保留着内部监督的特征,因此,将人民监督员制度由体内转向体外就是一种既合规律又合目的必然。就是说,这种“转向”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一)实践根据
一是实践需要。如前所述,试行中的人民监督员制度使人们有理由怀疑外部的监督主体在内部制度下有内部化的可能,进而怀疑监督的效力及其权威性。检察机关试行人民监督员制度中的缺陷,是自身所不能克服的,这就必然要求寻找更为合适的一种外部监督体系。三年多的实践一方面证明检察机关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契合“权力监督权力”的要求、契合“公众参与管理”的要求、契合“实现公平正义”的要求,具有促进社会正义和进步的功能。另一方面也为“转向体外”积累了经验。
二是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希望和呼声。一些专家学者建议加强对人民监督员制度立法问题的研究,适时将人民监督员制度作为检察机关外部监督制度,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一些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建议将人民监督员制度纳入立法程序。同时提出,人民监督员的管理是一个值得研究和重视的问题,人民监督员作为一个机构,应当有自己的管理体系和层次。从“监督是旁观者的监视和督促”这个基本特性看,人民监督员理应独立于人民检察院之外。
三是人民陪审员制度为人民监督员工作提供了成功的典范。我国从1954年实行人民陪审制度以来,虽然几经波折,但五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人民陪审员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对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保证审判权全面正确反映人民的意愿,客观、公正地行使审判权,确保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全国人大《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的颁布与实施,在人员的产生、组织管理、培训、权利义务等方面做了明确规定,使人民陪审员制度真正成为由国家法律所确认的一项民主制度,是我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也为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深化提供了范例。
(二)法律根据
我国法律就人民对国家机关的监督作了明确规定。《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为了贯彻宪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工作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人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是宪法赋予人民的一项重要权利,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接受人民的监督是其法定义务。问题是,如何把宪法规定的权利义务变成现实的权力和义务,将人民监督员制度转向体外,为在检察制度中完成这种实现提供了可能。
(三)理论根据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使人民群众真正掌握监督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之一。列宁认为,法制的实现不仅需要运用国家权力对违法者制裁,而且首先要求在国家的权力结构中确立一种督促人们遵守法律、发现并追诉违法者的法律监督机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设想,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结构中,需要有一个监督其它国家机关和公民遵守法律的监督机关(检察机关),这个监督机关在履行监督权的同时,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显然,这里的人民群众监督指的是对监督机关进行的外部监督。因此,将人民监督员制度转向体外,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监督理论的。
那么,体外监督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笔者认为,体外监督区别于体内监督的本质特征有二:一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保持一定距离;二是监督者的活动具有独立性。试行中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有了前一个特征,因此,将人民监督员由体内转向体外的关键是使这一制度具有相对于检察机关的独立性。主要表现在:制度制定主体的独立性;人民监督员任免的独立性;人民监督员管理工作的独立性;监督活动的独立性。
三、人民监督员制度由体内转向体外的实现——立法和立法根据的提供
1.人民监督员制度由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制定或者通过,由此,这种制度才具有了合法性和一体执行的效力。
2.人民监督员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者人大常委会任命,这符合人民权力禀赋原理。
3.在人大常委会内设置人民监督员联络办公室,负责人民监督员的日常联系、培训和管理工作。
4.参加具体监督活动的人民监督员由人民监督员联络办公室依一定程序确定。
为了贯彻上述制度,在人民检察院内部设立的人民监督员办公室予以保留,做为与人民监督员联络办公室的联系和协助人民监督员开展监督活动的工作机构。
人民监督员制度作为一项全新的改革,其生命力在于不断地改进与完善,这也是以上设想的出发点所在。设想的实现一方面需要实践检验,另一方面也需要关注与争鸣,恳切盼望各位同仁的批评,愿与各位同仁携手在检察改革的实践中,探索求实,使其更趋完善,为保障检察权的正确行使发挥更大作用。
责任编辑:张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