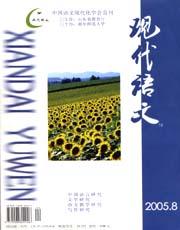评伍铁平先生的语言学评论风格
一、引言
20世纪末期的10多年间,北京师范大学伍铁平教授在国内学术刊物上连续发表了不少进行语言学批评的论文,并收集在1997年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和文化评论集》中。由于近几十年来,我国语言学界很少展开应有的学术评论,发表的评论文章也不是很多,在此情况下,伍铁平先生的《语言和文化评论集》的结集出版尤其引人注目。此书集中反映了他对目前国内语言学界存在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对学术界的不良风气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表达了净化学术空气和促进学术争鸣的良好愿望。他本人也因此被赞为“敢于净化学术风气的伍铁平教授”。这些评论文章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观点明确、条理清晰、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使人信服。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伍铁平先生扎实的学术功底、严谨的治学风格和为真理而斗争的勇气和胆量。这些不仅对我国语言学的发展有很好的监督、引导作用,对于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说也是十分有益的,因为伍铁平先生通过这些文章不厌其烦地纠正有些学者因基础知识不扎实而犯的错误,帮助我们辨清了许多容易混淆的概念,这一切都有利于我们的知识的巩固。何况真理愈辨愈明,这个过程加深了我们对这些知识的理解和把握。伍铁平先生向我们树立了严肃认真的学风的好榜样,但是他的语言学评论风格也并非无可指摘。
二、基础扎实、尊重科学
“尊重科学,用科学的语言理论做武器”是语言学评论的原则之一。
《语言理论》(彭泽润、李葆嘉主编,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对“语言学评论”是这样诠释的:
语言学评论是对语言使用、教育、研究中的现象进行理性的肯定和否定,或者进行表扬和批评,引导它们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显然,语言学评论是学术评论,而进行学术评论要求评论者必须有扎实的理论素质。这样才能在尊重科学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出科学的语言理论作为武器的威力。否则不仅无法说清问题,甚至还会混淆是非。
伍铁平先生就是凭借着深厚的理论素养在多篇论文中反复指出有些学者经常容易犯的“常识性错误”并予以纠正。
何谓“语言科学常识”?为何有些人会犯“常识性错误”?
语言科学常识就是指语言学概论涉及的理论问题,包括语言的性质、作用、结构、发展规律。例如:语言中的口语和书面语,文字和口语等是什么关系;五四运动为什么要废除文言文;为什么古代汉语的词以单音节为主,而现代汉语的词以双音节为主。这些都是关于语言的宏观知识。不是语言的微观知识。一般人都具有对一种语言的感性的微观认识,也就是会使用一种语言(包括方言),但是,他们不一定具有宏观的语言知识。
伍铁平先生就曾在《评鲁枢元著〈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学刍议〉中的若干语言学观点》一文中集中指出了鲁枢元所犯的十余种常识性错误:由于概念混乱导致的指称不明、混淆语言和文字、否认人类思维具有共性(混淆语言与思维)、混淆命名与概念、混淆字与词、混淆语言所表达的内容与语言这一表达手段的特点、混淆语言和对语言的研究,即语言学、由于缺乏对索绪尔的了解导致研究对象不明、对索绪尔评价错误、对汉语的错误判断、对语言和言语区别不明,等等。针对鲁枢元做出的辩驳,伍铁平还在后来的《要运用语言学理论必须首先掌握语言学理论》一文中进一步挖掘并剖析了鲁枢元所犯的语言学基础知识的错误。
同样,伍铁平先生也在《不要胡批索绪尔——评徐德江书文的一些错误》、《语言学和文字学的基本知识不能违背—评徐德江的三篇文章》、《学问不是“吹”出来的——再评徐德江〈当代语言文字理论的新构想〉》等论文中一一指出并纠正了徐德江所犯的错误。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赘述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文章中,伍铁平先生一再强调不能违背语言学和文字学的基础知识,并且他自己也是依靠牢固掌握科学的语言理论作为武器,才使他的评论文章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下面具体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一)鲁枢元在《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学刍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中说:
汉字是一种脱胎于图画的文字,它基于主体对于客体的直感的、形象的、整体的把握,而不象西方的拼音文字那样建立在理性的分析和规定之上的,因此汉语词汇的意义常常是浑沦混沌而模糊的。
伍铁平对这句话的评论是: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作者认为汉语词汇意义的特性是由文字决定的。这既违背了语言学的起码常识,又混淆了语言同文字这两种既有联系,但迥然不同的事情(疑为事物—引者)。我们都知道词汇意义(简称词义)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概括反映,并以一定的语音形式固定下来。词义的形成直接来源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语言的历史要比文字的历史长得多。根据人类学者的推测,人类大约在几十万到几百万年前就有了语言,而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的历史距今才三千多年。无疑在汉字产生之前,汉语就存在着,当然汉语词义也就产生了。怎么能说汉字造就了汉语词义的“混沌”和“模糊”呢?……
把汉字脱胎于图画作为有别于其它文字的特点也是不正确的。其实,世界上的文字追溯几乎都脱胎于图画,……
伍铁平的这两段话不仅一针见血地指出鲁枢元原话所隐含的错误,并透彻地剖析了语言和文字不是一回事、词汇意义不是文字造就的、汉字脱胎于图画不能作为区别于其他文字的特点,观点明确、条理清晰。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使人信服。
(二)对于徐德江的文章《汉字是高级的书面语言》(《汉字文化》1994年第4期)伍铁平这样评到:
不仅题目文理不通,而且其内容也完全错误,严重混淆了文字和语言。汉字是文字单位,怎么可能等于书面语言呢?……汉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它们既可以记录书面语言,也可以记录口头语体的语言(或称言语),如话剧和相声脚本的语言和文艺作品中的对话等,因此将文字等同于书面语言,违背了语言学和文字学的基本常识。
这段话清楚地阐明了文字不同于书面语。
以上两个例子充分说明了牢固掌握基础理论知识的重要性,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还有一个迫切性。
就让我们来看看《语言理论》是如何阐述词和字的异同的:
(1) 词、字都是语言结构系统的基本单位,都是最小又自由的第二级别的语言单位。这就是它们的相同特点,也是人们容易混淆它们的原因。(2)词是语言中最小的又自由的内容和形式结合的实体单位。词作为语言的实体单位,不仅要有形式还要有内容。例如汉语的“学习”,英语的“study”都是一个词。如果再分解,就失去了自由的特点,例如“习”。如果再扩大就会失去最小的特点,例如“学习汉语”。(3)字是文字中最小的又自由的视觉形式单位。字作为语言的视觉形式单位,不要求一定能够单独记录有意义的语素等单位,也不要求一定能够单独记录音素等声音单位。
此外,掌握文字和书面语、书面语和口语的关系理论也很重要:
(1)文字是书面语的形式。书面语和口语是语言的两种表现方式。(2)书面语是用来记录口语的,书面语要把口语作为基础,并且尽量和口语保持一致,不能像文言文那样长期脱离口语。
书面语长期严重脱离口语是违背语言发展规律的,因为语言的结构规律要求书面语与口语保持一致。
以上几个概念及相互间的区别是最最基本的语言科学常识,然而也是很多人常犯错误的知识点。只有具备了较高的理论素养才能做到真正的“尊重科学”。
三、治学严谨、目光敏锐
“学术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不能容纳任何虚假、随便的东西。”无论是进行科学研究,还是进行学术评论,学者都应该具有严格的科学态度。
“治学严谨”体现在伍铁平论文形式上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条有理:先摆出要评论的对象,然后运用科学的语言理论知识层层剖析,在摆事实、讲道理过程中推倒对方的立论,彰显自己的观点。例如:
索绪尔说“文字掩盖住了语言的面貌,文字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种伪装。”徐君(指徐德江—引者)据此批索绪尔,说他“用否定和憎恶的字眼来描述文字和文字的作用(《汉字文化》1993年第3期第10页)这真是典型的断章取义、为我所用。上引索绪尔话的后面紧接着一句徐君没有引用的十分重要的话:“我们从法语oiseau(鸟)这个词的拼写方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这里,口说的词(wazo)中没有一个音是用它固有的符号表示的;在这里,一点也看不出语言的音响形象(法文原文用的是image,当指词的音响形象,因为索绪尔认为词是由概念和音响形象构成的)了。”( 见《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第56页。我根据法文本对中译文作了个别修订。)由此可见,上引索绪尔的话根本不象徐君批评索绪尔所说的那样,在“诅咒”文字,“没有认识到”“文字的产生在人类历史中的巨大作用”,而是指法语这类拼音文字,由于语音的历史演变等原因,有时并不能反映语言的语音面貌这一客观事实。
在这里不难看出,只有作风严谨的人才会核查别人的引文,才会发现这个错误观点是断章取义的结果。伍铁平紧接着就摆出事实,用徐德江未引用的索绪尔的一句原话来反驳徐德江的观点,并作出正确解释。这样的治学风格值得敬佩和学习。
从内容上来看,伍铁平将他的严谨风格发挥到了淋漓尽致,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错误;哪怕是对自己的措辞也总是引经据典,设法将最精确的意思表达出来。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这里就仅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1)索绪尔将所指和能指的关系同劳动和工资的关系相比较,伍铁平指出这里的“劳动”应改为“劳动力”。
徐君说“索绪尔……根据劳动与工资的关系提出能指与所指等一系列语言学的概念”(《汉字文化》1993年第4期第18页,着重号是我加的)(着重号是伍铁平加的—引者),说明他既没有弄清索绪尔误将“劳动力”称作“劳动”,又不理解劳动力与工资密不可分的关系只能同能指和所指的关系相比较,徐君在索绪尔话的后面加一个“等”字,是不对的。……
(2)鲁枢元的《超越语言》中提到“卡西尔”这个人,伍铁平指出“此人德文原名Cassirer,应音译为卡西勒尔”。
《超越语言》第59页说,美国加州有雅那语(yana)和雅西方言(yahi)。我们没有查到后一个词。即使有,两处的Y 均应大写,因为英语的语言和方言名称第一个字母都应大写。
《超越语言》第201页将丹麦语Kirkeg°ard(教会庭院)误写作Kierkegoard,且鲁君将“教会庭院”等同于“庙堂”,也完全不对。
(3)伍铁平为了说明他所说的“沙文主义”一词用在学术问题上的确切含义,曾引用了五种语言词典上的解释:
我们这儿所说的“沙文主义”指的是西方部分语言中chauvinism(英语:沙文主义)常用的那种意义:“对自己国家过份(应为“过分”—引者)的、常常是盲目的赞赏”(英国《朗文当代英语词典》,1978年),“扭曲的、盲目的爱国主义”(H.C.Wyld 《通用英语词典》,伦敦,1956年),“没有根据地热衷于自己国家的荣誉”(《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1988年,北京);G.Wahrig编的《德语词典》(1927年)对Chauvinismus(沙文主义)的注释也是“对自己国家的过份(应为“过分”—引者)的热爱”;F.Palazzi编的《最新意大利语词典》(1939年)对sciovinismo(沙文主义)的注释也是“对自己国家的过份(应为“过分”——引者)的爱和自豪”。
以上的例子说明,进行学术研究和学术评论不仅需要严肃认真的态度,具有敏锐的眼光和严谨的作风也是十分必要的。伍铁平先生在这些方面表现得就很突出。
四、结论与思考
随着语言学形势发展的需要,语言学学术评论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它不仅能让人们了解学术理论是在真理与谬误的斗争中前进的,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对语言学的发展起监督和引导作用。因此有的学者呼吁“应该让语言学评论成为语言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议。
伍铁平先生的语言学评论在语言学界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在此就不赘述了。本文着重讨论的是伍铁平先生的语言学评论风格的主要特点—尊重科学、重视基础知识、严肃认真的态度和严谨的作风等,以及这些特点对语言学初学者的启发作用和指导意义。但是必须指出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而且我本文认为也是不可取的,那就是在学术批评中给对方扣上诸如“骗子”、“伪科学”之类的帽子,这样的做法不仅使学术争鸣的空气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而且也会对初学者造成负面影响。学术观点的分歧本来是学术研究的正常现象,进行学术争论的双方都应该心平气和、宽容大度。善意、客观的学术评论有助于推动学术进展,而如果在评论中加入了不必要的个人的感情因素就会使学术研究走样。因为任何真理都是具有相对性的,所以我们应该尊重学术分歧,努力推动真理的进步。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方光焘的一位朋友曾引用笛卡尔《方法论》中的一段话来提醒方光焘:
经院式的辩论,后来不曾把从前未发见的真理,阐述明白;因为在这种情形下,人人都竭力求胜,都想把似是而非的理论,说得极其中听,从不想在问题的两造,衡量衡量真正的理由。至于平素为我自己鼓吹的人们,当然狃于成见,在后来也不能判断得宜了。
面对这样的提醒,方光焘是这样回应的:
我很感谢这位朋友对我的警告。但愿我们的辩论,不会流于经院式。我虽然明知自己是没有能力去把从前未发见的真理阐述明白,可是我总可以竭力克制“求胜”的心理,时时预备着屈膝在真理面前。我也希望世禄先生此后不要“狃于成见”,那就可以“判断得宜”了。
方光焘这种忠实于真理、谦虚冷静的态度令我印象深刻。同样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在他的语言学评论文章中他就没有给与自己学术论点有分歧的对手戴过什么帽子。只有采取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学术观点的分歧才能有益于学术研究的发展。
至于语言学评论者是否始终要以挑剔的眼光、批判的态度对待所有的语言现象、语言研究中的观点和行为这个问题,我本文的看法是认为:如果在单纯属于语言学领域的范围内,那评论者一定得一丝不苟、严肃认真、不轻易放过任何可疑的细节;然而目前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越来越多,并且大多数还处在起步阶段,这样的形势对研究人员的跨学科科研能力的要求是相当高的,当然相应的扎实的理论素质是必不可少的。从现阶段来看,跨学科研究人员也正处在探索阶段,由于理论基础不够扎实而犯的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觉得本文认为跨学科研究人员的勇气和胆量以及探索精神是可敬可佩的,况且学术研究需要宽容,原先某个领域的学者们应当怀着一颗宽容的心去帮助他们,在给他们指出错误以后给予引导和鼓励,而不是批评和打击。这样才会有利于新兴学科的发展,同时也能给原来的学科注入新鲜的血液、带来生机勃勃的活力。
(何晓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