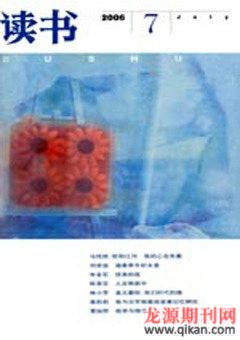一件“国家一级文物”的流传
钱里月
读书献疑
不久前,笔者撰文(《证,就要证得准,证得实——读〈荻岛静夫日记〉》,《读书》二○○六年二期)指出,《荻岛静夫日记》(以下简称《荻》)作为一个译本,在译文质量上存在着严重问题。
本来,话也只能说到这儿,因为看不到更多的日记手稿原件。但问题的严重性却在于,这个不可靠的译本已经成了专家学者乃至媒体讨论“荻岛静夫日记”的底本,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各种相关的疑问。例如,荻岛静夫的日记“怎么会留在中国?”荻岛静夫本人是否还活着?如果活着的话是否可以找到?
二○○五年九月六日“人民网”以《荻岛静夫日记来源仍是谜》为题,发表署名甘丹的报道,介绍了专家学者的质疑:
在前日的研讨会上,现代文物鉴定专家阮家新、沈庆林、万冈都认定了《荻岛静夫日记》的真实性,但同时也提出了几点疑问。阮家新在发言中质疑:“荻岛静夫安全回国了,那日记怎么会留在中国?最初是什么人保存着这本日记的?这些问题我们都还希望能进一步了解清楚,如果能找到荻岛静夫的后人那就更好了。”
这则报道中提到的“研讨会”,是指《荻》出版后举行的一个座谈会,据新华社九月一日报道,“来自博物馆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中日关系研究中心的十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座谈会(张琴、海明威:《侵华日本兵战地日记出版引起史学界高度关注》)。而上文中出现的阮家新、沈庆林、万冈三位,据说就是直接参加过荻岛静夫日记手稿和影集的鉴定,并将其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现代文物专家。
“十多位专家、学者”的座谈讨论,其所依据的底本自然是译文质量有问题的中译本,这一点无须多说。只就专家在会上提出的“日记怎么会留在中国”这一质疑而论,其前提当然是“日记在中国被发现”这一认识。
那么,这种认识是怎样形成的呢?当然是根据中译本。在《荻》的封底,有一行具有认定性的广告断语:“日记一九五○年起保留在中国”。很显然,这是出版者加上去的。附于书后的《编后的话》亦就此向读者呼吁:“一九五○年日记就收藏在中国,收藏者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得到的这些东西?他与荻岛静夫是什么关系?荻岛静夫还活着吗?能否找到他的后代或家人?请给我们提供线索!”(中译本,236页)而出版者的“日记一九五○年起保留在中国”这一认识又来自哪里呢?回答是“今年五月,樊建川透露:他收集到一套完整的日军日记并配有照片,而这套日记从一九五○年起就收藏在中国……”(234页)樊建川即日记手稿的现在的收藏者,据樊本人说:“二○○四年初夏的一个傍晚,……一个电话打进来,……对方是一位……文物商人,这次传来的消息是:天津的一位王姓先生,藏有一套日军的日记。”(1页)“按照日记上附条的记录,是一位叫做王襄的人,一九五○年收藏。”(2页)由此可见,日记在中国被发现这一信息,不论是口头还是文字,最早是来自樊建川。这里不妨将其概括为“一九五○年天津王襄”说。这一说成了从出版者到专家学者,再到媒体的认定“日记一九五○年起保留在中国”的基本依据。樊也在《寻找荻岛静夫》一文中,基于这一前提提出了饶有兴味的历史悬念:
在许多个独处的夜晚,我总想荻岛静夫是否活着?是否能够寻访到他?是否能找到他的后代或家人?如果他知道,他当年记下的日记全套留在了中国会有何感受?
还有那个最初日记收藏人——王襄:“他是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得到这些东西?他与荻岛静夫是什么关系?这个过程又有多少故事……”(3页)很显然,专家的“怎么会留在中国”的质疑也与这些悬想直接相关,并且基于荻岛静夫日记手稿“全套留在了中国”这一前提。
随着主流媒体和专家的声音被各种大众传媒的大量复制和放大,荻岛静夫日记“怎么会留在中国”之谜,一时间成了铺天盖地的疑问,如《财经时报》就以《荻岛静夫日记悬疑重重》为题做了整版报道(二○○五年九月二日),并且还对“王襄是谁?”这一“新悬念”做了一大段追踪介绍,甚至还附了“王襄”的照片。由该版报道可知,“王襄是谁?”也是上述座谈会上的议题之一;而在日记是在中国被首次发现和出版的意义上,“专家们都极力推荐该书要在日本出版日文版”,“让日本人民通过这个书教育自己”。——笔者非常赞同专家们的这种意见,并且在上一篇文章中指出,尤其在译文不可靠的情况下,更应该直接出版影印版,以使读者和研究者能够获得足以为凭据的原始资料。
悬疑重重,固然会使读书步入佳境,却也令人无法释然。
上一篇谈中译本译文质量的稿子写完后,笔者又利用业余时间做了一点调查,并且得到了有关上述疑问的重要答案。不过,其中有一条却几乎使笔者的头脑发生混乱。
“怎么会呢?”——看到出版物原件,笔者简直不能相信,一套“一九五○年起保留在中国”,当然也是“在中国被发现”,并且已经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又以中文版的形式“首次出版”的日本兵日记手稿,在距今十七年前就已经在日本出版过!
这是一套十六开本红色硬壳的精装书,分上、中、下三卷,题目叫做《捛壇偺帇慄》(可直译为《追忆的视线》,以下简称《追》),其出版信息为:田中常雄(恒夫)编,有限会社僆乕儖僾儔僀僯儞僌平成元年——即一九八九年七月十日出版发行,页码数为上卷471页,中卷274页,下卷297页,定价二万日元。
现在,这套书就摆在笔者的案头。“荻岛静夫日记”以“阵中日记”为题收在下卷第71—274页。由于是在日本本国出版,当然是地地道道的日文版;日记内容无需翻译,编者只需把日文手稿文字检读出来再变成铅字就可以了。因此,应该说这是到目前为止和荻岛静夫日记手稿内容最接近的出版物了。
而且,荻岛静夫“阵中日记”作为史料,也已经进入知识的生产过程,开始出现在一些日本学者的专著和论文当中。就是说,“荻岛静夫日记”在日本不仅有,而且也正在被使用。
《追》中的“阵中日记”的底本,当然是来自荻岛静夫的日记手稿,据编者言,手稿原物直接借自荻岛家族,而在下卷72页还附有七本日记本的照片,即为手稿的保存形态。
这令人越发糊涂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荻》封二也有七本日记的照片,当视为中译本的底本。假设中译本照片上的日记本和日本版照片上的日记本为同一物体,那么,“一九五○年起就由天津王襄保留在中国”的日记手稿,怎么会在一九八九年被拿回到日本出版呢?而且怎么会在日本出版以后,又于二○○四年神差鬼使地在中国“被”发现呢?笔者一时还真无法为日记手稿的这种“往返”于中日之间的旅行理出一个合理的头绪。于是,脑子乱了。
看来,要想拨乱反正,也就必须恢复到一种符合常识的思维,即只能在两种相互排斥的“事实”当中选择一种。《追》里收入荻岛静夫“阵中日记”一事,无疑令在中国的被“发现”和“首出”之说十分难堪,然而,却是个不争的既成事实,在这一事实面前,关于日记手稿的所谓“一九五○年天津王襄”说,就只能当作一个假定的“事实”来看。另据上引《财经时报》的报道说,寻找原始收藏者和“来源”,已经成了“史学家、文物专家等人的心病”,“樊建川还特意找到将《荻》转给自己的天津某文物商人,也许是出于行规,也许出于年代的久远,除了日记本附条上的记录,新的消息没有太多”云。尽管国法与“行规”孰轻孰重不言自明,而手稿的经手者既已牵动举国,亦有义务做出解释,不过既然不易再获得新的消息,也便无法强求。但唯其如此,也就在加重说明“一九五○年天津王襄”这一假定“事实”的脆弱易碎。
比较合乎情理的解释,只能是日记手稿在日本出版之后被转卖到中国——如果建川博物馆收藏的那套手稿是真品的话。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追》里的荻岛静夫“阵中日记”就是根据荻岛家族提供的日记手稿直接检读和编辑的。《追》是一套以收集战殁者的遗书、日记和书信为主的资料集,其凡例称,“本书以战殁者个人为中心,由略历、记录、战斗状况、日志、书信、诗歌和遗族的回忆等构成”;另据前言和后记介绍,该资料集征集了在“日俄”、“日中”(即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三场战争中“加住地区”(旧东京府南多摩郡加住村——今东京都八王子市宫下町)一百五十二名战殁者的资料,全部直接来自遗族或亲属,资料的收集花费了“三年半”的时间,编辑又费时“一年有余”才最后完成。这就意味着荻岛静夫日记手稿至少在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九年这段时间内还在遗族和编辑者手中。
收录在《追》下卷第71—274页的“阵中日记”,是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到一九四○年三月十七日的日记。这期间的时间总长为九百三十八天,实有日记篇数为八百五十八篇,与之相对照,中译本只译了其中的五百一十七篇,约占日记总篇数的60%。其各年度的天数、篇数以及中译本的实收篇数的对照如下表。如果把已经翻译的各篇当中所存在的大量“漏译”也计算在内,那么中译本实际翻译的内容将不到日本版“阵中日记”的50%。如上所言,倘若假定中译本与日本版所依据日记手稿相同,那么则可以知道,中译本当中所缺少的一半左右的内容,是中译本出版者有意删削的。本来,有选择地节译也未为不可,但不能使事实的本来面目发生扭曲和改变,而且更应该对删削情况做出明确的说明。但是,没有。这就无形中大大降低了中译本作为重要史证资料的公信度和可靠性。事实上,这种不加注明的胡乱删节已经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即误导包括专家在内的中译本读者相信日记手稿“全套留在了中国”。
比如,中译本只截止到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刚好是荻岛静夫所在部队要从战场上撤下来回国的日子。见于中译本的最后两篇日记,记于南昌,时间分别是十二月二日和七日。前者记“尾家部队长对集中起来的归国者作最后的告别训话”,后者记“对部队转移行动的种种细节做了准备工作”——如果到此为止,只读这些,那么当然会留下种种悬念,包括日记的去向和作者的命运。然而,如果参照《追》里的“阵中日记”,便可知道作者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一日随队撤离南昌,一路经过九江、安庆、芜湖、南京,于当月二十八日抵上海,一九四○年一月十二日在上海登船,一月十八日抵东京湾,二十日登陆进入习志野兵营,在此后的两个月中,部队解散,本人于三月十七日复员,由东京站乘车回到老家宫下村。
三月七日晴宫下
今天终于迎来了返回故乡加住的日子。自己本于生还无所期,不知是神佛的保佑还是惠蒙后方的赤诚而得以长命至今。晴空万里,春意盎然。午后零时半,由东京站上车,一路奔八王子站驶进。车窗外呈现的郊外风景,充满春天的活力,仿佛在迎接我的归来。两点抵达改建过的八王子车站……
——此后是作者受到全村人的出迎并参加“归还报告式”的情形,“下午五点回到了我眷恋的家”。这段话译自“阵中日记”的最后一篇,明明白白告诉人们,不仅日记作者荻岛静夫归国返乡,而且日记也跟着他一起回去了——并且一直带在身边,也一直记到返乡的这一天。倘若读了这些文字,读者还会再有日记手稿“全套留在了中国”的悬想吗?还会令专家再提出“荻岛静夫安全回国了,那日记怎么会留在中国”这样的疑问吗?笔者不能理解中译本究竟是出自何种理由完整地删掉了最后一百零一天的日记,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它在客观上导致了一个事实真相的被掩盖,即日记手稿当初并没留在中国,而是被荻岛静夫本人带回国了。
如此说来,中译本《荻》作为史证资料的不足为凭,还不仅是已经指出过的译文上的漏译、误译和语不达意等缺欠所导致的“史实变形”,更重要的是对原始资料的任意斧削所导致的“事实丧失”。而正是基于这个“史实变形”和“事实丧失”的译本,出版机构、专家学者、新闻媒体正在展开讨论,并且把读者引导到“日记怎么会留在中国”这样一个本来并不存在的徒劳的问题上来。
还有,“荻岛静夫是否活着?是否能寻访到他?”——既然已经成了一个面向全社会的大疑问,也就有必要根据现成的资料做一下介绍。在《追》资料集里,除“阵中日记”外,下卷275—291页《战殁者名簿》(见282页)和上卷305—311页都对荻岛静夫有记录。“荻岛静夫”既已名列“战殁者”之列,所以他“是否活着”的悬念便不复存在。试译其生平简介如下(括号中公历年为笔者所注):
明治四十四(1911)年三月二十一日出生于当时东京府南多摩郡加住宫下五九七番地(现在为八王子市宫下町五九七番地),父光吉,母忒舞(音,原文テウ),为三男一女兄弟四人中之长男。
加住寻常高等小学毕业后在家务农。
昭和十二(1937)年八月,支那事变战争之际,二十六岁应征入伍,编入加纳部队东部一六部队。
昭和十五(1940)年三月复员。
昭和十九(1944)年一月,太平洋战争时,三十二岁再次应征入伍。
昭和十九年七月十八日下午三时,在马里亚纳群岛之塞班岛的战斗中战死,享年三十三岁。(上卷,305页)
又,从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一日给妻子的信(资料集里附有原件照片)中知道,妻子名“绢”(音绮奴,原文きぬ),有一女儿名克子。
如上所述,当已经确知日记手稿当初就没留在中国,所谓“一九五○年天津王襄”说又可能是文物商人的天方夜谭,而荻岛静夫的下落也找到了,那么,伴随着中译本《荻》的出版所发生的历史“悬念”便不复存在。然而,尘埃落定才发现,一些真实的疑问才刚刚呈现出来,并且需要认真研究和回答。
比如,假设日本版与中译本所依据日记手稿为同物,那么日记手稿一九八九年在日本出版以后,是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流传到中国的呢?既然是经了文物商人之手,那么它被转卖而来的可能性也就非常之大,而最清楚这其中过节的亦莫过于经手的文物商人。倘是纯私人藏品,他人也不必过问那些生意上的秘密,但既已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相关人士便有义务也有责任对来龙去脉给予澄清和说明。根据国家文物局二○○三年五月十三日发布的《近现代一级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试行)》,其第三条规定“一级文物必须是经过科学考证,确为原件、源流具有确凿依据”的文物,哪怕就凭这一条,讲清手稿“源流”,拿出“确凿证据”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其次,这也涉及到文物的评定问题。笔者愿意相信第一流文物鉴定专家的睿智与慧眼,但还是希望能够看到关于荻岛静夫日记手稿的鉴定报告,笔者想知道专家们究竟根据什么样的标准,又是如何鉴定的,想知道其“科学考证”的过程和怎样“确为原件”的经过,当然也更想知道手稿源流所具有的“确凿依据”。然而,至今还看不到这种报告,只有媒体上传来的评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喜讯。
最后,笔者还有两点疑问。第一,荻岛静夫到底使用什么样的书写工具写日记?实际目睹过中译本所依据日记稿本的四个人都说是“用铅笔”,如收藏者樊建川说,“他用铅笔头,记了近二十万字日记”(中译本,3页);译者袁定基说日记的“书写的工具往往又用的是铅笔”(同上,233页);责任编辑脚印说日记“内文用铅笔头工整记下”(同上,235页);第四个是《财经时报》记者,他也目睹了“锁在樊建川公司楼下财务部的保险柜里”的日记原件:“纸张已微微泛黄,用铅笔写的小楷密密麻麻……”(《六十八年前的日军日记被发现 日本兵成为杀人机器》二○○五年八月十三日)。就是说,“用铅笔”这一点,被上述四人异口同声地证实。但与之相对照的是,日本版的编者田中常雄却在“编者按”里明确说,书写工具是“用钢笔”:“七册笔记本,用钢笔记得一丝不苟。因日月长久亦有墨水洇散而无法判读的部分。这样的地方留作空白,请读者根据前后文来理解。”(《追》下卷,272页)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呢?
第二,从上面介绍过的《追》所使用的七本日记本的照片(该资料集里没附,也没有提到中译本所见影集)看,其排列为左四右三,左为封底,上端横印英文“memorandum”(记事本)的字样清晰可见,前面说过,中译本封二也有七本日记本的照片,但其中所见三本日记的封底,类似西文字母的文字却都印在下端,而且究竟为何字母,也无法判读。所以最好还是能请可以接触到原物的人再翻看一下其余四本的封底,看看是不是也有把“memorandum”清晰地横印在封底上端的本子,如果有的话,当然再好不过,但如果没有,也就要再次发出相同的疑问了: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呢?
以上两点疑问,使笔者担心日本版《追》和中译本《荻》所依据的日记稿本是否相同的物体,倘若相同,那么也就无非意味着同一物体在六十八年间的往返于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旅行:当初是由荻岛静夫把它们带到中国,又从中国把它们带回日本,收藏在家里,在他死后也一直由后人来保管,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某一天应资料编者之请求,其后人才把手稿拿出来,《荻》出版之后,手稿当然又归还给了荻岛家,而这之后究竟又怎样到了中国的文物市场也的确是个谜了。不过,这是就两者“物体相同”的意义而言,倘若物体是两样东西,那可就糟了,其“国际玩笑”的程度也就远非日本版《追》里的“阵中日记”所带来的尴尬可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