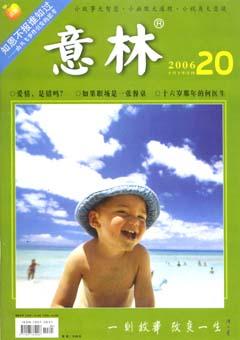狗娘
江 薛
乡下人养狗,狗崽子都不愿在附近抱,因为往往前脚抱回家,狗娘后脚就找来把狗崽子领回去了。我爷爷家与我家隔了一道山梁一条马路,虽说站在屋后的山冈上叫得应,但弯弯曲曲的太远,所以,我很顺利地把旺喜抱回了家,而且让它在这儿扎下了根。
旺喜是我给我的狗取的名,它娘叫旺财。旺财到爷爷家一年多了,这是头一回当娘,就了不起地生下了五只狗崽子。我跟旺财也很熟,我去上学,非得从爷爷屋前过,能不熟?可抱旺喜那阵儿,它对我特不友好,一直警惕地守在窝边。后来还是爷爷把它骗进屋,堵好狗洞关好门,我才有机会抱上旺喜急匆匆地奔回了家。
听爷爷讲,我把旺喜抱走后,旺财非常愤怒,白天不吃不喝,也不喂其他狗崽子,四处寻找,晚上光听它在窝里哀号,仿佛呼唤旺喜一样。第二天上学,我就远远地躲着旺财,心慌慌地不敢看它。
旺喜跟它娘一样,雪白雪白的身子,半根杂毛也没有,我在日记里这样形容它:要是它有翅膀,飞到空中,你一定以为它就是一团白云呢!
抱回家时,旺喜刚满月不久,能自己吃一点儿饭。我只给它煮粥吃,生怕硬饭把它噎着。有肉吃,我就先放在自己嘴里,使劲嚼个稀烂,再吐到它碗里。看它吃完,我赶紧把碗拿过来。洗得跟自己的碗一样干净。那一段,我的手指都不知充当过多少回奶头呢!我没有兄弟姐妹,放学回家一个人很没劲,有了旺喜,日子就过得有意思多了。
转眼半年过去,我从五年级升到六年级,我的旺喜呢,都不知什么时候长的,腿赶上我的手臂一般粗了。骑在它背上,它居然能坚持一会儿。而它的娘旺财就可怜多了。我把旺喜抱走后,不久爷爷那儿又去了几个人,说想买走剩下的几只。爷爷问买去干吗,他们说养大了看果园子。爷爷就松了手。可没想到,那几个人把四只狗崽子弄到饭馆里,吃了顿乳狗火锅。辛辛苦苦生下五个孩子,如今一个也不在身边。旺财一下子就瘦了一圈,然后像患上忧郁症似的,谁也不爱理,蜷在一个地方就是一天。
立秋过后,不能下池塘玩水,我就带着旺喜去屋后的山上玩。山挺高的,顶上有一块废弃的地,草铺成一张绿毯,是玩耍的好地方。
放下书包,我和旺喜就往上冲。我每次都跑不过它,等我看到它,它都自个儿在草地上打滚儿玩上了。站在高处,举目四顾,天地在远远的地方重叠,那儿有云在飘,仿佛仙境一般。尤其是夕阳西下,照得我和旺喜红光满面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好伟大好伟大。我喊,旺喜呀旺喜呀!天就跟着喊旺喜呀旺喜呀,地就跟着喊旺喜呀旺喜呀。旺喜也叫,旺喜一叫,天也跟着叫地也跟着叫,然后山脚下四面村子里的狗就嚷成一片,嚷得那缕缕炊烟左一扭右一扭的。
一次,我喊累了,躺在地上看云,旁边的旺喜突然低低地吼起来。我坐起来看,嘿,雪白雪白的身子,这不是爷爷家的旺财吗?它也看到了我,轻轻摇着尾巴,慢慢地靠近。警告不见效,旺喜恼怒起来,龇起牙狠狠地叫。旺财一惊,目光停在旺喜身上,站住了。我就笑起来,搂住旺喜的脖子说:“叫什么叫,不认识了?它是你娘。”
第二天,我放学回家,居然不见了旺喜。我急得要死,使劲喊,一会儿,就看见旺喜箭一样从后山奔下来,到面前,却是两团白色。另一只是旺财。它们俨然相熟已久的模样,嬉闹着,你咬我的脖子我咬你的腿,一只烂袜子成了它们的宠物,争抢个没完没了。
十月,秋天的味道就浓了。那天黄昏,我爷爷告诉我,旺喜死了。我呆住了,我不相信,但爷爷是不会骗我的。我飞一般跑回家,院子里静得可怕。我看到了旺喜,它静静地侧躺在墙角,四肢僵硬地伸展开,嘴角淌的血已凝成一条长长的蚯蚓。旺喜!我的心被一只锤子敲得咚咚响,眼泪成了六月突降的雨。
——旺喜在马路上闲逛,一辆汽车飞驰过来,旺喜就真的飞了,像云一样。
晚上,父亲回来了。他看着我红肿的眼睛,骂我没出息,然后伸手拎了拎旺喜,说:“有好几十斤呢,宰了炖肉吃。”我一听,弹簧一样蹦起来,抢过旺喜,愤怒地瞪住他:“你把我也杀了炖肉吃吧!”
父亲被我吓住了。后来,我把旺喜埋在了后山的草地里。它喜欢那个有草有风的地方。旺喜死后,我的那些快乐也随之而去了,倒是旺财天天来我家。我不知道它是否知道旺喜死了,反正我不会再理它。每次来,它与我对视的时候,我的目光都含着刀子。一个母亲,竟然没看好自己的孩子,这算什么好母亲?我恨,我就捡起脚边的石头,奋力地砸过去。
旺财总是把自己放得远远的,没想过要靠近的模样,站在那儿,看看我,看看山,又看看我看看山,然后转身而去。只是步子一天比一天缓慢,背部的肋骨一天比一天清晰了。
那是个星期六的下午,爷爷跑到家里问我旺财有没有来过,说一天一夜不见它了。我淡淡地说旺财没来过,有两天没来了。爷爷遗憾地去别处寻找了,我不打算帮忙去找,我觉得它这是活该。只是旺财的失踪,又让我想起了旺喜。心里一动,便去爬山,要去看看旺喜。旺喜又在我脑子里活了过来,雪白雪白的身体,吐着红红的舌头,在我前面蹦跳着。眼前白影晃动,我笑了,赶紧加快步子和它比赛。
近了,白影越来越清晰。我站在小小的土堆前,使劲地揉揉眼,肯定了面前真的有一团白色——那是旺财。它死了,白色的毛被风吹出一个个漩涡。它蜷曲着,四肢僵硬地伸出去,却将那个土堆揽在怀里。它的眼睛轻轻地闭着,安详得仿佛不曾死去,却像在让自己的孩子吃奶。
泪,再一次如泉般涌了出来。
(林玄生摘自《百花园·小小说原创版》200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