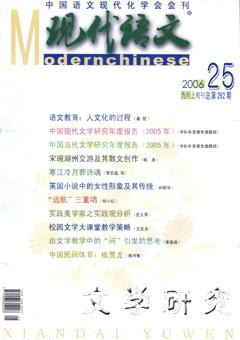寒江冷月葬诗魂
李宗超 韩 霞
一、孤独的个体生命意识
有人曾经这么说过,“法国的诗人死于醉酒,俄罗斯的诗人死于决斗,中国的诗人死于穷困潦倒。”这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事实。中国现当代的白话诗人多如浩瀚的星河,璀璨夺目,但多年来,白话诗的早期开创者之一朱湘却好像是一颗被世人遗忘在天边的星星,没有人注意,如同他生前一样的寂寞,死后也是寂寞的。
在学贯中西的诗人朱湘身上,体现出了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碰撞。既有东方孤独的名士风情,又有西方酒神精神的迷醉。狂与狷是中国古代的名士风情,在朱湘的身上也能找得到影子,如倪婷婷在《“名士气”:传统文人气度在“ 五四”的投影》中所提到的“中国千百年名士风流的佳话, 就行为方式而论, 不出乎放达和隐逸两种, 名士们也大致分为两类:‘狂与‘狷。‘五四作家的‘名士气 也不外乎‘放达与‘隐逸的范畴”。[1]不过,在诗人朱湘的身上,体现的更多的是中国文人的孤独意识,朱湘似乎永远不会放达,但是很狂,他穷困潦倒和人生坎坷,却贫贱不移;他没法像中国传统的文人那样饮酒赋诗,自得其乐,却有着中国文人的骨气。在朱湘的诗歌中,我们更能深刻体会到的是那种孤独和无法排遣的阴气。在诗人的内心世界里,他自己永远是孤独的局外人,但实际上,在他那些反映内心苦闷孤独的作品背后,是对寂寞的恐惧,他害怕被人们抛弃在一边,害怕被主潮逐到边缘,但是由于他性格的不合时宜和孤僻的行为使人们很难接近他,难以了解到他的内心世界,其知音自然就更少了。就像柳无忌所说:“不懂得子沅的人时常奚落他,以为他是怪,是孤傲;熟识子沅的人,方知道子沅为人是这样的清高,这样的直爽,对待友人的心情是这样的忠厚。但是诗人都不免有一样吃亏的地方,太易感触,太多猜疑了。诗人对于情绪和外界的事物特别易受刺激,对于一点不如意的事故,也容易生出不快的情感,这种做人的特质也许就是子沅不能做成事业的致命伤吧。”[2]罗念生也说,“朱湘性情孤僻,傲慢,暴烈,倔强,表面上冷若冰霜,内心里却是一团火。”[3]
他在诗中经常写道自己孤独的苦闷,借用诗歌表达自己的心情,如发表于1922年的《地丁》“地丁仰头柔声和我说:/‘别摘我,我求你!/我颈儿很低,/我花儿又细,/我岂是为你花瓶开的?”[4]如王国维所说的“一切物语皆情语”。这里,朱湘借《地丁》又何尝不是表现了他的孤独的心境。又如《寄一多基相》中“我是一个惫殆的游人,/蹒跚于旷漠之原中,/我形影孤单,挣扎前进,/伴我的有秋暮的悲风。//你们的心是一间茅屋,/小窗中射出友谊的红光;/我的灵魂呵,火边歇下罢,/这正是你长眠的地方。”[5]其实,这里正是诗人自己的写照,他是一个永远飘泊的孤独的灵魂。但是,正是在这孤独与寂寞里,诗人的灵感才被激发出来,在寂寞里闪出激情的火花,他在《石门集》高呼:“我的诗神,我放弃了世界,世界也放弃了我……给我诗,鼓我的气,替我消忧。我的诗神!这样你也是应该看一看我的牺牲罢。这么多!醒,睡与动,静,就只有你在怀;为了你,我牺牲一切,牺牲我!全是我自取的;我决不发怨声。”同时,作为对寂寞的逃避,朱湘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美好的艺术形象,同时加上现实生活的穷困与挫折使他的诗风更显得别致而不同一般,大概这就是“文学憎命达”吧。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到了西方文学中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他把它们概括为梦境和迷醉。在梦境中,人们暂时忘却了现实世界的苦难,可以随心所欲地去编织美丽的幻景。在梦境中为自己创造出一个远离现实苦难的美妙世界。尼采因而认定在这里每人都有自己和谐安宁的天地,梦境世界成了躲避现实痛苦的庇护所。这里是个体的天堂,人人都有自己丰富多彩的世界。“梦境中的美好的幻象,每一个人证明他自己为一完美的艺术家。这不仅是一切造型艺术的要件,同时也是广大的诗之领域所必须”。[6]我们不知道朱湘在美国有没有读过尼采,但是我们看到,朱湘身上体现了西方文化中的酒神精神,对梦境的迷醉,他常常沉迷于自己的诗歌的世界里,在诗的世界里,他总是在幻想着美好的世界。如那久负盛名的《采莲曲》,优美的文字与和谐的旋律,奏出一曲优美迷人的江南曲。“邯郸呀半开,/蜂蝶呀不许轻来,/绿水呀相伴,/清静呀不染尘埃。/溪间/采莲,/水珠滑走过荷钱。/拍紧,/拍轻,/桨声应答着歌声。”[7]真切的体现了新月派所倡导的诗的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
在朱湘的身上,既有东方孤独的名士风情,又有西方酒神精神的迷醉。本文下面将换用另一个角度,继续论述这一主题。
二、悲剧的意识
对于当年曾经名满京城的、春风得意的清华四子之一的朱湘来说,大概谁都没有想到,他会死于贫困潦倒。然而现实就是那么残酷。在“五四”文学影响下的那一代人带有狂放与孤傲的个人主义精神,但是现实的残酷却往往会扼杀他们粉红色的美梦。他们在生活的重重打击面前,被逐出时代的主潮,走向个体的心灵。朱湘应该是这一典型代表。
在生活的挫折面前,他一步步退缩到个体的心灵世界里,孤僻而又倔强、多愁善感而又过度敏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样的性格一方面成就了他杰出的诗歌创作,另一方面又使人望而却步,诗人反而进一步的陷入孤独与苦闷之中。就像他自己所说:“我真是一个畸零的人,既不会做成一个书呆子,又不会作为一个分世故的人。”[8]
到了朱湘的晚年,生活的种种打击使这个本来就心灵脆弱的诗人倍受煎熬,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绝望,孤独的性格使他不能畅谈自己的苦闷,仿佛是一座火山,压抑的越久,能量就越大,等到它喷发的时候,也就是灭亡的时日。其实,诗人的性格是异常独特的,他的心灵世界也是难以追寻,这几年研究诗人之死的文章有很多,比如刘小枫的《拯救与萧遥》。王德威在《现代中国小说十讲——诗人之死》中提到朱湘与陈三立时说:“自杀,成为两位诗人在一个诗意匮乏的年代,所共同承担的宿命。”[9]
大凡以自杀的形式为自己生命作结的诗人,内心世界往往是极为孤僻的,他们已经对这个喧嚣的世界毫无希望,他们没法向这个活着的世界去诉说自己的苦闷哀愁,他们没有真正的知心朋友,世界上也没有他们心灵的听众,他们已经毫无出路,只有死亡才是一种对当前世界的解脱、自我生命的升华,把希望寄托于另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里。其实,说到底,就是无可挽回的绝望。朱湘的死亡在这里具有典型性,又具有特殊性。他孤独而又缺少足够的知心朋友,生活的重重磨难已经让这个性格脆弱的诗人无法承担生活的重担,他性情浪漫,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又无法浪漫,他自认为是这个世界的弃儿,世界抛弃了他,于是他也就抛弃了这个世界,当他在自己的诗歌世界里都无法躲避生活的烦恼时,他已经无路可走,无处可逃。1934年在《人间世》上发表了他的一篇遗作《吊自杀者之歌》,原诗如下:
“啊来,你创伤遍体的失败的生命!/夜是冥黑的,如同死一般的静沉!/ 风吹拂着,细雨也飒飒地飘零--/停止吧,你破碎而还在跳动的心!/归来吧,反于虚无缥缈之乡!/你,生活的失败者,还留恋作甚?安然地睡去罢,而憩息于死!/这儿,不会有人哭泣于你身边!//……啊,来,你创伤遍体的生命!/也是暗墨的,如同死一般的静沉!/风吹拂着,细雨也飒飒地飘零。/ 停止吧,你破碎而还在跳动的心!”[10]
在这首诗歌,似乎已经是其绝笔了,诗人在诗中已经认为自己是一个生活的失败者,一个苦闷的孤独的局外人,他似乎已经无路可走,就只有走向死亡。实际上,朱湘的死是偶然也是性格决定的必然。
这里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新月派的另一位诗人徐志摩,同样是作为新月派的才子诗人,同样是一个短命却又在诗坛上成就非凡的人,我们在他们两人的身上看到了不同的命运,不同的人生。一个人死于风流,一个人死于穷困;一个人死的浪漫,一个人死的悲哀;一个人为情而活为情而死,一个人却是生的悲哀死的也悲哀。
徐志摩和朱湘都是才子,诗歌创作也多以才运笔,但两个人的世风却是那么的不同,神韵上更是相差的太远。这里,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朱湘的名士气与徐志摩的才子气。一个孤独,一个欢快,一个是哀愁的怨妇 ,一个是风流倜傥的才子 ;一个是饱经坎坷的夜行者,一个是欢快跳动不息的生命水。一个为生活而四处奔走,一个追求着“美、爱、自由”;一个低吟着:“我是一个惫殆的游人,/蹒跚于旷漠之原中,/我形影孤单,挣扎前进,/伴我的有秋暮的悲风。”一个高咏着:“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飘逸与悲苦,潇洒与愤懑,两种诗风,两种人格,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朱湘和徐志摩同为新月才子的诗人,命运竟是如此的不同。
三、独特的诗风
朱湘诗歌在艺术形式上同样也体现出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在他的诗歌中有着新月派诗风的特征:格律的整齐,音调的和谐,讲究建筑的美、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对五四白话诗的狂放不羁是一种反驳,纠正了早期白话新诗的狂躁、俗白,对中国传统诗风的借鉴,注重意象的营造,使他的诗歌更加锤炼;同时又积极借鉴西方古典诗歌十四行诗的体式,创作新的白话新诗。
作者在《石门集》中充分借鉴了西方十四行诗体,尽管朱湘在这一诗体的应用上不能说是成功的,但毕竟带有开创性,应用西方的十四行体来写汉语诗,这在中国新诗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不过在借鉴西方十四行体的时候,其格调暗合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悠远情怀,在《石门集》中,采用的即是西方的十四行体,却格调静谧,如其中的一首(英体十六):“只是一镰刀的月亮,带两颗星,/清凉、洒脱,在市廛定下来的夜;/远方有犬吠,车辆奔走过街心,/寥落的;扰攘与喧嚣已经安歇。/古老的情思蓦然潮起在胸头,/以及古老的意境。”
同时,朱湘注重西洋诗歌还表现在他积极主张和实践移植西诗。特别是在《石门集》,他移植了三叠令、巴俚曲和英体、意体十四行诗等多种西方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不过,朱湘移植西方的十四行诗体只是初步的探索,为中国新诗以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朱湘的诗歌中,他的移植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就。倒是在借鉴西方叙事体长诗上,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中国的古代的诗歌很少有叙事体的长诗,它只是大多出现在西方诗歌中,朱湘借鉴了西方的诗歌理论,在中国传统题材的基础上,在中国白话新诗早期,写作了最杰出的叙事长诗《王娇》,借用冯梦龙的《警世通言》第三十四卷《王娇鸾百年长恨》的故事,并进行了艺术加工和改编,完成了这首叙事体长诗。
所以有人这么评论,“朱湘一直注重西洋诗歌,但《草莽集》又以浓郁的东方情调显示其民族性和本土性,它以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实、新与旧、土与洋、艺术与人生多重对立与相通为中国新诗乃至新文学提供了一个复杂的标本。”[11]龙泉明也在《中国新诗流变论》中说到:“朱湘的诗既承受了古代词曲的文字,同时还承受了古代词曲的风格,并注意吸收西洋格律体诗的长处,造成了一种既整饬多变又悦耳动听的艺术效果”,[12]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碰撞对朱湘造成的影响。
朱湘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借鉴体现在对中国古典诗词意象的借鉴上,在这方面,朱湘更是见功夫。苏雪林在《论朱湘的诗》中也谈到朱湘善于融化旧诗词,并举出《落日》的例子,借鉴了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诗句。不过我认为,朱湘并不是单纯的借用,而是把他的人生体会,通过诗歌的意象表达出来,融化在字里行间。他有些诗歌的意象冷酷萧索,充满着鬼气;有些诗歌类似于中国唐代李贺的诗风,阴冷之气贯穿全诗。而且与李贺的人生相同,短命而亡而又才华横溢。
朱湘有些诗歌的诗风奇诡、阴暗,远远的不合乎常人。诗人独特的想象和异样的观察视角,使人们明显的感受到诗人内心世界的阴冷与寂寞。朱湘的短命而逝恰似李贺,奇诡的诗风自然独特,诗中充满着“鬼气”,而这种“鬼气”又不同于同时代的“诗怪”李金发 。
在《死》中,朱湘这么写道:“隐约高堂,/惨淡灵床;/灯光一暗一亮,/想着辉煌的以往。/油没了,/灯一闪,熄了。/蜿蜒一线白烟/从黑暗中腾上。”诗的意境是凄清冷空的,又如 《有一座坟墓》:“有一座坟墓,/坟墓前野草丛生,有一座坟墓,/风过草像蛇爬行。//有一点萤火,/黑暗从四面包围,/有一点萤火,/脥着如豆的光辉。//有一只怪鸟,/藏在巨灵的树荫,/有一只怪鸟,/作非人间的哭声。//有一钩黄月,/在黑云之后偷窥,/有一钩黄月,/忽然落下了山隈。”我们这里对比一下唐代诗人李贺的【南山田中行】的诗句:“秋野明,秋风白,塘水漻漻虫啧啧。云根苔藓山上石, 冷红泣露娇啼色。荒畦九月稻叉牙,蛰萤低飞陇径斜。 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诗中飘荡着的是一种“鬼气”,“鬼灯如漆点松花”,大概只有身有鬼气的人才写的出如此作品。这里,我们看到,朱湘与李贺的诗风都是怪异的,鬼气弥漫的,在这种诗风的背后,映射出诗人内心世界的阴暗、孤独与苦闷,正是这种诗风产生的源泉之一。朱湘短命而亡,选择自杀结束他年轻的生命,这与他孤寂的内心世界,阴暗而又孤独的灵魂,是密切相关的。正如古人所说:“诗言志,歌咏言。”每一首诗歌都代表了一个诗人,代表了诗人当时的心境。朱湘写下如此充满鬼气的诗歌,很容易让人想到他的人生结局。
诗人生前是寂寞的,死后同样是寂寞的。寒江冷月葬诗魂,朱湘只是一个畸零的漂泊者,活在没有温暖的世界里,不如选择死亡,朱湘借他的诗神,传达了他精神上的贵族之气。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朱湘是一个杰出的先行者也是献祭者。魂断采石矶,凄苦还是浪漫?这里就借用他的《草莽集》中的《葬我》这首诗作为本文的结尾,愿诗人与他的诗永恒。
葬我在荷花池内,/耳边有水蚓拖声,/在绿荷叶的灯上/萤火虫时暗时明——
不然,就浇我成灰,/投入泛滥的春江,/与落花一同漂去/无人知道的地方。
注释:
[1]《“名士气”:传统文人气度在“ 五四”的投影》《文学评论》,1999年6月。
[2]《二罗一柳忆朱湘》,三联书店出版社,1985年第37页。
[3]罗念生《朱湘·序》,孙玉石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2月。
[8]朱湘,《中书集》,上海生活书店发行,1937年5月第168页。
[4][5][7]《朱湘诗全编》,吴方、越宁 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第7、22、91页。
[6]《尼采文集》,楚图南译,改革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528页。
[9]《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208页。
[10]《吊自杀者之歌》,《人间世》第十一期,1934年。
[11]徐莉华《我国现代诗人创作与借鉴的另一种尝试》,《外国文学》,2002年11月。
[12]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49页。
(李宗超 韩 霞,日照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