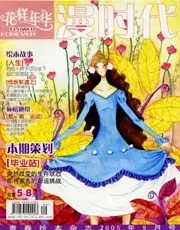三个人的毕业走失
风 快
消失在尘埃
他先被一方抛弃,另一方却没有及时接纳他,他悬在空中没有皈依感,成了走入人生的第一个冲突,第一个断层,尚未完全成熟的独立人格反过来耻笑他不能独立的现状,于是他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用自杀来消除学校和社会的断层。
柳涛四岁那年做过一个梦:一列火车从头顶飞驰而过,他被甩了下来。那年母亲离家远行,从此柳涛与父亲相依为命。柳涛显得早熟,从小便沉默寡言,上学以后老师表扬他聪明懂事,但每次考试前,他都会出现异常的低烧症状,四肢痉挛、疼痛,并且消化不良。后来他开始偷窃,简单的学生用品,伴随着一场一场谎言。
没人知道,柳涛的内心深处充满了撕裂般的痛苦。16年的求学生涯,学校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成绩上,老师按成绩区分“好学生、差学生”,柳涛是“好学生”,于是他带着所有的心理负担,走到了大学毕业前夕。终于在这个夏天,柳涛迎来了第一个“心理高危期”,他变得更加焦灼、忧虑。按照专家们的说法,大学生的心理困扰首先来自“神经”方面,也就是神经症。
柳涛是极端的例子。他神经衰弱、注意力涣散、食欲减退。接着,焦虑症的折磨使他出现了头晕、训季、呼吸困难等症状。然后就是强迫症——他猜疑社会的陌生环境将如何“陷害”他。对于走出校园后的生活,他无数次暗示自己:“我将是一个失败者。”这变成了不可抗拒的观念和意向。
最后,当校园恋人随着一列火车远走之后,四岁的那场噩梦又一次笼罩了柳涛。此时此刻,他仍能勉强克制自己的绝望,仅存的理智告诉他,后面的路还要再走。
他抑制着强烈的心理冲突带来的焦虑和恐惧,投入到汹涌的求职大潮中。他认为自己能证明一些什么;比如“好学生”的成绩带来的成就感,或者繁忙的社会人角色带给他的荣誉。
与其他应届毕业生一样,柳涛学着微笑,在一次次面试中,努力用稳重的语调展示自己的信心。有时他接到父亲从家乡打来的电话,关切中透出怀疑和期待。他对父亲说,我在应聘……我在等候通知……我在继续等候通知……
他忘了投出去多少简历,混乱无序的情绪和冷酷的表格形成强烈对比,笔端流淌的一笔一划越来越沉重,仿佛刻在父亲的血肉上。终于,他对面试产生了强烈的恐惧,他开始逃避,变得更加压抑、沮丧。
柳涛这种不断发展的行为特征,介于精神病患者和正常人之间,通常在巨大的断层前被激化。毕业前后,校园与社会在这个焦点上形成巨大落差,犹如地壳运动产生的强烈震动一样,终于将柳涛的心理疾病引爆了!
柳涛在思家情绪的推动下,扒上一列火车。从童年开始,他就被火车的噩梦裹挟,也许此刻他想用这个方式进入那场梦,为自己的过去做一个告别。火车的摇动与轰鸣,使他想起了求职的人群,以及整个不安定的青春期,空洞、茫然、狂喜、愤怒的神情中,透出可怕的意念,柳涛又在暗示自己:“我矢口道,我是一个失败者。”
柳涛半夜回到家中,父亲惊醒过来,看到他时,目光里有着欣慰和无奈交织的复杂情感。柳涛在家里暂时平息下来,然而不久以后,他陷入更加奇怪的混乱状态中,并伴随有幻觉出现。他意识到自己仍然受到父亲的供养,这对他赖以生存的独立人格是个严重打击。他突然想结婚,摆脱父亲对他的期望;但马上又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终于,他在焦虑的精神状态里,走向了极端。
柳涛选择的方式与一名即:曙毕业的博士生一样,从九层楼跳下。他给父亲的遗言说:我也想列出一张单子,左边写着活下去的理由,右边写着离开世界的理由。我在右边写了很多很多,却发现左边基本上空白。父亲,对于您,我只能无奈,或许死后时寂静,就是为了屏蔽您的哭声,就是能让我不会在那一刻后悔……
柳涛给人们留下了非常复杂的问题。首先,他的“成人礼”是缺失的,就像他列出的单子一样,一半空白,一半充满痛苦与绝望。
他的思想意识想尽早建立“自主权”,想与成年的环境实现有效沟通,然而实际上,他的内心却处于幼稚阶段,仍需要父母的关怀。在以往漫长的求学生涯里,他可以暂时接受老师的引导,那是一种无知无觉的沉溺状态;就像找到了“代理父母”。毕业之后,代理父母的角色原本应该由学校转交给社会,然而此刻,柳涛突然对陌生环境产生了不信任感,甚至猜疑社会可能“陷害”他。接下来他在求职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挫折,这些原本都是正常的,是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部要经历的风雨磨练,但他脆弱的心理却将这一切无限扩大,变成了灾难。
他先被一方抛弃,另一方却没有及时接纳他,他悬在空中没有皈依感,尚未成熟的独立人格反过来耻笑他,于是他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消除断层。
柳涛将自己的人生定义为宿命的悲剧,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位毕业生警醒,更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引起高度重视。我们不能将心理疾病从学校带到社会,再传递给下一代,这样的大学教育成本太高、代价太大、后果太严重。
行走的事业线
刚刚脱离校园的大学生,常常是痛苦大于希望,她在不同城市中游移不定,本身就是对16年校园生活的一次颠覆!
大三那年,郑雨彤参加了一次网友见面会,当时有个朋友看了她的掌纹,半开玩笑地说,你的事业线很复杂,注定一生行走,就像城市游牧族。
那一刻,雨彤怦然心动。她知道自己骨子里是很不安定的人,永远不会属于某个地方,或某个人,这与父母对她的期望完全相反。大学毕业,周围的同学都在为即)曙离开校园的宁静港湾而伤感,同时又为迷茫的未来焦灼不安,雨彤却有了一种彻底解脱的感觉,她首先想到的是:生命从此自由。生命属于我自己了。
雨彤从一座城市游移到另一座城市,每到一座新城,她都要将QQ上的签名换掉。比如她写:给你武器去原野奔跑,从此不复相见。还有:我在等待结果的结果,你不会懂。再有:我拒绝死不暝目的感动,我行走在自己的生命漩涡。
她常常对生活抱有一种好奇的眼光,她的工作就围绕着好奇的生活。她会做漂亮的设计方案,很多公司挽留她,而她的回答永远是:这座城不属于我。或者仅仅一笑而过。
她也接到父母的电话,他们对她说不上失望还是欣赏,一个女孩子,他们总这样说,一个女孩子……雨彤便在心里接上一句:一个女孩子,怎么也会有英雄情结?
行走,其实是一种潜在的“追求复活”过程,是内心深处对远古诸神的膜拜。也许雨彤只把她的游走当作游戏,至少,流动状态可以减轻某种,心理压力,但她没有意识到,就像她所热爱的季节一样,她其实热爱着某种神圣的祭仪——弃一座城的同时,便拥有了另一座城,这使她在心理上完成了一次重生。最显著的例子,一是那年冬天她感到冷,便买了一张车票从西到南,一直来到海南,呼吸到阳光里的热情青。正如古老的游牧民族膜拜冬至的节日,一抹阳光令北半球渐渐消失的冬景得到更新的希望,不
知不觉地,他们一起进入了“再生”的象征意义中。
这种心理模式解释起来有些困难,它更多地属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境界。可以这样说,古代游牧民族追逐日升、日落,循着自然的生命状态度过自己的一生;雨彤这样的城市游牧族,则完全按照内在的精神需求安排自己的脚步,两者的本质是一致的:追求消亡与新生的永恒重复。
我们不难看出,这个重复过程与“毕业”非常相似。毕业生从校园走向社会,完成了一次结束与开端,雨彤用生命在行走,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校园与社会之间存在的断层,换句话说,她的游移不定,本身就是对16年校园生活的一次颠覆!
当然,有时也会有强烈的伤感。人,总是需要安定的,这种伤感便来自无法寄存的灵魂,有时也与爱情有关,细腻的内心变得躁动不安。刚刚脱离校园的年轻人,总是痛苦大于希望,即使如雨彤这样“自我意识”非常强烈的英雄主义,性格,也常常对自己的力量产生怀疑。这是心智渐趋成熟的阶段,毕业使她有了成熟的意识,游走使她学会了成熟。
雨彤目前还没什么野心,也许等她真正成熟以后,她会停下脚步,像典型的英雄人物一样,为一个永恒的目标耗尽心力。然而,游牧族的气质是终生的,记住雨彤的行走过程,那是牺牲与重生的完美公式。
“校漂挨”其实是家庭和学校共同制造的“寄生物”,把“校漂”作为人生的缓冲期,维护自己脆弱的心理,以便寻找更好的人生起点。
李维钶与另外两名大学毕业生合租了一套房子,寄居在学校边缘,开始了“校漂族”的生活。李维钶是为了避开就业高峰,同时增加就业砝码而留下的“考试派”;赵勇是不愿离开学校的“恋校派”;孙利磊则是求职不满意、要求回校再谋出路的“不就业派”。
他们租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房间里没什么摆设,他们都很清楚,无论出于什么目的,现在的生活状态都是暂时的,只是一时无法适应从校园人转向社会人的心理落差,而实行的战略退却。
李维钶给自己的房间门贴了告示:影响别人休息是一种犯罪,本区每晚11:30执行“三闭”政策:闭门、闭灯、闭嘴!他用这种方式,既向自己的成年期挑战,同时又是一种妥协。毕业后,他原本已经工作了一年,但是不满意工资收入,干脆辞职来北京考研,算是背水一战。
李维钶在工作期间没什么积蓄,现在生活来源的大部分仍靠家里支持,重新;仑为“寄生虫”让他感到既羞耻又无奈。由于他经受过短暂的社会磨练,发现实际所得与内心期望总是存在巨大差异,于是常常产生“相对剥夺感”。与此同时,竞争压力、生存焦虑和强烈的发展期许交织在一起,对他脆弱的心理更是一种痛苦折磨。
相比于李维钶,身为“恋校派”和“不就业派”的赵勇、孙利磊则相对轻松一些。赵勇在北京另外一所高校某系实验室从事计算机网络维扩工作,收人能维持生活。他和孙利磊不离开学校的理由很简单:“学校单纯啊,可以做透明人。虽然我能去校外的公司上班,凭我的技术,也能赚更多的钱,但我害怕与领导、同事相处,我的不少同学都说社会上人际交往太复杂、太危险。我喜欢学校的温暖环境,我熟悉这里的一切,不但能利用学校的资源,每年还有两次长假,能做自己喜欢的事。”
“校漂族”其实是家庭和学校共同制造的“寄生物”,把“校漂”作为人生的缓冲期,维护自己脆弱的心理,以便寻找更好的人生起点。选择“校漂”大致出于以下几种原因:安全需要、依赖心理、逃避心理、现实考虑。
心理学告诉我们:我们的意识中,没有什么东西是陈旧的,也没有什么东西会真正地、肯定地消亡。如果有人想退回到过去,来回避新鲜的、陌生的东西,那他会陷入神经症的状况;反过来,如果有人只接受新东西而背离过去的话,结果同样交口此。
引用心理学家荣格的一句话:在人的整个一生中,他应该做的,只是在固有的性格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展它的多样性、连贯,性与和谐性,不能让它破裂为彼此分散、相互冲突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