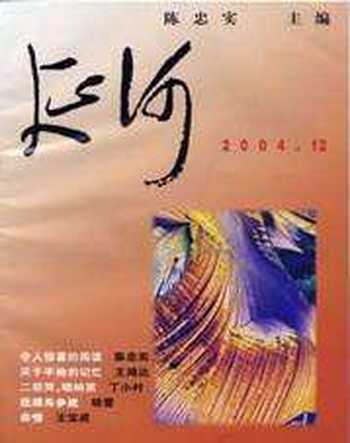陕西多出奇人
艾 涓
已记不清是因为什么原因,我请好友阿明画了柳青先生漫画。
记得是在办公室里,正好有半张宣纸,便将漫画随意撕下贴在上面。也是巧合,这天我去向平凹君约稿,他正在写字。平凹的字难求人人皆知,但我还是拿出这经过加工的有柳青先生漫画的小纸片,请他题写几句相关的话语。大概因为上面有他尊敬的人物,阿明也是他的好朋友吧,平凹显得很大方,信笔写了起来,写满了这张纸片。字一如既往,随意而自然,与神形俱佳的漫画相映成辉。所写话语更是表达了他的心思:“陕西多出奇人,现代以来,有于右任、柳青、石鲁、张艺谋。而于、石、柳我皆未见过,张遇见一面。晓明今作柳像,算我见了先生。”这是平凹所推崇的陕西文学、书画、影视四个方面的重量级人物。
这四个人物,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是杰出代表,影响着这些领域的发展。于右任是国民党的元老,他的标准草书开风气之先,左右着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关于柳青与《创业史》,著名评论家阎纲有过精彩的评述,他说:“柳青一生热爱农民,歌颂农民,最后变成农民。他取得农民的资格以后,便以中国农民真正的代表表现中国革命。他的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以大量无可置疑的生动细节建造而成一座庞大的殿堂。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农民运动行将到来和已经到来时各阶层农民面貌和心理的忠实表现者,柳青的确是杰出的,《创业史》因此成为史诗性的名著。”这段话从人格魅力、艺术魅力和思想魅力上高度总结了让中国文学骄傲的柳青先生。石鲁,同样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早在四十年代就以绘画艺术反映人民战争生活,进行革命宣传。解放后他潜心钻研中国画,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其作品表现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是长安画派中的领袖人物。而张艺谋,也是以他的独特风格驰骋国际影坛,为中国的电影事业发展创下了几多辉煌。当然,如今的张艺谋,因其导演的电影《英雄》《十面埋伏》受到几乎是所有娱乐媒体的责难,从《十面埋伏》公映以来,不间断地有媒体在一边倒的批评。偶见《西安晚报》上就有半个版的关于他的批评,一篇是《娱乐传播“运动化”,进步?恐怖?》其中有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苏牧说,我是不能原谅张艺谋的。因为我认为,原谅了张艺谋,对中国电影的发展和生存,会更加不利。一篇是《名导朱延平:张艺谋已经“死”了》,朱导毫不客气地说:“《英雄》和《十面埋伏》走的都是豪华路线,就是纯粹的商业片。尽管炒作和拍摄非常成功,画面精美、制作精良,但已经不能代表张艺谋本身了。这样的片子只要有钱,任何一个导演拍出来都不会输给他,只能算是一部不错的商业片。严格意义上讲,张艺谋已经‘死了。”
平凹推崇的张艺谋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严峻的挑战,为他的艺术。我自以为,张艺谋似乎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比如在电影的原材料———故事的准备上,就犯了严重的失误。大家还记得让他名扬天下的那几部电影,诸如《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等,每一部电影的故事原创都是其作品本身已在读者中获得了较高的声誉,每一部作品都有着耐读的故事情节。而后来的张艺谋的电影作品的故事,来自哪里,这里面又有多少成分是搀杂了张导的个人情绪呢?我想,这可能是张艺谋遭到全面攻击的重要原因吧。
由平凹的题字说到现时的张艺谋,似乎跑题了,就此打住。
周明与文怀沙
周明先生是著名的编辑家、散文家和文学活动家;文怀沙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国学大师、楚辞泰斗。以两位重量级人物为题作文,是因了我所收藏的几幅墨宝。
我收藏的“一生只流双行泪,半为沧桑半美人”字幅,是2004年5月下旬召开的陕西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研讨会上,周明先生为我书就的。题款:“录文翁句赠艾涓。”文翁———就是文怀沙先生,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关于爱美和性的精彩评论。九十高龄的文翁,还经常骑自行车出入街头,有人劝他出门坐车,不要再骑车了。他说,坐车人是不自由的,骑车人精神是自由的。骑车人只要不闯红灯,可以东南西北自由行驶,坐在汽车里就没有这份自由了。再譬如,路旁走过一位婀娜美女,坐在汽车里的只能看个瞬间,而骑自行车则可以下车驻足仔细观之品之,人生赏美是一大乐事,失之则不再来!这是老人的美人情结。关于性,他以性命两字作解:“性命,有性有命,无性即无命可言。”(大意如此)。这些年来,老先生对美的率性追求,流传在文坛上的风流韵事,竟遮掩住了他作为国学大师和楚辞泰斗的光辉形象。我倒要说文怀沙先生可算是当代的奇人义士。我品味着老先生的鹤发童颜与风流倜傥,也感慨着耄耋老人竟有如此的炯然精神。这一联句,恰到好处地印证了我脑海中所存留的文怀沙的形象……
然而,时隔不久,关于这一联句,又有了新的话题。
10月10日左右,周明先生去宁波参加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和翻译家王鲁彦先生逝世60周年纪念活动,恰与文怀沙先生同机前往。我便请周先生求文翁为我题写“虚室小品”四字。并求证“一生只流双行泪,半为沧桑半美人。”联句的写作背景。很快,12日晚,我接到周明先生电话,一是告知文翁已题写了“虚室小品”,二是讲了“一生”联句有出入以及联句的写作因由。
“一生”联句的本来面目是“平生只有双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大概是在1941年的某个季节,文怀沙对暨南大学附中的一位女教员十分钟情,大有非此女不娶之念头。他辞掉原来的工作,追到暨南大学附中应聘为国文教员。然而,文怀沙的痴情并没有赢得这一女子的芳心。爱情的失败,国家遭受外敌的侵入,使他感慨万分,吟咏出了“平生”联句。后来,柳亚子先生知道了文怀沙的情事并见到这一联句,大加赞赏,有联为证:“未嫁已倾城,君诗如美色。”
在宁波,文翁将“平生”联书赠周明先生,并对自己的人生大发感慨。在谈到和自己有过情感冲撞的女人,他说:“我只记她的爱,不记她的恨;只记她的恩,不记她的怨。”能见出老人的心性来。关于“平生”联,文翁还讲到另一层意思:“美人者,既涵盖了人间美女,但比美女含意更为广泛,《诗经》里把‘美人兮‘芳草兮,视为人间美丽的象征,因而你们可以把它看成是美到极致的追求和表达。”这是一个多情多义的文人,有着万般的柔情,万般的智慧。
借周明先生之光,我写了上面这段文字,至此本应结束这篇文章,不意,我读到了丛维熙先生写的《文怀沙剪影》,其中有一段文字能见出文翁的另一面。大概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文怀沙被下放劳动期间,陪文怀沙老母前去看望的友人,劝他给江青写封信,一表示悔改,二表示知恩图报。文怀沙断然拒之,并写成了一首诗表明心迹。其言曰:“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若将每句的第六个字连接起来,就是“龟主江青”。在那个乌云蔽日的年代,有如此的胆识,能见出一个铮铮铁骨、阳刚之气甚盛的文怀沙。
因了周明先生,我既得到了文翁的墨宝,还成了这篇文章。依文翁解释“性命”的方式,“缘分”就是“无缘无分,有缘有分”。周明先生、文翁与我,也算是“有缘”“有分”的。
白烨与郁达夫
郁达夫是写小说的;白烨是读小说的。写小说的郁达夫用自己风格和思想留下了传世之作,不说别的,一部《沉沦》小说集,就能使我们永远记住郁达夫。在谈论时人很挑剔的知堂老人有一篇专说《沉沦》的短文,我以为入情入理。谈到文坛上有人说《沉沦》是不道德的小说时,他列举美国莫台耳(Morddell)在《文学上的色情》里论不道德的文学的观点,认为“《沉沦》是显然属于第二种的非意识的不端方的文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他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示自己,艺术的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所在。”“而《沉沦》却是一件艺术的作品。”我推崇知堂老人的这篇文章,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其中的一些说法还能让读者对以往的关于郁达夫创作之外的某些放浪形骸行为以及被冠上“浪漫派”“颓废派”的称号,会有重新的认识。他说:“生的意志与现实之冲突,是这一切苦闷的基本;人不满足于现实,而复不肯遁于空虚,仍旧在这坚冷的现实之中,寻求其不可得的快乐与幸福。现代人的悲哀与传奇时代的不同者即在于此。”今时不同于往时,人们的思想也在发生着变化,也许,在今天的读者,还会将羡慕的目光投向郁达夫时代的生活方式。我想,这不是他所希望的。
写郁达夫,我拉出了白烨,是因为“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这两句诗,十多年前,我曾请著名书法家邱星先生书写过,也曾让平凹君写过。邱星老的书法作品被我转赠友人;平凹君是写在册页上,不宜示人。2004年的初夏,我与白烨先生有过几次同案书法表演的机会。期间,我请他书写了这两句诗。而这两句诗,是摘自郁达夫《钓台题壁》,现录于此:“不是尊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欣赏这首诗,非本文所能,只说“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其一是讲诗人纵酒狂放,生恨生怨迁怒于马;其二是说有情者自是多情,爱美人却还要怕累美人。郁达夫的热爱美人,从他的作品包括日记里我们都能有深刻的体会,无须赘言。白烨才识、胆识具备,与酒有缘;也是多情而爱美之人。写小说的郁达夫给我们留下动人的诗句;读小说的白烨馈赠我书写郁达夫诗句的墨宝。
我一再说白烨先生是读小说的,读者万不可认为他是如同你我般地读。你我读小说,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选择作品,而白烨的自由不多,他是职业读小说的,绝对不能有好恶之念,他必须将市场上流行的长篇小说整体阅读。如不这样,我想每年关于长篇小说的综述文章他是完不成的。即使能完成,也不能服众。这些年来,写小说的人是风起云涌,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老的少的、美的丑的都可大把大把地抓起来,数量之大可想而知,再加上新兴的八十年代派,我真不知道白烨怎么会有如此的勇气,敢揽这档子事———这可是出力不讨好的事啊!文章中提到的,必须说好,稍有不妥,会招白眼的;未提到的,当然是要骂上几句方能解恨,于白烨只能是忍受了。
白烨先生读小说,读出了自己的感受和理性的升华,也读出了风情万种。爱美是人之常情,如同读小说一般,白烨的爱美和为美付出的表现也是很独特的。既不同于郁达夫,也与我等平常人有异。这些年街上流行的美女作家,十有八九都于白烨有关系,当然不是暧昧关系,读者千万不敢理解错了,我说的关系,是指这些美女们出的书大都是经过白烨的策划而出笼的。卫慧啊、棉棉啊、等等、等等,她们的成功与白烨身心的付出是分不开的。现在,白烨先生除了诸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等职务外,还被同行誉为文坛上女性作家的“党代表”。听说在2002年5月20日由北京文学和北京日报联合举办的“她世纪与当代女性写作研讨会”上,白烨成了万红丛中一点绿。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这是男人写的诗句,为男人而写。我收藏了白烨先生的墨宝,经常拿出来欣赏———为这两句诗的深刻含义,也为如白烨先生形象一般清爽、俊朗的书写风格。
艾涓原名刘辉,男,1967年生。1991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先后出版了诗集《这边风景》,随笔集《移动的城市》、《艺文空间》等,系省作协会员。现就职于省政府某部门。